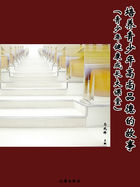从这个世界一开始,每个世纪都会发现奇妙的事物,但上个世纪发现的数目超过了以前任何一个世纪,这个世纪则揭示了成百上千个更加震撼人心的事物。一开始,人们不相信自己能做到一件奇怪的事情,接着他们希望自己能做到,并看见别人做到了,最后自己也做到了,全世界都感到奇怪,为什么几个世纪以前无法做到呢?这个人们开始发现的事情之一就是思想,它的威力就像电池,或者像阳光一样美好,像病毒一样恶劣。如果我们内心产生了一个悲伤或恶劣的念头,它所具备的危险性可以等同于在身体内放入一个猩红热病菌,只要让它继续留下来,那么我们永远也无法痊愈。
如果玛丽小姐心里一直充满不开心的想法,她就会讨厌其他人,并决定不让任何东西取悦自己或引起兴趣,她就是个脸色蜡黄、病怏怏的倒霉孩子,但现实情况非常善待她,虽然她自己并未意识到。当她四处游荡时,心里逐渐填满了知更鸟、旷野、古怪的老花匠、朴实的约克郡小女仆、挤满孩子的农舍、一个农家男孩和他的小动物,还有春天和逐渐苏醒的秘密花园,这些东西很有好处,因为她的心里再也没有地方留给那些不开心的想法了,那些东西只会影响她的肝脏和消化,让她的脸色变黄,容易疲倦。
如果科林一直待在房间里考虑自己的恐惧、虚弱,以及讨厌被别人看见,每个小时都想着小包和死亡,他就不会知道阳光和春天是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如果自己努力尝试就可以好起来,可以站起来,他会成为一个歇斯底里的小疑心病患者,甚至陷入半疯状态。当美丽的新念头推开丑陋的旧念头时,他重新恢复了生命,健康的血液流过血管,洪水般的力量涌进体内。其实,他的科学实验非常简单而实用,没有丝毫奇怪之处。如果我们的理智能及时用坚决勇敢的念头推开不开心和泄气的念头,那么任何人都会发生更加惊人的新变化。这两种念头永远无法同时存在。
我的孩子,如果你种下一株玫瑰,那么,它身边绝不能生长刺蓟草。
当两个孩子随着秘密花园活过来之后,有个人一直在美丽但遥远的地方——挪威的峡湾和深谷、瑞士的群山——游荡,他心里装满了令人心碎的黑暗念头,至今已经有10年了。他在蓝色的湖泊边想着它们;在开满了深蓝色龙胆花的山腰上想着它们,空气中弥漫着犹如地毯一般的鲜花气息;他曾经一度幸福,但可怕的悲痛突然降临,从此,他的心灵塞满黑暗,并顽固地拒绝哪怕一丝阳光。他荒芜了自己的家园,忘记了自己的责任,当他四处旅行时,脸上笼罩着黑暗,对别人来说,看见他是一件坏事,因为那种阴郁似乎毒化了四周的空气,陌生人多半以为他是个半疯的人,或者隐藏了某些罪行。这个阴郁的高个子男人是个驼背,他登记住宿时的名字是:“英国、约克郡、米瑟威斯特庄园、阿奇博尔德·克雷文。”这个不曾勇敢的人从未尝试用其他想法来代替灰暗的念头。
自从他在书房接见了玛丽小姐,并告诉她可以拥有“一点泥土”之后,便开始了旅行。他旅行的地域很遥远,范围也很广大。他去过欧洲最美丽的地方,但他在任何地方都待不长久,于是只好选择偏远而宁静的地方,他曾在山顶俯瞰世界,初升的太阳为群山染上光辉,仿佛世界正在诞生。
但这些光辉从未给他带来光彩,直到有一天,他突然意识到,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这是10年来从未有过的情形。
这次,他独自穿越奥地利提柔省的一个美丽山谷,眼前的美景能够将任何人的灵魂从阴影里解脱出来,但依然没有让他打起精神。他走了很远,最后觉得有点累了,于是坐在溪流边休息。清澈的溪水在狭窄的河道间快乐地奔流,它穿过芳香湿润的绿地,有时冒着泡越过石头,发出的声响好像有人在轻笑,这些细小的响声让宁静的山谷显得更加幽远。
阿奇博尔德·克雷文凝视着清澈的流水,偶尔会有小鸟飞过来喝水,然后拍着翅膀飞走了。慢慢的,他觉得身心安静得就像这座山谷,他想:自己是不是睡着了?但他并未睡着,一直凝视着阳光照射的流水,并注意到溪流边缘有某些东西——是一株好看的勿忘我,它的叶片湿漉漉的,他突然想起来,自己多年前也曾注视过它。他温柔地想:它多么可爱,这些小花朵的蓝色是如此神奇。他不知道,一个简单的想法就这样慢慢注入了他的内心,它轻柔地推开了其他东西,仿佛一潭死水中突然升起了甜美清新的春天,最后扫荡了所有的黑色。不过,他完全想不到这些,他只知道,自己注视那些鲜艳娇嫩的蓝色时,山谷越来越静。不知道坐了多久,最后,他轻轻一动,仿佛从梦中醒来,他站着长长地吸了口气,觉得非常奇怪,心里的一些东西似乎悄无声息地解放了。
他用手摸着前额喃喃自语:“怎么回事?我觉得自己好像——重新活过来了。”
我不了解这个未知而奇妙的东西,因此无法解释究竟是怎么回事,他自己也完全不懂。但是,他一直记得这个奇怪的时候,当他重新返回米瑟威斯特庄园之后,偶然间发现,科林就在那一天进入了秘密花园,并在同一时刻喊出:
“我要活到永远的永远!”
这种异乎平常的平静保留了一夜,他的睡眠是全新的、安宁的,但它没有持续多久——他不知道这种平静可以一直延续下去,第二天晚上,那些黑暗的想法又通过他打开的门排队冲了回来。他离开山谷继续自己的流浪,但让他奇怪的是,有几分钟,或者半小时,他莫名其妙地觉得黑暗似乎走开了,他感觉到自己依然是个活人。慢慢的,在一种无人知晓的原因下,他随着秘密花园一起“活过来”。
当夏天过去,深金色的秋天来临时,他到达了寇眸湖,并在这里找到了可爱的睡眠。白天,他在蓝色的湖边或山坡上柔软浓密的青草中来回跋涉,直到累了为止,他想,或许这样能睡着。不过,他现在已经睡得好些了,觉得做梦不再是一种恐惧。
他想:“可能我的身体变强壮了。”
的确如此,不过,真正的原因是那些少有的平静时刻改变了他的想法,灵魂也随之变得强壮。他开始回想自己的家,考虑是否该回去,偶尔会模模糊糊地想起儿子,然后扪心自问:他是否能再次面对那个睡在四柱雕花床里的小人儿?那张沉睡的小尖脸轮廓分明,雪白的皮肤如同象牙,紧闭的眼睛周围是惊心动魄的黑睫毛。想到这些,他又退缩了。
有一天,他走得很远,回来时满月已经高高悬挂在天空,整个世界被银色和紫色的阴影包围着,宁静的湖水和树林如此美妙,因此他没有回到别墅,而是坐在湖畔树荫下的小露台里。他呼吸着夜晚散发出的香气,感到那股奇特的平静又悄悄蔓延开来,直到他坠入梦乡。
他不知道自己何时入睡,何时开始做梦的,因为他的梦就像是真的,后来他回想起时,总觉得自己当时非常清醒,觉得自己坐着享受玫瑰的芬芳,倾听拍打的水声,突然从远处传来一声呼唤,他听得清清楚楚,仿佛声音就在附近。
这个甜美、清澈、快乐而遥远的声音呼唤着:“阿奇!阿奇!阿奇!……”
他依然记得,自己跳起来毫不吃惊地回答:“莉莲!莉莲!你在哪里?莉莲!”
然后声音传回来:“在花园里!在花园里!”
梦结束了,但他没有清醒,而是继续睡了一个好觉。当他醒来时,晨光已经很明朗了,一个仆人站在他面前。这是个意大利仆人,他和别墅里其他仆人一样,对外国主人的怪癖已经习惯了,不会提出任何问题,比如主人何时出去?何时归来?晚上睡在哪里?等等,任由他们在花园里四处游荡,或在湖上的一艘船里休息。这个仆人拿着一个托盘,上面是一封信,他安静地等克雷文先生拿起来之后便离开了。
克雷文先生继续坐着观赏湖水,手上拿着信,那种奇怪的平静依然存在,而且还有一种轻松感,仿佛那些残酷的事从来没有发生过——似乎有些东西改变了。他回忆着那个梦——真实的梦。
他游移不定地低语:“在花园里!在花园里!但,门上了锁,钥匙被埋起来了。”
过了几分钟,他看了一眼信件,是一封从约克郡寄来的英文信,信封上的笔迹很朴素,但不是他熟悉的字体。他几乎不假思索地打开了信,完全没有想到寄信人,但第一行字就吸引了他的注意。
亲爱的先生:
我是苏珊·索比,曾经在旷野上冒昧地拦住了您,但那次的话题是关于玛丽小姐。现在,我再次冒昧地请求您回来,先生。如果换了是我的话,一定会这么做。我想,您回来之后肯定会很高兴的,而且如果您的夫人依然健在——请您原谅,先生,我想,她也希望您这么做。
您忠诚的仆人苏珊·索比
克雷文先生连着读了两遍才将信放回信封。他一直想着那个梦,最后他说:“我要回米瑟威斯特,对,立刻就走。”
他回到别墅命令皮切尔做回家的准备。
几天后,克雷文先生乘坐火车重返英格兰。在遥远的路途中,他惊觉地发现自己在思念儿子,虽然他并没有刻意思念,但关于孩子的记忆不断飘入脑海,在过去的10年中他从未像现在这么想,那时,他只希望能忘记一切。他记得,自己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像个疯子一样四处狂奔,因为孩子活着而母亲死了。他曾经拒绝探望孩子,当他终于想面对时,那个小东西既虚弱又可怜,所有人都断定他活不了多久,但是,那些照顾他的人非常吃惊,因为他竟然活下来了。接着,他们又认为这个孩子会长成一个驼背或者瘸子。
虽然他不想成为一个坏父亲,但他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个父亲。他一直为孩子提供医生、护士和奢侈品,但他害怕想起这个孩子,始终将自己埋进不幸之中。当他离开米瑟威斯特庄园在外面流浪了一年之后,曾回去探望了那个模样悲苦的小东西,他用围满黑睫毛的灰色大眼睛冷漠而疲倦地看着自己的父亲,这双眼睛和他曾经深爱的快乐的眼睛极其相似,但又骇人地不相似,他受不了继续看着它,只得面如死灰地转身离去。从此,他很少去探望这个孩子,除非他在睡觉,现在他只知道,这个孩子已经确确实实是个残疾,而且脾气暴躁,处于半疯癫状态,如果想让他避免危险的狂怒,唯一的办法就是所有的事情都顺从他的意思。
这些回忆并不是振奋人心的事情,但随着火车穿越蜿蜒的山路和金色的平原时,这个即将“活过来”的人开始用一种全新的方式进行思考,而且思考了很久、很透彻。他自言自语地说:“也许,我错了整整10年,很长的时间啊!也许,一切都太迟了,这么多年,我怎么会产生这些想法!的确太迟了!”
当然,一开始就说“太迟了”是错误的魔法,就连科林也知道这一点,不过,他完全不懂魔法,还要经过学习。克雷文先生想知道,是不是这个充满母性的人——索比太太已经发现孩子的病情更严重,甚至奄奄一息,才鼓起勇气写了这封信?如果那些神秘的平静咒语占据了他的身心,或许他现在的想法比任何时候都要悲惨,正是因为这些平静带来了一种勇气和希望,他没有屈从最坏的想法,而是努力在相信更好的情形。当他发现这一点时,自己也很吃惊。
他想:“她是否觉得我对孩子可能会产生一些好处,或者能控制他?不管怎样,在回家途中我要去看看她。”
于是,当他穿越旷野时便把马车停在农舍前,七八个正在玩耍的孩子聚在一起,每个人都行了一个礼貌而友好的屈膝礼,接着说:“妈妈清早就去了旷野的另一头,帮助一个刚刚生完孩子的女人。不过,我家的迪康在您的庄园,他每个星期都会去几天,在其中的一个花园里干活。”
克雷文先生看着这些结实的小身体和红红的圆脸蛋儿,他们友善地笑着,虽然每个人都各有特点,但克雷文先生吃惊地发现:他们都非常相似地健康。他也笑了,并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金币递给最大的“我家的伊丽莎白·爱伦”说:“如果你能将它分成8份,那么每个人都会有半个银币。”
然后在咯咯的笑声和轻快的屈膝礼中,他坐车离开了,身后留下的是孩子们轻推着手臂和高兴地蹦跳。
驾车穿越美丽的旷野是件神清气爽、心旷神怡的事情。为什么他产生了一种回家的感觉?这种感觉是天地万物都美丽,这种感觉是远处紫花开,心里暖起来,他曾一度认为自己再也不会出现了。距离那座巨大的老房子越来越近了——它保存着同一血脉的人们已经有600年了,他不禁想起上锁的房间,想起躺在雕花四柱床上的儿子,想起上一次如何驾车离开,这些都让他不寒而栗。或许他能发现自己正在好转,或许能克服无法面对孩子的畏缩?那个梦多么真实,那个声音多么美好而清澈,“在花园里!在花园里!”
他说:“尽管我不知道原因,但我必须找到钥匙并打开门,我必须这么做。”
克雷文先生到达了庄园,仆人们按照通常的仪式接待了他,他们发现,主人看起来好些了。他没有回到那个常住的、由皮切尔照管的偏远房间,而是派人找来梅德洛克太太,在书房接见她。梅德洛克太太过来时多少有点激动、好奇和惊慌失措。
他问道:“梅德洛克,科林少爷现在怎么样了?”
“嗯,先生,他——这么说吧,他变了。”
“恶化了?”他试探着。
梅德洛克太太竟然脸红了,她说:“嗯,您瞧,先生,克雷文医生、护士和我都搞不懂他。”
“究竟怎么回事?”
“先生,说实话,科林少爷的情形可能是好转,也可能是恶化,因为他的胃口简直难以理解,而且他的性子——”
“他是不是变得更加——古怪?”主人紧张地皱着眉头。
“是的,先生。如果将他和过去相比,现在更加古怪。以前他什么也不吃,但突然之间吃得很多,接着又突然停止,饭菜和过去一样被原封不动地送回来。您从来都不知道,先生,他从不允许任何人把他带到户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经历了无数可怕的事,想起来都会颤抖得像一片树叶。他会大发脾气,克雷文医生都不敢承担强迫他的责任。嗯,先生,他发了一场最厉害的脾气之后,事情毫无先兆——没过多久,他突然要求每天被抬出去,同伴只有玛丽小姐和苏珊·索比的儿子迪康,他能推动轮椅,还带着自己驯服的动物。科林少爷似乎迷上了玛丽小姐和迪康,还有,先生,如今,他在户外一待就是一整天。”
“他的身体看起来怎样?”
“如果他的饮食正常,先生,您一定会认为他在长肉,但我们觉得可能是浮肿。现在,他始终和玛丽小姐单独在一起,有时发出奇怪的笑声,要知道,他以前从来不笑。如果您允许,克雷文医生会立刻来见您,他这辈子从来没有觉得如此困惑。”
“那么现在,科林少爷在哪里?”
“先生,他在花园里,他总是在那,不过,他不允许任何人靠近,因为他说讨厌被人看见。”
克雷文先生几乎没有听见最后一句话,他打发走梅德洛克太太之后,便一直站着重复前面的那句话——“在花园里!在花园里!”
他费了很大力气才将自己的思绪拉回来,当他觉得重新回到现实中时,便转身离开了房间。他走的路线和玛丽寻找的一样,穿过灌木丛是月桂和喷泉花床,里面的喷泉正在喷水,花床则遍布着鲜艳的秋季花卉。他穿过草地拐进常春藤墙边的那条小径。他走得很慢,眼睛不断地盯着路面,他觉得自己仿佛被拉回了久久寻觅的地方,但他不明白是什么原因将自己带回来的。随着一步步地靠近,他的脚步反而变得更慢,尽管围墙上覆盖着浓密的常春藤,但他依然清楚地知道门的位置,不过,他无法确定那把埋藏的钥匙在何处。于是他停下来环顾四周,几乎在同一时刻,他似乎听见了一些动静,不禁蓦然一动,疑惑自己是否置身于梦境之中。
虽然常春藤依然挂在门上,钥匙依然藏在灌木丛下,这道门已经寂寞了10年,因为没有人走过。但是,花园里有声音,是奔跑的脚步声,好像在追赶着,还有奇怪的压抑的惊叫声,以及捂紧嘴巴的欢乐呼喊,听上去宛如孩子们不可抑制的欢笑。似乎他们想尽量不被别人听到,但过一会儿就会爆发,因为累积的兴奋实在无法压抑。看在上帝的份上,他听见了什么啊?他是不是在做梦?它是否来自于那个遥远清澈的声音?或者他得了失心疯,以为自己听见了其他人听不见的声音?
接着,那个难以控制的时刻到了。那些声音忘记了要安静,他们朝着花园门口跑过来,脚步声越来越快——克雷文先生听见一个急速、有力、年轻的声音无法自抑地爆发出一阵奔放的笑声——墙上的门被使劲儿推开,常春藤荡回两边,一个男孩全速穿过它冲过来,他没有看见这个外来者——克雷文先生,差一点扑进他的怀里。
克雷文先生担心他因为粗心大意撞上了自己而跌倒,于是他赶紧伸出双臂。当他松开手时,便真正停止了呼吸,这是个高高的、英俊的男孩子,因为奔跑而显得生气勃勃的脸颊上有一层鲜亮的颜色,他甩开前额上浓密的头发,露出一双奇怪的灰色大眼睛,里面洋溢着欢笑,黑而长的睫毛好像流苏一样。
正是这双眼睛让克雷文医生停住了呼吸,他结结巴巴地问:“你是谁?到底是谁?”
这种相逢绝对出乎科林的预料,这不是他的计划。他和玛丽一起赛跑,本来他认为,也许冲出去赢得一场比赛更好,但现在,他只有努力让自己显得更高。玛丽也冲出大门,眼前的情景让她相信,科林现在比任何时候都要高,甚至高了好几英寸。
他说:“爸爸,我是科林,你是不是不敢相信?连我自己都没法相信,我是科林啊!”
克雷文先生完全糊涂了,他只是说着:“在花园里!在花园里!”
科林赶紧解释:“是的,正是花园起了作用,还有玛丽、迪康和他的动物们,当然还有魔法。没有人知道这些秘密,我一直保留着,打算等你回来后再告诉你。现在,我完全好了,赛跑能超过玛丽,我要当个运动员。”
科林说话时完全像一个健康的孩子——涨红的脸,因为急切而说得颠三倒四的词句,克雷文先生的灵魂开始颤抖,他难以置信地感到快乐。
科林伸出手放在父亲的胳膊上说:“您难道不高兴吗,爸爸?难道您不高兴吗?我要活到永远的永远!”
克雷文先生抱着男孩的肩膀一动不动,因为他知道自己有一阵不敢开口说话。终于,他说:“我的孩子,带我去花园,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
于是,孩子们带着他进去了。
这里是秋色狂欢的海洋,充满了金色、紫色、蓝色和火焰一般的红色,每一侧都有不同颜色的晚百合,白色或白红相间。他清楚地记得第一丛百合种植的时间,每到一年中的这个季节,它们才开始展现出迟到的光彩。垂挂的玫瑰汇聚成数不清的串儿,阳光将树木的黄色染得更深,仿佛让人觉得置身于一个黄金庙宇中。新来者安静地站着,不停地环顾四周,就像孩子们刚刚进入花园时一样,那时这里是一片灰色。
他说:“我以为它们已经死了!”
科林说:“玛丽原先也这么认为,但是它们都活了。”
接着,他们全部坐在树下,只有科林站着讲故事。
阿奇博尔德·克雷文心想:这是自己听过的最奇怪的故事。科林用男孩的风格将整个故事任意地、滔滔不绝地倒出来。春天来临、野生动物、古怪的半夜相逢、被侮辱的小王爷出于自尊而站立、当面驳斥本·威瑟斯达夫、奇特的玩伴、当演员、小心保护的大秘密,以及神秘的魔法,听者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当然,他不笑的时候也会流泪。这个可笑又可爱的演说家、科学发现者、运动员是一个完全健康的年轻生命。
最后,他在结束故事时说:“现在,我们不必再保守秘密了。我敢保证,他们看见我之后会吓得昏倒,但我再也不坐那个轮椅了。爸爸,我要和你一起走回去,走回房间。”
虽然尽职尽责的本·威瑟斯达夫很少离开花园,但这次,他编了个运蔬菜去厨房的借口,结果被梅德洛克太太请到仆人大厅里喝啤酒,因为她知道本·威瑟斯达夫刚从花园过来。就像他所希望的那样,当米瑟威斯特庄园的这一代所经历的传奇事件上演时,他正好在场。梅德洛克太太希望,他正好瞅见了主人,甚至正好看见父子相逢的情形。
于是她问:“本·威瑟斯达夫,你有没有看见他们?”
本·威瑟斯达夫拿开啤酒杯,用手背抹了抹嘴唇,用狡猾而意味深长的口吻说:“是啊,我看见了。”
梅德洛克太太试探地问:“两个人都看见吗?”
“是的,两个人都看见了。多谢你,夫人,我能再喝一杯吗?”
梅德洛克太太一边将他的啤酒杯灌满,一边兴奋地问:“同时看见的?”
本·威瑟斯达夫一口喝掉半杯酒说:“是的,夫人。”
“科林少爷在哪儿?他的情形看上去如何?他们说了些什么?”
“这我倒没听见,因为我仅仅是爬在梯子上从墙头看。不过我可以告诉你,外面一直在发生事情,但房子里的人完全不知道。你很快就会知道这些想了解的事。”
不到两分钟他便吞下了最后一滴啤酒,接着便冲着露出草地的那个窗户严肃地挥了挥杯子:“瞧那儿,如果你很好奇,不妨去看看是谁过来了。”梅德洛克太太过去看了一眼,立刻高举着双手尖叫了一声,其他听到声音的仆人们也冲出仆人大厅站在窗前,他们的眼珠子都快掉到地上了。
穿过草地走过来的是米瑟威斯特庄园的主人,仆人们从来没见过他这副样子,他的身边是一个高昂着头、满脸笑容、走得很稳当的科林少爷,他和其他约克郡男孩一样强壮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