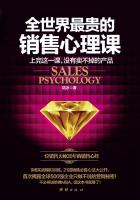在夜晚的阳台上,当我独自面对这炼油厂的火炬,面对这熊熊大火,燃烧的气体以及被火光照得通红的夜空,我感到一种现代城市人生存的那种虚空,巨大的虚空。在更多的夜晚,在我生活的这座长江北岸的化工城市,我无法仰望星空,我被那烈焰冲天的大火炬所钳制、制服。我一个人待在阳台上时,我的手指缝里往往夹着半支香烟,当我沉思这炼油厂的火炬,我的手被慢慢燃到尽头的烟头所烫痛。我们都喜欢燃烧,抽烟也是如此,在我看来,一个孤独的站在阳台上抽烟的人,他抽烟,实际上是需要指缝间有一点火光在黑暗中亮着。他蹲在那里,水泥地上,黑漆漆的夜色中,他不断地吸亮烟头,烟头所制造的那么一丁点儿亮光和他身体的一团黑影形成一种反衬和对比。
我在梦中梦见的那么多的失火的场景肯定都和这炼油厂的火炬有关。我曾经梦见过很多失火的事物,我出生的老房子,一座大学的旧红楼,江边的木制茶楼,它们都曾经在我的梦中突然失火,冲天的大火和呼天抢地的救火人群使我在梦醒后很长时间都不能安定下来。我一直以为我们的苦痛不仅来自现实生活中,也来自我们的梦中。在夜里我们做着失火的噩梦,在白天我们则神情恍惚,更像是一种梦游。
我知道,在炼油厂的火炬下方,是烟雾笼罩的厂区,是数不清的巨大的储油罐、炼化塔、大肠般的输油管道。我有一次在傍晚到郊外去,独自穿过炼油厂的厂区,蒸汽的轰鸣声和盘根错节的管道使我仿佛置身于一个奇境。人在巨大的机器和装置面前肯定会产生一种原始的恐惧,到一个异地去也是如此。我所生活的这个城市的炼油厂占据着的那片区域就是一个异地,我一踏入就感到陌生和恐惧的异地。并且我也知道,在我生活的这个城市里,肯定还有一些地方我至今没有去过,甚至我一辈子都不可能踏入。
但这炼油厂不分昼夜熊熊燃烧的大火炬人人都可以看得见,人人都可以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在无聊时独自走来走去的楼顶上,在厌倦了房间生活的阳台上仰望它。就是这样,望一望它,然后人们继续埋头去过自己的生活。其实也只能这样,谁也没有办法叫它烧得更猛烈些,或者悄然熄灭。这阳具,这铁管子,这喷火的恶魔,对于炼油厂的火炬,我所生活的这个城市的人有着各种各样的叫法,他们恶狠狠地,轻描淡写地,无所谓地称呼着它。人们习惯了炼油厂的火炬,习惯了烟雾笼罩的阴霾天气,习惯了这个有很多管道穿越的城市。人们所过的这种习惯的生活,我们称之为日子。
筒子楼
筒子楼就像一节黑暗的车厢,停留在我的记忆深处。但我这么说,并不意味着筒子楼没有光亮,相反,筒子楼里的光亮是我所见到的建筑物里最耀眼的光亮。那光亮不时地刺得我的眼睛发疼--甚至当我在纸上写下“筒子楼就像一节黑暗的车厢”这个句子时。
我回忆筒子楼时的情绪总是懒懒的,迂回的,漫不经心的。对于筒子楼的回忆和对于其他一些东西的回忆是一样的,都要陷入一种黑暗之中,但完全黑了是不行的,必须要有光亮,而筒子楼就拥有这种令人目眩的光亮。那些光亮是门的形状,门打开了,它们就斜斜地打在长长的黑漆漆的走廊上。我已经无法记清楚那些门洞里发生的所有的人和事,当我命令自己努力去回忆那些人和事时,我的思绪就像那些阴暗的房间里挂满的湿衣服一样凌乱不堪。偶尔,有一两个鲜艳的女大学生从筒子楼里穿过,使得我的记忆能够保持一丝鲜活。
一篇好文章是需要一个好的开头的,我自以为我为这些文字找到了一个好开头,但我现在觉得自己已经无法再顺着“筒子楼就像一节黑暗的车厢”写下去。有时候,光亮被挡住了,筒子楼里不时传来沉重的脚步声--这是我为这篇文字另起的一个开头。回忆某物根本不同于写某物,你不能违反回忆的规则。我回忆筒子楼时的情绪总是懒懒的,有时我甚至把自己当成了筒子楼里那个画画的男人。我想,我是被筒子楼的记忆阴影笼罩得太深了。
我知道,我有时慵懒的情绪很可能是受了那个男人的感染。慵懒就像一种病,有时也在我身上悄然发作。我只要一回忆那个男人,他便会躺在床上,抽着一两支烟,抬头望着它那幅尚未完成的油画,旁边总有一个默不作声的女人在过道里的煤炉上烧饭。这种场景给我一种无声的感染。随着时间的增长,这种场景慢慢具有了一种油画的质地,它幽暗、明亮,纹理清晰。一个搞艺术的人--有人这么称呼这个住在筒子楼里的男人。我不喜欢“搞艺术”这种说法,因为它太过于通俗、直截了当。我一直就认为一幅优秀的油画应该具有一种弥漫感,那是一种淹没观众的欣快感,一种沉醉。我对于这筒子楼的回忆包括那个男人画的几幅油画。我描述它们时,总是先说到“门打开了,门洞里泻出了刺目的光亮”。
好的电影应该是在电影院里观看的,四周一片漆黑,只有一道光束笔直地射在银幕上。我喜欢《阳光灿烂的日子》这部挽歌式的电影,但我从不喜欢记住这部电影的故事情节,甚至有时弄不清电影里主人公的名字,因此很多人据此认为我是一个经常在电影院里睡觉的人。我小时候在一个戏校的垃圾场里捡到过一些残缺的电影胶片,我把它们拿回家,用手电筒在墙上一张张地照着看它们,它们每一张几乎都是相同的画面,但它们每一张都有细微的差别。而现在,真正的电影开始了,一张张胶片运动了起来,四周一片漆黑。
我可能永远是那种只对细节和片段感兴趣的人。对于《阳光灿烂的日子》这部电影,我只记住了一幢旧楼和一座废弃的高大的烟囱。我的目光和摄影机同时长久地停留在一片陈旧而美丽的屋顶上,那屋顶从电影里冒了出来,如果我愿意,我一纵身就能跳到屋顶上,像一只猫那样在上面走来走去。我认为这是一部将屋顶拍到极致的电影。有时我觉得自己就是那个在屋顶上走动的人,无处可去。
但没有一个人能够一直生活在屋顶上。屋顶庇护着我们,我们寻找到适合自己居住的房子,在那些房子里制造某种气氛和味道,光线昏暗或者明亮。而门在这时打开了,门洞里泻出了夺目的光亮。很长一段时间,我就像回忆一场电影那样返回到筒子楼的场景里:我走过一条长长的没有尽头的走廊,只有光亮,没有尽头。在筒子楼里,我体验着穿越一个又一个门洞的快感。
同屋顶的干净和简洁相比,筒子楼里太凌乱了,堆满了各种杂物。我行走着,有时会一脚踢在煤灰上,我真担心那是一只猫。继续走,继续踢下去继续撞下去,前面越来越亮了。“门洞打开了”,我毫不犹豫地进去了吗?我究竟是在某个画展还是在筒子楼里看到那些水汽氤氲的油画的?多少年后,我向你们所描述的梦境就是那其中一幅画的内容吗?那个热衷于画自己梦境和潜意识的男人一直在筒子楼里蜷缩着,他开门,我们就有亮光。
实际上,筒子楼已经真的像一节车厢那样走远了,没有火车的那种哐啷哐啷声。写作有时令我苦恼,一些东西我一写出来就变旧了,就属于过去了。被我写出来的筒子楼在一瞬间变得更旧了,它灰灰的,爬满了有藤蔓的植物。而筒子楼越拆越少了,它的狭窄、封闭和黑暗注定了它将被封存进一些人的回忆。而想要回忆筒子楼,我在这篇文字的开头就已经说过了,先要陷入黑暗之中,然后在一种慵懒的情绪里回忆那夺目的光亮。
站在天桥上
傍晚,我高高地站在这个城市唯一的一座天桥上。我是个爱闲逛的人,但这次我却不打算到街的对面去,我只走完了这座天桥的一半。我停在它的中央。这座钢筋混凝土制造的叫做“桥”的建筑物就在我的脚下。在我的脚下有川流不息的车辆、人群和平坦无比的柏油马路,它们也在这座天桥下。天桥下面没有水,没有河流的桥才叫“天桥”?这个和往日一样平淡的傍晚,我站在天桥上,感觉到下面的一切都在如水一般地流淌。
流淌,速度使车辆和人群流淌。在这座宽阔的天桥下面,我看见了时间和速度。面对一辆卡车、一辆自行车和一个孤独的散步者,我不能虚妄地判断他们速度的快慢,我只能对自己说: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速度里。我静止地站在天桥上,并未来回走动,我有没有速度呢?在这个白昼即将消逝的黄昏,我强烈地感受到了正在我脚下前进的速度。这时,一个骑童车的孩子从下面经过,他不知道什么是速度,时间对于他来说是一块表发出来的动听的滴答声。然而,他也在以自己浑然不觉的速度慢慢地前进着。在这座不能称为“伟大”的天桥下,我看不到一个倒退着走路的人。
在这座高大的天桥上,我什么也不做,我两手空空,我是一个纯粹的观望者。有的人并不看风景,他们三三两两地来到天桥上,似乎在等待什么。约会发生在过去,约会要求他们现在去等待。漫长的等待,他们当中总有人不耐烦地走开,那些人不习惯于等待。但也有人会等到天黑。我在天桥下看见了一个熟人,我现在居高临下地看见的是他的双肩和头顶,这是我们平时在林阴道上相遇时所无法看见的,视角的改变竟使他在我的眼里变得陌生!我没和他打招呼,他不是我所要等待的人。其实我什么人也不等待,我是一个纯粹的看风景的人。
在这座静止的天桥上,除了一直没有走动的我,还有几位下棋的老人。在他们看来,天桥只是一个地点,适于安心下棋消磨时光的地点。他们的这种行为取消了天桥作为一种交通途径的概念。他们晚年中的一部分时间将在天桥上度过。我是个不会下棋的人,但知道作为一个非常投入的弈棋者是绝对不会感受到这桥底发生的一切,他们甚至连近在身边的吵闹也不会发觉。此刻,一辆白色救护车从桥下呼啸而过,在我的瞳仁里消失成一个醒目的白点。呼啸的救护车与平静的弈棋者,我知道他们形成不了相互的干扰。
奔跑者在道路上继续奔跑,我在暮色中的天桥上继续眺望。我知道这时候有很多人在急着回家,他们惧怕夜晚?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们承受不住劳累一天后的疲乏。累,平静的眺望也使我感觉到了累。我的脖颈有些酸疼,累只是一种又酸又疼的感觉?然而,累是不会降临道路的,对于道路上的石子和沙粒而言,从没有什么“累”,只有“粉碎”。人群和车辆的奔驰使它们粉碎,成为挡风玻璃上的浮尘。灰尘与累,它们有着一种无奈的相似。
我无法抗拒累,但我仍旧不愿走开。在这座坚固的天桥下,有很多事物正在走开。一辆长途客车在下面一晃而过,里面装满了去外省的乘客,他们离开这座城市需要几个小时,而他们离开我和这座天桥只需一瞬!我是个热爱步行的人,这说明了我的一生不能离开多少事物。然而就这一瞬,在那辆满是尘土的长途客车里,肯定有人看见了我和这座造型并不怎么特别的天桥。在终点,他们会把旅途中经历的一切全部忘记?
能够被别人回忆就是一种幸福。站在钢筋混凝土的天桥上,我想象着自己可能会被某一个人不断地纪念、想起。于是,我享受到一种非常遥远的幸福,提前到达的幸福。在这座不很美丽的天桥上,我为自己制造了一次眩晕的幸福。这很真实。这个美妙的黄昏很真实,真实的一切很真实!我站在天桥的中央,白昼和黑夜就要交替,我想:这座天桥会连同它周围所有的一切沉入夜色。在黑暗中,该进行的一切仍需进行。
在天空尚未完全黑下来之时,我要回去。在这个城市唯一的一座天桥上,什么也没有发生。我不打算到街的对面去,我是从哪儿来的,还会回到哪儿去。
6号码头
我来到6号码头的时候,一艘客轮正好靠岸。在喧闹的人群中,我默默地走了一阵子。我并不想成为一个乘客,在这些抵达了码头兴奋的人群中,我是唯一一个默默行走的人。我的方向是奔向码头,而这些经历了漫长的旅途而变得分外沉重的人,他们的方向是进入高楼耸立的城市。我行走着,风吹动着我的风衣。一个个陌生的乘客与我擦肩而过,我回头看了一眼他们肩上的行李。我到6号码头并不是来接人的,我只是想看看江、听一听风声。但是我一到6号码头,就有一艘客轮停了岸,一大群疲倦的旅客走下了客船。我没有听见汽笛的声音,难道这艘客轮是在悄无声息中靠了岸?这不可能。我竭力思索这艘客轮鸣响汽笛时我正在干些什么。然而,我的记忆一片空白。我只能肯定:当时我正走在去码头的路上。
我朝着大家相反的方向走着。在这群经历了漫长的漂泊的乘客中,没有一个可以与我握手的人。我沉默无声地朝6号码头走着,在我和一只大铁锚的距离中间,是一大群喧闹的旅人。在我的身后,有人发出了幸福的啜泣声。我停了一下,但没有回头。我知道那一定是一个人终于等到了另一个人。我想到了“久别重逢”这个词。我想此刻,有两个久别重逢的人正紧紧拥抱在一起,他们共同发出了幸福的啜泣声。在6号码头,我发现了很多没有情节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