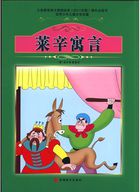堂吉诃德叫喊的声音很高,店主急忙打开大门想出去看看是谁在吵吵,后来的那几个人也跟着凑了过去。马里托尔内丝也已经被惊醒。她一下子就想到了是怎么回事,于是蹑手蹑脚地去到草仓松开了拴着堂吉诃德的驴缰。店主和那些来人瞧见堂吉诃德猛地跌到了地上,马上走上前去问他为什么那么大呼小叫。他一言不发,解下手腕上的缰绳,站起身来,爬上若昔难得,挽着盾牌,端起长矛,跑出一段距离之后重又掉转了马头款步跑了回来,边跑边说道:
“甭管什么人敢说我活该中邪,只要米壳米空公主殿下批准,我定将揭穿他的谎言并约他决斗。”
到场人被堂吉诃德的话搞得不知道怎么回事,不过,店主对他们讲了他是什么人并要他们别去理他,因为他头脑有点问题。来人向店主打听是否有个十四五岁的少年来店投宿。他们说他假装成骡夫并描述了他的外貌,这一切跟克拉拉小姐的情人的情形没有区别。店主说客栈里住了那么多人,未曾注意有没有他们说到的那个孩子。这时候,他们中有人看到了法官乘坐的马车,于是说道:
“可以肯定,就在这儿,这就是人们说他紧跟不放的那辆马车:留下一个人把住大门,其他的进去找,最好再有个人在客栈外面巡逻,别让他跃过墙头跑掉。”
“好吧,”有人应道。
两个人走进了客栈,一个人留在了门边,一个人围着客栈转了起来。
这时候,天色已经全亮,再加上堂吉诃德的吵闹,店里的人全都醒了并接连起了床,特别是堂娜克拉拉和多罗特娅,一个因为挂念着近在眼前的情人、一个迫切想要见到那个小伙子,整整一个晚上都没能睡得踏实。
堂吉诃德见来人既不理他、也不应战,十分生气。来人最后发现那个少年就睡在一个年轻骡夫身边,根本没有想到会有人来找,更不用说是被人找到了。那人抓住他的胳膊说道:
“堂路易斯少爷,您的母亲对您娇生惯养了一场,您竟然这样一身打扮、睡起了这种床铺啊。”
那小伙子揉了揉惺忪的眼睛,瞅了瞅揪着自己的人,认出了他是父亲的仆人,刹时一惊,长时间没能说出话来。那仆人又说道:
“堂路易斯少爷,您就甭打别的主意了,老老实实地回家,否则,就是想要逼迫您的父亲、我的老爷去死,因为您的出走让他老悲痛欲绝。”
“我父亲怎么会晓得我走这条路、这身打扮?”堂路易斯问道。
“您把自己的计划告诉给了一个同学,”仆人说,“他看到您父亲思念您时的悲伤样子,一时心软就说了出来。您父亲派我们四个出来找您,我们全都听您差遣。这么顺利就能将引到那么爱您的人的面前,实在是让我们太高兴了。”
“那得看我愿不愿意和老天是什么意思喽,”堂路易斯说。
“除了回家,您还能想怎么样?只能如此。”
听到了他们的谈话,和堂路易斯在一起的那个年轻骡夫就起身跑去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给了堂费尔南多、卡尔德尼奥以及其他,对他们说,那些人叫那小伙子为“堂”,双方争吵不休,那些人想带小伙子回家,可是他却坚决不同意。
人们已经领略了年轻人那得天独厚的噪音,得知这一情形之后,就更想知道他到底是谁了,而且,如果那些人想要强迫他的话,甚至也愿意助一臂之力,所以,他们就一起走了过去而且看到那小伙子还在跟仆人对峙着。
此时,多罗特娅走出了房间,堂娜克拉拉慌张地紧跟着。多罗特娅将卡尔德尼奥拉到一边,简要地对他讲了那位年轻歌手和堂娜克拉拉的故事;卡尔德尼奥也对多罗特娅说了小伙子的家人前来找他的事情,由于讲得声音挺大,堂娜克拉拉听得很清楚,结果,差点儿就摔到地上去了。卡尔德尼奥让她们赶紧回到屋里去,让他去想主意。两位小姐听从了他的劝告。
前来寻找堂路易斯的四个人都已进了客栈。他们围着他劝他立刻回家去抚慰他的父亲。堂路易斯却说,不把那件事办完,决难从命。那几个仆人也不让一步,表示决不空回,不管他愿意还是不愿意,都要把他带走。
“你们妄想,”堂路易斯说道,“除非是带着我的尸首。假如你们来硬的,我就不活了。”
正在这么对峙着的时候,店里的大多数客人都已经围了过去。业已了解那青年的来历的卡尔德尼奥问那些准备将他带走的人,是什么原因一定要强迫他回家不可。
“我们是想救他父亲一命,”来人中的一位答复说,“少爷的出走使老人家悲痛欲绝。”
堂路易斯随即说道:
“谁也管不着我,愿意回去的时候,我一定会回去;不愿意回去,谁也不能强逼。”
“您有您的道理,”来人说道,“假如跟您说不通,我们就有理由履行职责。”
“各位请说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法官插言道。
“法官大人,这位是您的邻居的儿子,您已经瞧见了,他穿着跟自己的身份完全不符的衣服离家出走,您难道没有看出来?”
法官于是认真端详了一番,最后认了出来,接着将他搂在怀里说道:
“堂路易斯先生,这套衣服跟您的身份太不般配了。您打扮成这个模样,耍的是什么花招或者有什么难言的苦衷?”
那年轻人登时泪如泉涌,哽咽着。他拉着堂路易斯的手将他带到一边问他究竟是怎么回事。就在他们两个叨咕的时候,两个在店里过夜的客人想不付店钱就逃走,可是,店主在门口揪住了他们,要他们付钱,他们就对他挥起了拳头,可怜的店主于是大声呼救。老板娘和她的女儿一看只有堂吉诃德有空儿可以帮忙,那姑娘就对他说道:
“骑士老爷,您是个大好人,快去帮我父亲一把吧,有两个家伙正在拼命地打他呢。”
对她的请求,堂吉诃德从容不迫地说道:
“美丽的小姐啊,您的请求不是时候,我已经答应为别人做事了,事情未完成之前不能节外生枝。不过,为了能够帮您,咱们先这样吧:您快跑过去告诉您的父亲,先尽可能地顶着、绝对不可认输,同时,我去乞求米赤米空公主批准我前往帮忙,只要公主发话,我肯定会救他脱险。”
“别怪我多嘴!”马里托尔内丝插言道,“等不到您讨得那份恩准,我家老爷也就没命了。”
“小姐,您就让我去讨取那份批准吧,”堂吉诃德说,“只要得到了批准,即使他死了也没什么关系,我肯定强行将他再从天上请回来;假如不这样,我就狠狠地惩罚那些打发他归天的家伙们,这样一来,您多少也能消消气。”
堂吉诃德说完就去跪到了多罗特娅的面前,恳请公主殿下恩准他前去搭救大难罗身的城堡主公。公主欣然同意,他于是立刻挽盾操剑直奔两位客人还在死命殴打店主的门口而去。但是,他到了那里以后却又束手而立,全然就不理会急于救父和救夫的马里托尔内丝和老板娘的催促。
“我不动手,”堂吉诃德说道,“是因为我与他们级别不同,不过,你们把我的侍从桑丘叫到这儿来,这场助弱伐强之战理当由他担当。”
在客栈门口,只见拳起脚落,拳拳脚脚全都落在店主的身上;马里托尔内丝、老板娘和她的女儿眼睁睁看着主子、丈夫和父亲大吃苦头又气又急,深深痛恨堂吉诃德胆小怕事。咱们还是退到五十步以外去瞧瞧堂路易斯是怎么回答法官的吧,适才说过了,法官问他为什么那么衣衫不禁地徒步去到了那个地方。
那年轻人用力地攥着法官的双手,痛哭流泪说道:
“尊敬的先生,我只能对您讲实话了:苍天有意和邻居之便使我有幸见到了您的女儿——我的心上人堂娜克拉拉小姐,从见到了她的那一刻起,我就把自己的心完全交给了她,如果您愿意,我今天就可以娶她为妻。我因为她而离家出走、因为她而如此打扮,为的是能跟随她走遍天下。她并不知道我的心意,顶多不过是有几次远远地看到我哭泣罢了。先生,您了解我父母的财力和家世、也知道我是他们惟一的儿子,假如您觉得这一切完全能让您成全我的幸福,那就请您马上同意我做您的儿子吧;如果家父因为另有打算而不喜欢我为自己打造的幸福,时光比人心更能使事态改观和发生变化。”
痴情少年说到这儿就停住了,而法官却惶惑、错愕和惊讶不已:一是有感于堂路易斯畅所欲言的方式和智慧;二是不知道应该如何面对这件突如降临的事情。法官一时间什么都没说,只是让那少年先放下心来,想办法拖住那几个仆人当天别走,以便能有充足的时间想出一个周全的计策。堂路易斯强行亲吻了法官的双手,甚至还在那手上流下了不少眼泪。那情景完全会使铁石心肠也会感动,更不要说是法官了,其实他是个聪明人,完全知那门亲事对自己的女儿该有多么美满。他还知道堂路易斯的父亲正在为儿子谋求爵位,假如可能,他很希望那位老人能够承认这桩婚姻。
这时候,两位客人和店主业已讲和。这得归功于堂吉诃德,此次他没有威胁吓唬,而是摆事实、讲道理,竟然让那两个客人如数交了店钱。与此同时,堂路易斯的几个仆人在等着主子跟法官谈话的结果和他的最后决定。然而,祸不单行,被堂吉诃德抢了曼博里诺头盔、又被桑丘·潘萨换过驴具的那位理发师刚好在这个关键时刻来到了这家客栈。那理发师将自己的毛驴牵进牲口棚的时候,碰到了正在那儿整理鞍子的桑丘·潘萨并一眼就认了出来,于是,立刻扑上前去说道:
“好啊,你个贼坯子,可让我抓住了!抢了我的铜盆和我的鞍具,赶快交出来!”
桑丘看到忽然有人连声叫骂地朝自己扑了过来,一只手抓起鞍子,另一只手攥成拳对着理发师的脸上就是一下子,打得人家立刻嘴角出血。可是,那理发师并没有松开已经抓到手里了的驴鞍,而且还大喊大叫,使得客栈里的人全都闻声赶来,只听他说道:
“这个拦路强盗抢了我的东西,还想杀人!”
“胡说,”桑丘驳斥道,“我不是拦路强盗,这些都是我家主人的战利品。”
看到自己的侍从能进能退,堂吉诃德暗自高兴,觉得从此以后应该把他当个人物,暗自决定找机会册封他为骑士,相信他不会称职的。那位理发师还在不停地数落着,只听他说道:
“诸位先生们,这鞍子是我的,我认得。我的毛驴就在牲口棚里,不允许我胡说,不信的话,各位可以试嘛,如有半点儿不配,算我耍赖。还有呢,抢了我的驴鞍那天,还夺走了我的一个崭新的铜盆。”
这时候,堂吉诃德不禁想要讲话了。他站在两人之间并将他们分开,然后又把驴鞍放到了地上,很明显是想要对事实加以澄清。他说道:
“我想请诸位先生认真看清这位老实侍从的荒谬,因为,他所说的铜盆,却是曼博里诺头盔,我经过公平的交战从他手中夺了过来,属我所有合理合法。至于驴鞍嘛,我不搀和,不过,我要说的是,我的侍从桑丘请求我允许他用这位败北的懦夫的马鞍装备自己的坐骑,我批准了,他也就更换了。至于怎么又从马鞍变成了驴鞍,我只能说这很正常,作为证明,桑丘,伙计,赶快去把这位老实人说成是铜盆的头盔拿到这儿来。”
“算了吧,老爷,”桑丘说道,“除了您说的话,咱们哪有什么证据啊,马里诺头盔本原来就是铜盆,这位老实人的马鞍本来就是驴鞍嘛!”
“照我说的去做,”堂吉诃德说。
桑丘跑去拿来了铜盆,堂吉诃德随即接了过去说道:
“诸位请看,这位侍从还怎么恬不知耻说这是铜盆而不是我说的头盔呢。这就是我从他手里夺得的那个头盔,原封未动。”
“这倒是无可置疑的,”桑丘接茬说道,“因为,从得到它之后,我家老爷只戴着它经历过一次战斗,就是解救那些囚犯那回,若是没有这个头盔盆儿,他可就受伤了,当时那石头块儿就像下雨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