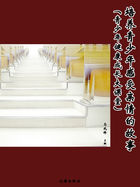“你说钻了8英里?”我叫起来,“你是否知道5000英尺已几乎被认为是打井的极限了?”
“我完全知道这个极限。这个问题不用你管。我只要求你准备好一根钻杆,越锋利越好,长度不超过100英尺。在我们大功告成之前,你的性命就维系于这根远距离操作的钻杆上了。”
“那么,我将要钻透的是什么土壤呢?”我问。
“姑且说是一种胶状物质吧。”查林杰说,“现在,你可以找我的工程总负责人签定合同了。”
我鞠了一个躬转身出来,可是没到门口,好奇心又留住了我,我忍不住问他:“先生,这个非同寻常的实验的目的是什么?”
“走吧,快走!”他愤愤地叫嚷起来。他低下头去,他的一大把胡须戳到纸上弯成弓形,叫你分不清哪是头哪是胡须。就这样,我离开了这个怪人。
我回到我的办公室,看见马龙正在那儿等着我,要听听我这次会晤的消息。
“喂,”他嚷道,“他没有打人吧?你对他一定应付得很策略,你觉得这位老先生怎么样?”
“是我碰到过的人中最令人讨厌、最盛气凌人、最偏执和最自负的了。但是……”
“说得好,”马龙叫道,“说到后来,我们都有这个‘但是’,这个伟人不是我们能用尺子衡量的。因此,我们在其他人那里忍受不了的,在他那里就能忍受得了,对不对?”
“不过他说的话可靠吗?”我问。
“当然。”马龙说,“我可以向你担保亨吉斯特高地是一桩实实在在值得干的事业,而且也快竣工了。目前,你只需静观事态发展,同时把你的工具准备好,我会给你消息的。”
几个星期以后,马龙就给了我消息。“一切都弄好了,现在就瞧你的啦。”他说。于是,我们就动身了。在途中,他给了我一张查林杰写给我的纸条,上面写道:
皮尔里斯先生:
你一到亨吉斯特高地,就听从总工程师的调遣,他手里有我的施工方案。我们在14000英尺的井底见到的景象,完全证实了我对星体性质的看法。你乘缆车下去时,会依次经过二级白垩层、煤层组、泥盆纪和寒武地层,最后到花岗石岩层。目前,在井底覆盖着防水油布,我命令你不得乱动。因为毛手毛脚地碰地球的表层会使实验流产。按我的指示,在离井底20英尺处横架了两根结实的大梁,大梁之间留出空档夹住你的钻杆。钻杆的尖端要几乎触到防水油布。油布下的物质很软,将来只要把钻杆一松,它就可以把那物质戳穿。更多的情况,到亨吉斯特高地再说。
查林杰
经过一路颠簸,我们来到了亨吉斯特高地。这真是个神奇的地方,规模比我想象的要大得多。已从井中挖出了成千上万吨砂土和岩石,围着竖井堆成一个马蹄形的弃土堆,现在已变成相当规模的小山了。在马蹄形的凹处矗立着密密麻麻的铁柱和齿轮,操纵着抽水机和升降机;发电大楼后面是竖井口,直径有三四十英尺,井壁用砖头砌成,上面浇了水泥。我伸过头去看那可怕的深渊,感到头晕目眩。阳光斜射进井里,只能看见几百码内的白垩层。正当我打量的时候,发现在无比深邃的黑暗中,有一个小小的光斑,它在漆黑的背景中显得清清楚楚。
“那是什么光亮?”我问马龙。
“那是一架升降机上来了,”他说,“那道小小的闪光是一盏强大的弧光灯。它速度很快,几分钟就到这里了。”
确实,那针孔大的光越来越大,后来井里撒满了它的银辉。我不得不把眼睛从它眩目的强光中移开去。不一会儿,升降机蓦地落到平台上,4个人爬出来朝出口走去。
马龙把我领到一座小房子里。我们把衣服脱得一件不剩,先换上一套丝质的工作服,再穿上一双橡皮底的拖鞋。于是,我们在总工程师的陪同下踏进了钢网升降机,朝着地层深处疾冲而下。升降机高速运行,我们像是在做一次垂直的铁路旅行。
由于升降机是钢网围成,里外照得通明,我们对经过的地质层看得很清楚。在风驰电掣般下降时,我能认出每一层来:浅黄色的下白垩层,咖啡色的海斯汀层,淡色的阿什伯纳姆层,黑色的含碳粘土。再往下,在电灯光下闪烁的是交混在粘土圈中乌黑发亮的煤夹层。不少地方砌上了砖头,但总的来说,这竖井是靠自我来支撑的。对于如此浩大的工程和它体现的工艺技巧,人们不能不叹为观止。在煤层下面,我认出了外表像水泥的混杂层,然后很快来到原始花岗岩层。在那里,晶莹的石英石闪闪烁烁,似乎黑墙上点缀着金钢钻石粉末。我们下降、下降,不断地下降,降到人们从未到过的深度。古老的石头五颜六色,光怪陆离。我永远忘不了那玫瑰色长石地层,在我们强大的灯光下闪耀,表现出一种尘世上见不到的美。我们一级一级地往下降,换了一架又一架升降机,空气越来越闷热。后来,甚至连轻便的丝质衣服也穿不住了,汗水一直流进橡皮底的拖鞋里。正当我觉得无法忍受的时候,最后一级升降机停下来了,我们踏进掘进岩石井壁的圆形平台。我发觉马龙露出奇怪的疑惑神色,朝井壁四周打量。
“这玩意儿可鬼了!”总工程师说着,用手摸摸身边的岩石,把灯光凑上去,只见那东西莹莹有光,上面是一层奇异的黏糊糊的浮渣状物质。“在这井底下,一切都在哆嗦和颤抖,太新奇了!”
“我也见过井壁自己颤动,”马龙说,“上次朝岩石里凿孔,每敲打一下,井壁就似乎朝后一缩。老头的理论看来十分荒谬,但是在这儿,就不敢说了。”
“如果你看到防水油布下的东西,恐怕就更没有把握了。”总工程师说,“这井底下的岩石,凿上去简直像乳酪。教授吩咐我们把它盖上,不许乱动。”
“我们看一眼总可以吧。”
总工程师把反光灯朝下照,他伛下身子,拉起拴住油布一角的绳子,露出被覆盖的那种物质的表层,大约有6平方码左右。
多么不寻常的景象啊,简直惊心动魄!那物质略带灰色,油光发亮,像心脏那样一上一下慢慢地起伏着。这种起伏,一下子是看不出来的。给人的印象只是它表面上泛起微微涟漪,很有节奏,逐渐扩展到整个表面。这表面层本身也不是匀质的。而在它的下面,像隔着层毛玻璃似的,隐约可看到有不甚明亮略带白色的斑点或泡泡,形状大小各不相同。面对这一奇景,我们3人站在那儿看得着了迷。
“确实像个剥了皮的动物。”马龙轻轻说。
“我的老天,”我叫起来,“要让我用一把鱼叉刺进这畜牲的身体里去吗?”
“啊,”总工程师断然说,“要是老头坚持让我留在下面,我就辞职不干,太可怕啦!”
那灰色的表面突然向上隆起,像波浪一样,朝我们涌过来,然后又退下去,而且还继续出现像刚才那种隐隐约约的心脏搏动的样子。总工程师把油布盖好。
“看来这东西好像知道我们在这儿。”总工程师说,“是不是亮光对它有某种刺激?”
“那么,现在我的任务是什么呢?”我问。
“老头的意思,是要你把钻杆设法固定在这两根大梁之间。”
“好吧,从今天起我就接手这项工作。”我说。
可以想象,这是我在世界各大洲从事打井的历史中最奇特的一次经历了。查林杰教授坚持要远距离操作,他确实有道理,我一定得设计一种电力遥控的方法。我把一节钻管搬了下来,堆放在岩石平台上。然后把最下面的那一级升降机位置升高,好腾出地方来。我们把压铁挂在升降机下面的一个滑轮上,把钻杆伸下去,上端安一个杆头,最后又把拴压铁的绳子系在竖井壁上,一通电就会松脱下坠。在工作的时候我们特别小心,因为一不注意把工具掉到下面的防水油布上,就会产生难以预料的奇灾大祸。同时,四周的环境也叫我们骇惧不已。我们一次又一次看见井壁出现奇怪的颤抖,我触摸了一下,两手隐隐发麻。
完工后的第三天,查林杰教授向各方面发出了请柬。我们头天晚上就去井下对一切准备工作进行检查。钻孔器装好了,压铁调节好了,电气开关接通电流也很方便,可以在离竖井500码的地方操纵电气控制装置。
伟大的日子终于来临了。我爬上亨吉斯特高地,准备一览整个活动的全貌。整个世界似乎都在奔向亨吉斯特高地。极目望去,路上尽是密密麻麻的人群,汽车沿着小路颠簸驶来,把乘客送到大门口。只有持有入场券的少数人才有幸入内,其余大部分人只好分散加入到已经集结在山坡上的大量人群中去。
11点15分,一长串大客车把特邀贵宾从车站接到这里。查林杰教授站在贵宾专用围地旁边,身穿大礼服和白背心,头戴亮堂堂的大礼帽,浑身上下光彩照人。他面部的表情,既有盛气凌人的威仪,又有令人讨厌的慈悲,还混杂着老子天下第一的神气。他被来客中的显贵们簇拥着,登上了一座居高临下的小山就了座。然后他就大着嗓门对着众多的观众大发了一通宏论,接着宣布实验马上开始。
我和马龙急急忙忙朝竖井跑去执行我们的任务。20分钟后,我们到了井底,掀开盖在表层上的防水油布。
我们眼前出现了一幅惊人的景象。这颗古老的星球凭借着神奇的宇宙心灵感应,好像知道要对它进行一次前所未有的冒犯,暴露的表层此刻像一只沸腾的锅子,巨大的灰色气泡冒起来,劈啪一声裂开。表层下的充气空间和液泡骚动不安,忽分忽合。面上微微横波,好像以更快更强的节奏左右摆动。一种紫黑色的液体似乎在表皮下蛛网般的血管里搏动。这一切都是生命在跳动。一股强烈的气味直呛人的肺部。
我正在全神贯注地看着这幅奇景,突然,我身边的马龙惊呼一声:“我的上帝,瞧那里!”
我瞥了一眼,立刻放掉电线,纵身跳进升降机。“快!”我叫道,“不知还能逃得了命不?”
我们看到的东西实在怵目惊心。竖井的整个下部,似乎和我们在井底看到的景象一样,也渐渐活动起来了。四周井壁以同样的节奏一张一驰地搏动着。这动作影响到搁置大梁的洞眼。很明显,只要井壁稍微再后缩一点——只消几英寸——大梁就会塌下来。这样,我们的钻杆尖刃不用通电就会戳进地球的内表皮。我和马龙必须在这以前逃出竖井,这是性命攸关的事情。在地下八英里深处,面临着随时可能发生的奇灾大祸,怎不叫人魂飞魄散。
我们俩谁也忘不了这次梦魇般的经历。升降机嗖嗖地朝上直飞,然而一分钟过得像一小时那么慢。每到一个平台,我们就一跃而出,再跳进另一架升降机,一按开关,又继续朝上飞驰。从升降机的钢格子顶上望去,可以看到遥远的上方有一个井口的小光点,它越变越大,渐渐成为一个完整的圆圈。我们兴奋地盯着那砖砌的井口,升降机不断地朝上飞升——欣喜若狂、谢天谢地的时刻终于来到了。我们从牢笼中跳出来,双脚重新踏上草地。真是千钧一发啊!我们还没有跑离竖井30步,安置在井下深处的铁标枪已经刺进大地母亲的神经结,伟大的时刻来到了。
究竟发生了什么,我和马龙都无法说清楚。两人好像被一股旋风卷倒在地,像冰球场上两颗滴溜溜打转的小球在草地上打着滚,同时传来一声从未听到过的震耳欲聋的怒吼。在这一声嗥叫里,有痛苦,有愤怒,有威胁,还夹杂着大自然的尊严受到凌辱的感情。由这一切汇集成的骇人的尖声厉叫,整整持续了1分钟之久,好像上千只汽笛齐鸣。这声音持久而凶猛,惊呆了天地万物,随着宁静的夏日空气飘向远方,最后回响在整个南海岸。历史上没有任何声音能和这地球受伤的痛叫声相比。
从地壳里最先喷出来的东西是升降机,总共14架,依次射出,在天空中翱翔着,组成一条蔚为奇观的抛物线。
接下来的是喷泉。这是一种具有沥青浓度的黏糊糊的脏东西,向上猛喷到约2000英尺的高空。在上空盘旋着看热闹的飞机好像被高射炮打中了似的被迫着了陆,飞机和人一起栽进污泥中。这种可怕的喷泉,奇臭刺鼻,好像是地球维持生命所必需的血液,否则就是一种保护性的黏液,大自然用它来保护大地母亲免受查林杰之流的侵犯。那些不幸的报界人士,由于正对着喷射线,被这种污物弄得浑身透湿,以致好几个星期都走不进社交场合;那股被喷出的污物被风吹向南方,降落在耐心地久坐在山顶上等着看好戏的人群头上。
再接下来是竖井自动闭合。如同一切自然伤口的愈合一样,总是由内及外,大地也以极快的速度,愈合它重要机体上的裂缝。竖井井壁合拢时,发出高亢持久的劈啪声,先从地下深处开始,越朝上声音越大,最后一声震耳巨响,洞口的砖砌建筑猛然坍下,互相撞击。同时,像小规模地震一样,大地颤抖着,把土堆也摇塌了,而曾经是竖井井口的地方,砾石断铁之类倒堆起一座高达50英尺的金字塔。查林杰教授的实验不但就此告终,它的遗迹还永远埋在人眼看不到的地下深处。
人们愣住了,久久不能作声,全场一片紧张的沉寂。随后人们恢复了神智,他们恍然悟到这是卓绝的成就,是宏伟的构思,是神奇的工程。他们不由自主地一齐朝查林杰望去,赞美声从每个角落传过来。从查林杰所在的山顶上往下一看,是一片昂起的人头的海洋。查林杰从椅子上站起来,左手贴着臀部,右手插进大礼服的胸襟里。照相机就像地里的蟋蟀一样,咔嚓咔嚓地响着。6月的阳光照在他身上,好像镀上一层金辉。他庄严地朝四面鞠躬致意。科学怪人查林杰,先驱领袖人物查林杰,他是人类中迫使大地母亲予以承认的第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