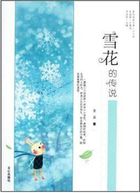8
一夜都没有睡踏实。他迷迷糊糊的,感觉在过去的岗位上夜班,机器在四周鼓噪。他想睡,又不敢睡着,沉沉的机声中似乎潜伏着某种危险。他拿起一根细长的铜听棒,戳在泵体上,倾听着单向阀敲击的声音。他在轰鸣声中巡回检查,看有无跑冒滴漏的地方……事故像野兽藏在暗处,虎视眈眈。他得提防它。记得,他曾经查获一个重大事故隐患,得到过一次奖励,奖金是一块钱。那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一块钱可吃四份红烧肉。突然,一个黑影从暗中蹿了出来,他知道,它就是事故,他瞪大了眼睛。可是它怎么是个人形呢?它张牙舞爪地向他扑了过来,他不知所措,惊慌之中只拿两只手掌遮住自己的脸……
天蒙蒙亮时他再也不想睡了,爬起床来,到宿舍区走了一圈。然后,他跑到山包上的一幢男工宿舍楼里。他来到自己住过的房间,站在门前发着愣。枣红色的门油漆斑驳,无声的关闭着,有一种拒绝的意味。难以想像,他在此住过八年,他最美好的青春时光,曾关在这扇不起眼的门里。他举手欲敲门,想想又作了罢。时辰还早,还是不要影响别人睡觉吧。无论如何,你的岁月已经流走了,你不属于这儿了。
他回到招待所,黄宇正在318房门前焦急地踱步,一瞟见他就说:“你跑到哪去了?赶紧收拾东西走吧!账我给你结了,火车票也给你买好了!”
他已打算离开了,但被黄宇这样催促,心里颇不是滋味。他默默地开了房门,默默地收拾自己的东西。
黄宇替他提着旅行箱,上了停在院子里的一辆桑塔纳。黄宇亲自开车送他。关上车门后,黄宇说:“你昨晚的事,我知道了。”
他瞟瞟黄宇说:“你早知道了吧?”
黄宇嘴边咧出一缕苦笑:“我晓得你会误会的,我怎会做这种事?”
“那哪种人会做这种事?”
“告诉你吧,有人在你这看到一份材料,就打了小报告,公司里有人担心你会介入,所以就……”
“这人是谁?”
“还能有谁?你那个好徒弟!”
他吃了一惊:“谢见屏?为什么?”
“也许为了邀功,以便改制时得到照顾;也许只为报复你。也许什么也不为。”
他哑口无言。黄宇开着车出了招待所。忽然,他看到前面马路边跑过来一些人,都是同班的工友。黄宇急忙说:“快,低下头!”他不明就里,望了望黄宇。黄宇赶紧摇上了车窗,说:“大家都听说你的事了,都是来看你的。别再见他们了,卷进去对谁都不好!”他默然,盯着车窗外,看着那些熟悉的面孔一晃而过,心里似乎有根筋被扯动了,隐隐作疼……
黄宇一直将他送进火车站候车室。告别时,黄宇抱歉地说:“很对不起,特殊时期,没招待好你不说,还让你遭遇了窝心的事……不过,你是作家,应当想得开的,就算你深入了一回生活吧。”
他说:“哪是我深入生活,是生活深入了我。”
黄宇拍拍他的肩:“管谁深入谁,有收获就行。哎,还记得当年我们老唱的那首歌么?‘再过二十年,我们再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
他说:“当然记得。”
黄宇说:“记得就好。你看,我们真的一别就是二十年,别再过二十年才来看我们呵,那样的话我只怕不在了呢!”
他眼睛发烫,不说话,轻轻点了点头。他很有些忧伤,他一点都没想到黄宇的话会一语成谶。
9
半年后,很偶然的,他在一张报纸上看到一篇报道,说改制后的青衣江氮肥厂人心稳定,生产经营两旺,能耗降低,效益增高,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报道还配了工厂新主人莫光头视察车间的照片。他本当感到欣慰的,奇怪的是没有,相反,他莫名的心神不定。放下报纸的时候,他听到遥远的地方传来几声闷响,令他心头一震。那闷响节奏均匀,带着嗡嗡的回音,很熟悉。他立即问身边的妻子,听到什么声音没有?妻子却摇头否认。一连几天,那闷响都挥之不去,老在他脑子里回荡。他惶惑不安,便给黄宇打了电话。但是,黄宇的手机里传出的是黄宇妻子肖小云哽咽的声音:“别找黄宇了……他、他已经不在了!”他大吃一惊,迭声询问,但悲痛让肖小云说不出话来。他只好通过114打了厂办公室,问到了向丽娟的手机号码。向丽娟告诉了他黄宇出事的经过。
原来,工厂并非报纸所说的那么人心稳定,原因是为减少成本,一笔化工岗位补贴停发了。改制改得收入比以前还少了一百多块,工人们就有意见了,上班操作时就不那么精心,工艺指标的掌握就不那么精准了。终于有一天,导致尿素融液水分过高,从造粒塔上的喷头里喷射出来后,就不能在下坠过程中凝结成颗粒,而是在塔壁和塔底的漏斗上结成了疤,凝成了壳,像厚厚的冰,不得不停产处理。莫光头对此大为恼怒,硬说是有人蓄意破坏,还向公安部门报了案。其实这种事过去常有,没什么奇怪的,用大铁锤将漏斗上的尿素块打掉,就可以重新开车生产了。这个处理过程还有个专用名词,叫做打疤。他很熟悉,因为他曾无数次参加过打疤。黄宇像过去在车间当班长和主任时一样,带着临时组成的突击队冲上了打疤的阵地。这本是件平常的事,但平常事里有不平常的东西,那就是这一次结的疤特别厚,还有就是,黄宇不该叫谢见屏也参加。
谢见屏少一根手指,又身单力薄,黄宇就没叫他挥舞八磅铁锤,而让他当了望员,专门观察塔壁上的尿素结晶块,提防它受到震动后掉下来砸伤人。照理说应当先处理掉塔壁上的结块再打疤才安全,但造粒塔高七十多米,根本无法企及,只能冒险行事。但仰头望着塔壁,时间长了会肩酸脖子疼,也很累人的。谢见屏认了一会真后,就心不在焉,抽自己的烟去了。等谢见屏再次仰头,只见高高的塔壁上一个大结块已张开了裂口,颤颤欲坠。谢见屏惊慌大叫,黄宇立即叫人撤退。塔底只有一个小门进出,且门槛高过漏斗,撤退时并不方便。黄宇自然是让别人先撤的。等到黄宇最后一个撤退时,门槛下的踏脚已被惊恐的人们踩偏了,头上的尿素块也要掉下来了,黄宇已来不及放正那个踏脚了。于是,黄宇向坎上的谢见屏伸出手,希望能拉他一把。谢见屏拉了,但谢见屏的手少了一个指头,又粘了些尿素溶液,很滑,根本抓不住。黄宇不但没能借上力,反而因此失重倒下了。这时,一块巨大的尿素块从天而降,直接砸在黄宇身上。黄宇戴了安全帽,但完全无济于事……
黄宇是在昏迷了六天之后才去世的。在第四天的晚上,黄宇还醒来过,并用微弱的声音和肖小云开玩笑,说若是开他的追悼会,不要放哀乐,要放就放《国际歌》。没想到,这成了黄宇的遗言。医生做了最大的努力,最终还是无力回天。
他相信,他冥冥中听到的那几声闷响,就是黄宇打疤时发出的,是黄宇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的声音。
他想参加黄宇的追悼会,但路途遥远,时间来不及了。他给向丽娟打电话时,向丽娟就在大礼堂里,追悼会就要开始了。向丽娟说,全厂的职工和家属都来了,大礼堂里挤满了人,到处是一片伤心的哭泣声。他央求向丽娟别关手机,他想听一听。向丽娟应允了。他将耳朵紧贴着手机。但是,他并没有听到哭泣,他先听到的是造粒塔下那一声惊心动魄的巨响,接着,又听到了久违的《国际歌》。随着那沉雄的旋律一波一波地从遥远的天际涌来,灼热的泪水慢慢地湮没了他的视线……2006年8月于常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