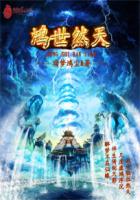唐龙和张汉在姚记煤场附近转悠了八天,却一无所获。
每天进出煤场的都是些力脚,他们衣着肮脏邋遢,面色就如煤场里的灰土地一样。
限期将至,两人不由得开始着急。
从保定到安成县的路程,正常人赶路大约要走两天,但是轻装快马,一天足够。
所以俩人商量着在保定多呆一天,最后再使一把劲儿。
若不是出发之前,秦天保反复叮嘱他们不要以身犯险,以二人的脾气和胆量,早就翻进煤场一看究竟了。
煤场对面的街上有个汤面铺子,两人坐在路边,一边吃着汤面,一边观察对面的状况。
正在这时,四名轿夫抬着一顶软轿从远处过来,旁边还跟着个老妈子。
现如今还坐软轿的人,除了作风老派的达官贵人,就是尚未出阁的大家闺秀了。
软轿停在煤场门口,轿夫正欲落轿,只见老妈子把身子靠在矫窗边说了两句话,然后又回过头和轿夫们交代了几句。
然后轿夫们重新抬起轿子,忽忽悠悠拐进了小巷。
唐龙和张汉对视了一眼,他们知道煤场的侧门就在小巷里。
过了一会儿,轿夫抬着轿子退出了小巷,停在路边墙根底下,然后几个人围坐在一起晒太阳。
“老板,再来半斤护心肉。”张汉喊道。
面铺老板是个方面大耳面色红润的汉子,他喜眉笑眼地跑过来,将一盘酱肉放在二人桌前。
“我就和你们说过,咱做的酱肉,吃完一口还想下一口。”老板操着山东口音说道。
“老板你看,这年头坐轿子的人可不多了。”唐龙装作无意地说道。
“可不是,现在都兴坐洋车,洋车一个人拉,轿子四个人抬,你坐洋车花一块钱,坐轿子就得花四块钱。”老板说道,“但是坐轿子可舒服啊,风吹不着日晒不到,又不用闻马臭味。”
“那坐汽车可不是更舒服?”唐龙笑道。
“咱保定府才有几辆汽车?除了日本人,也就是头头脑脑那两三个人。”老板说道,“咱们寻常老百姓,就是想花这钱也找不着车啊。”
“我可是有些年没见过坐轿子的主儿了。”唐龙说道。
“你看看,你看看,你要想看坐轿子,就天天到我这儿来吃饭,隔三岔五就能看着。”
“就是这个吗?”唐龙问道。
“是啊,可不就是这个。”老板把手插进袖口,蹲在地上说道。
“这是什么人的轿子?怎么还来煤场这种地方?”唐龙皱起眉头问道。
“我听说是这个煤场老板的干女儿,谁知道是咋回事?”老板有些不屑地说道。
“煤场老板的干女儿能有这么大的派头儿?”唐龙咂舌道。
“你可莫要瞧不起这个煤场老板,你看他每天脏乎乎的啥也不是,和工人一起搬煤扫地,其实人家可有钱了。我听说,就连日本人都和他做生意。”
“日本人都和他做生意?”张汉接口道。
“那可不是咋的?”老板说道,“日本人要在咱保定修铁路,铁路修好了就得跑火车,火车不就得靠烧煤嘛。日本人自己没功夫管这个事儿,就找他来做呗。”
“老板,你知道的还挺多。”唐龙笑道。
“我可不瞎说。”老板以为唐龙不相惜他说的话,急忙辩解道,“前段日子挂着膏药旗的日本车经常来煤场,这都是我亲眼看着的啊。而且煤场里的管事儿还来找过我,让我把生意关了跟他们去工地做饭,给的工钱还不少哩。”
“那你怎么不去?”
“太远了,据煤场都说在下面的县里,我可不想受那份罪。”老板笑着说,“我这么大岁数了,还拼那个命干啥,混吃等死得了。你说是不是?”
“没错。”唐龙笑着点了点头,然后说道,“老板,你打点酒来,咱们一块儿喝点。”
“那怎么好啊。”老板高兴地推脱着。
“没事,反正我们也吃不了这么多。”唐龙笑着说。
“那咱们进屋喝吧,我再给你们把肉热热。”老板张罗着。
约莫两个小时之后,秦天保忽然发现一个人影出现在小巷里,正是刚才跟在轿旁的老妈子。
他给张汉使了个眼色,然后两人装作吃饱喝足的样子,和老板会了钞,溜达着走了。
果不出他所料,轿夫又把轿子抬进巷子,然后退出来向着来时的路走去。
唐龙和张汉跟在软轿后面,不紧不慢地走着。
街上虽然人来人往,但轿子却只有这一辆,所以即便跟得很远,也不会跟丢了。
就这样,他们一路跟着轿子来到了花都夜总会。
这是保定这座古老的城市在西风东渐的大潮中结出的奇异果实,这栋高大的西式建筑与周围低矮的土坯房子站在一起,形成了一副既冲突又融合的画面。
轿子停在夜总会的正门口,老妈子掀起轿帘,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从软轿里走出。
她身穿白色点缀金色和蓝色花边的紧身旗袍,肩上围着纯白色的皮草,头发盘在脑后,手里抓着一支给色小皮包。
在老妈子的引领下,她快步走进了夜总会富丽堂皇的旋转门。
夜总会的外墙上挂着一张巨大的海报,上面画着一个身穿旗袍、躺着卷发的美女正对着话筒忘情歌唱,下方用白色油漆写着五个大字:大明星雅菲。
“刚才从轿子上下来的那个女人,和画上的女人是一个人吗?”唐龙问道。
“不像。”张汉摇了摇头。
张汉是侦察兵出身,他的眼神在整个钱怀恩的队伍里都是数一数二的。
“不像还是不是?”唐龙再次问道。
“不是!”张汉这次肯定地回答道。
就在这时,远处忽然传来了“砰砰”几声枪响,紧接着是人们惊慌失措的尖叫。
俩人都是久经沙场的老兵,自然能听出来这就是快慢机特有的动静。
他们顺着声音跑过去,在往东的街道拐角处,他们看到了一群人在路边围观。
人们都躲在周围几十米远的地方看热闹,一辆马车横在路口,车夫已经倒在血泊中。
过了好一会儿,十来个警察跑了过来。他们扒开人群,跑到马车旁边,先是将马卸下,然后才里里外外检查起来。
终于,两名警察把一个满身是血的人从车厢里抬出来。
人群中立刻一阵低呼。
“这不是张五爷吗?”旁边一个小贩模样的男人脱口而出道。
“张五爷是谁啊?”唐龙递上一支烟,然后问道。
“张五爷你都不知道,刚来保定吧。”小贩不客气的接过香烟,来回舔了两下,然后放在嘴里。
“我们初来乍到,确实不知道。”唐龙给他点上火,笑呵呵地说道。
“这可是咱们保定府有名的大财主。”小贩说道,脸上骄傲的样子就像再说他的亲戚。
“哦?说来听听。”唐龙来了兴趣。
“张五爷家的买卖,一口气都说不下来,你知道花都夜总会吗?那就是张五爷的产业。”小贩使劲嘬了口烟说道,“就连日本人都和他做生意呢。”
“张五爷这么有钱,出门怎么也不带个保镖?”
“半个保定府都是他家的,他跺跺脚,城墙都得掉块砖,谁能想到有人敢对他下手啊!”小贩摇着头说道。
“他是不是有仇人?”
“谁敢跟他结仇啊,那不是不想活了?”小贩说道。
“皇军和他做什么买卖啊?”唐龙随口问道。
“什么买卖都做,小到替日本军洗衣服,大到办工厂造枪炮,据说现在还和日本人谈修铁路的事儿呢。”小贩故作神秘地说道,“搞不好就是被那边的派人过来给收了。”
“那边?”
“南边。”小贩低声道,“我听人说,这些天咱这保定府可是不太平,无论是当官的还是有钱人,只要是和日本人打连连,都是他们的目标。”
“还有这事儿?”
“那可不嘛!”小贩撇着嘴说,“这都死了好几个了!”
就在这时,一对牵着狼狗的日本兵跑了过来,他们驱散了围观的百姓,唐龙和张汉也趁势离开了。
俩人一合计,闹市上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搞不好日本人得封城,于是俩人决定离开保定府。
白文弱看着秦天保送来的三口装满财物的大箱子,嘴都拢不上了。
其实秦天保还留了两箱,一箱送到了守备司令部的后院,一箱分给了当晚参与夜袭的弟兄们。
钱怀恩看见杨红兴高采烈地围着箱子转圈,立刻就明白了这是秦天保掩人耳目的计策,于是也装作兴致盎然的陪着杨红赏玩起来。
“秦队长,这都是你们用性命拼回来的,我怎么能收下。”白文弱摆手道。
“您可不能这么说,清剿土匪原本就是我们的职责。”秦天保恭敬地说,“钱司令说这些财物是我们执行军务的战利品,为的又是给孙家屯冤死的百姓报仇,于情于理都应归于县库,才打发我来面呈给您。”
“当晚参与作战的兄弟们,可分到了?”白文弱问道。
“分到了。”秦天保点头道,“多谢县长挂念。”
“钱司令那边?”白文弱继续问道。
“也有了。”秦天保回答道。
“唉!真是皇天不负苦心人啊!”白文弱叹道,“这些日子,我无时无刻不为了钱发愁。安成县甫经战乱,百废待兴,哪一处都要用钱。不瞒你说,我这个县长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多亏你送来的这些财物,又能让我挺上一段日子了。”
“白县长为了百姓生计,苦心经营,真是令我们佩服啊!”秦天保这句恭维话倒是发自肺腑。
“为官一任,就得造福一方。无论是国民党统治,还是日本人统治,亡国不亡国,老百姓的日子总要过下去,咱们中国人的种儿也得传下去,这才是最根本的。”白文弱忽然动情地说,“只要咱们中国人的种儿还能留下去,再大的苦难,我们也能经受。为了把种儿留下去,再大的苦难,我也只能硬着头皮扛下去。”
秦天保差点一时冲动,要把两匣黄金的事情告诉白文弱。
话到嘴边,他终于咽了下去,转而说道:“白县长,这次剿灭王坤一窝,咱们尚且取了这么多财物,如果我们继续剿匪,所得的财物不就可以使县里的财政大为改观吗?”
“古语说:佳兵不祥。”白文弱摆了摆手道,“你的意思我明白,但是不能为了那些钱财就把你们推向战场。只要还有别的办法,哪怕多吃几天苦,我也不能拿你们的性命去换。时局艰危,多得一天安生便是一份福气啊。”
从县府出来之后,秦天保一直在琢磨着白文弱的话,这个优柔寡断的小老头,似乎也有着一股子韧劲。
他一路胡思乱想,回到指挥所的时候,正好撞见了唐龙、张汉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