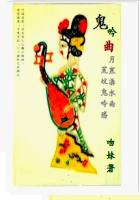平川上缓行着两骑素影,在红霞的映照下,依稀还能看见马蹄下半扬起的飞尘,两骑大马一黑一白,不是上乘的好马,只是李谨霖去城乡上随意找来的。
白马在后,他看了看比他走的稍急一些的男人,“真这么心急吗?”
那名男子没有回眸,“我已经错过了许多,怎能不急。”
他的声音很低沉,仿佛被什么东西压制住了,那是他受过的伤,或许是这辈子里最重的一次,颈侧有一道很长的伤痕,过了许久的时间,声线还未完全恢复。
李谨霖笑笑,“你欠我一条命,若是我要你用她来还,你会怎样?”
男子回头,眼底带着漠然的冰箔,“你想这样羞辱我,大可以不必救我。”
李谨霖没有搭话,他有过这种念想,可明知即使他离开人世,那个女人也不可能为你泛起波澜时,这种念想仿佛就成了妄想,他不敢再妄想什么。
良久,白马落停,他拉着缰绳站在原地,“我就不送你了,往后的路,你自己珍重吧。”
男子闻声回头,“今后有什么打算?”
李谨霖笑笑,“这是对救命恩人最后的关心吗?”
“辞了官,似乎没以前那么冷漠了。”
“人总是会变的。”李谨霖低眉看向夕阳,迷人的晚霞令人感觉很轻松,卸了铠甲后,今生最大的枷锁仿佛也烟消云散了。
男子跟随他的目光,看向那抹凝血的嫣红,南归的大雁徐徐飞过,繁忙中有一丝道不明的悠然。
“你放心,我答应的事,不会食言。”
李谨霖回头,拱手道谢,“我知你不会食言,多谢了。”
男子缓缓的看了他一眼,“那只是一件小事,比起我欠你的,远不足为道。”
“我也只是受人所托,如果可以,我真情愿你已经死了。”
男子再没有出声,不知该怎么搭话。
李谨霖无害的笑,“时间不早了,你启程吧。”临别在即,再没有多说的必要,他边说着边调动缰绳,转开方向。
“恩,你也多保重。”
下一刻,黑马转动,伴着长嘶响起踢踏作响的马蹄声,马下的尘土随风扬去,仿佛寄了凝重的相思与归愁,黑马如箭离弦奔走。
夕阳的落辉缓慢悠长,站在原地的李谨霖自嘲的微扬嘴角,晃悠悠的回想起年岁的那个晚上……
品酒宴未始,前殿灯火通明,悦耳的器乐声不断,而后侧内殿却昏暗阴沉,一个挺拔的墨色身影迈入泽明宫内殿,守卫内监连忙做礼。
“奴才参见李少将。”
李谨霖身后灯影筹措,他脚步微顿,低声道:“劳烦公公跟皇上通报一声,微臣有些事要与皇上禀报。”
内监面带难色,“少将军,皇上正与九殿下说事,奴才不好去打扰,要不,您先稍等一阵,等九殿下走了,奴才再为您通报?”
“无妨,我去前头等。”李谨霖微躬身致谢,脚步沉稳的走向内殿回廊。
那时仍是风歇雪止的好光景,他站在泽明殿映光的玉石廊上,四周的一切景物都悄然沉寂,气温低俯,微风拂动树梢的雪被,落下一些雪末。
回廊灯光昏暗,落影旁,他漆黑如夜的目光中透着坚韧的底蕴,第一次,他许下承诺。
域华城是纷纷扰扰勾心斗角的深渊,她或许能适应,但却不适合,她脾性太烈,属于更自由的天地,他想带她去龙岩看世外桃源,去南疆晒阳赏月,去东临观海寻鱼,去西川策马狩猎,北朔南疆的浩瀚江河,任她想去哪里,他都可以都誓死相随。
他无意投靠北堂景,但在域华城,那个人的危险存在不容忽视,对立不如知敌来的明智。
北堂逸继续留在域华城,北朔与苍古一脉的恩怨随时都有可能爆发,到时的局面必定势如水火,她怀着身孕,留下只会陷入混沌险境。
等了一阵,他深思着踱步移动,忽闻内殿厢房里隐约传来诚然庄重的声音。
“如果父皇坚持儿臣不娶司徒雪盈是忤逆犯上的话,请父皇削除儿臣的皇子身份,让儿子带着阿衡永远的,离开域华城。”
他深吸一口气,蓦然愣在原地。
他本以为北堂逸有太复杂的身世,他的自私不值得莫梨君为他留守,可原来,他们,早已紧系在一起。
半晌后,内监公公小步寻来,却见回廊上空荡无人,搔头疑惑着离开,心疑惑李少将军怎么这小半会儿都等不住。
那晚夜风渐起时,他回首抬眸,远处光影交错,他一眼望空了磁瓦新筑的梦。
此去经年,浮世流转。
还记得吗?
“曹岳的清溪湖边……夏天的时候,开了窗子就能看见碧绿的清溪路……等我们去的时候,再在屋前开一片田园,种下花草蔬果,好不好?”
清溪湖边,那栋他为自己筑梦的屋子出现在眼前,莫梨君拉停马匹,怔怔的看着那幢房子。
北堂逸失踪后,她也曾来这里找过,每一景一致都跟北堂逸和她描述的一模一样,但她不太敢来,怕看见这里空荡荡的样子,怕在这里,相思会不一留神就淹没自己。
她每次靠近屋子,都习惯性的屏着呼吸巡视,可最后,这里总是空无一人,屋子依旧是空荡着的。
胡遇舟来了曹岳后,老爹果然兴致高涨,他的阵营有了同盟,对抗起骆先生时就越发嚣张,有小刀在,他们的争执永远不绝不休,于是,莫梨君带着小刀来清溪湖避住。
半年前,小刀满周岁,老爹与骆先生抱着她抓周,满满一地的东西,连赶回来的曲屏谋都要凑一脚热闹,他们一个摆了金算盘,一个摆了侯印,一个摆了大刀与山寨令牌。
北堂小刀那日特别兴奋,她在地上满地寻找,先是抓了自己最熟悉的金算盘,然后又找了一支金毛笔,那时骆子虚高兴的胡子都可以飞到天上去了,紧接着,小刀用小手去握大刀,吃力的拿不起来,她躺在大刀上纵横翻滚,一点没有离开的意思,看着众人发晕。
胡遇舟在一旁摸下巴,啧啧道:“小肉团果真贪心……”
山溪的水碧绿幽然,滤波随风荡漾,溪面透着别样沉寂的美。
一抹浅紫的小身影蹲在山道的树荫下,她在地上玩耍,用树枝在泥土上画画,她垂着头,稀疏纤细的头发顺在她的脑后,脑袋上用红丝扎起一个小揪,头顶有些斑驳的落阳,虫鸣鸟啼,身边的一切都不能引起她的注意。
她用树枝在泥土上画出一条很长的直线,尾处断一下,又继续画下去,她画的是胡叔叔送给她的小刀,胡叔叔说,那跟她的名字一样,她挺喜欢那柄小刀的,可是现在那柄刀被阿娘没收了。
小刀低声埋怨,“讨厌的阿娘。”
清溪湖畔,一个浅白的身影缓缓行来,那人骑着黑马,缓行着打量四周的景色,清水白面的脸长得俊俏儒雅,可眼中却噙着浓郁不散的浅愁,那种哀戚令人心涩。
不多时,骑马人遇上在道上玩耍的小刀。
轻碎的马蹄声引来小刀的注意,她站起身子,肃然瞪着出现在她面前的男人,小小身子里有说不出的倔强与傲慢,男子翻身下马,怔怔的望着那个孩子。
午后的落阳洒在他的身上,浅白色的身影泛起微光,如漆长发被一抹红丝系着,安静的垂在身后。
他们两两相望,却谁都没有开口说话,一阵微风吹送,带落一阵萧条的落叶,是殷红的枫叶从树梢舞落,男子心弦一动,微张嘴,却不敢开口确认。
是小刀脆生生的声音打破了宁静。
“看什么看?打劫!”
“呃?!”男子忽的愣在原地,简直以为自己是听错了。
“打劫打劫!”
这是她从外公和胡叔叔那里听来的,他们前阵子老在讨论什么事情,中间总是出现这个词,她坐在外公的大腿上玩,默默就记住了。
男子扯开一抹安详无奈的笑,轻柔出声,“你叫什么名字?”
“不告诉你,打劫打劫,听到没有!?”小刀姑奶奶无比霸道。
男子摊开手,“好,那你要劫什么,你来拿吧。”
小刀挑眉,心中一阵雀跃,想不到这话这么好用,她刚要上前,又忽然停住了脚步,用树枝指挥,“不,你过来!”
男子虽然困惑,但依旧笑着靠近,依言站在她的跟前。
男子的身形高大,小刀很辛苦的昂头,才能艰难的看清他,很不满意的蹙眉,“你蹲下来。”
“好。”男子听话的不得了。
小刀怔怔的看着与自己近在咫尺的男人,有些不争气的咽了口水,她的干爹绝顶漂亮,她的胡叔叔绝顶潇洒,可眼前的这个男人也长得好好哦,他身上有很舒服的气味哩……
“你要劫什么呢?”男子见她没动静,笑笑的开口问。
小刀眼眉微蹙,很不得了的大声说道:“亲一下!”小姑娘不害臊,说着就很不学好的在男子脸颊上亲了一口。
男子还有些反应不过来,光天化日之下,他又一次被劫色了……?
小刀靠近时眼角瞄到一样东西,她噌一下睁大了眼,有些惊讶的说道:“咦,这是我阿娘的!”
男子顺着她的眼神看向自己的腰间,那尾红丝狐裘安安静静的系在他的腰上,一点不晓得自己造成了多大的轰动。
“你说,这是你阿娘的?”
“嗯!打劫打劫,快还给我。!”
男子不敢置信的抓着她的小手臂,“你说,你娘也有这样东西?!”
“恩啊!”
小刀有些害怕,她怯怯的退后两步,她说错什么了吗?她阿娘确实也有一个,天天带在身边的呢,她怎么会认错!只是这个男人为何这么激动呢?
男子咽了咽口水,轻揉了揉刚才紧抓过的小手臂,缓缓的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小刀半扬起下巴,这话她说的最熟练,“我叫小刀!”
许多年以后,北堂小刀没心没肺的长大,她一点也不知当年这时,她自报家门的短短四个字,给她阿爹造成了多么震撼激动的影响。
倒是她阿爹,用几近哽咽的情绪紧紧拥着她,念念不停的解释自己的身份,“我是你的爹啊,你爹。!你是我的女儿,小刀,你是我的女儿!”
影响不记得,她倒还能依稀记起自己那时的惊讶情绪。
若问北堂逸,此生有什么是最遗憾的,那便是女儿的那些岁月。他错过了许多,没能陪着娘子,没能看着小刀出世,没能第一个喊出她的名字听她的第一道哭声,在她初生安睡时,时时刻刻的抱着她……
父女相认的那时,莫梨君正在清溪湖畔的屋里收拾行李,她决定上京一趟,北堂逸生死未卜,苍古一脉的事一直没有结果,她能等一辈子,找一辈子,他们不能……
“阿娘!”小刀在屋外欢快的唤了一声。
莫梨君闻声抬头,听着声音在很近的地方,她这女儿不是一般的顽劣,才一岁多就学会了各种坏习惯,总是不经意就挑起老爹与骆先生的争执,从不肯在屋里老实待着,前些日子,小刀拿着胡遇舟送她的小匕首玩耍,在楼梯上对着云姨挥舞,愣把云姨吓得跌下阶梯……
想到这,她立刻起身走了出去。
“小刀,你怎么……”木扇门出去,她忽然怔住了。
眼前,北堂逸抱着小刀疾步走上阶梯,阳辉铺展的门沿内,莫梨君诧异的站在原地。
她不记得自己幻想过多少次再见时的情景,多少次,那张清俊温和的脸若出现在她的眼里,心中会涌起的惊涛骇浪,可现在,他那么真切的站在那里,她的脑子却瞬间空白了。
还不能有知觉时,她被人拉进那个熟悉而温暖的怀里。
多么惊天动地的言语都比不上这样强烈的拥抱,她真实感受到了他的存在。
“你回来了……北堂逸,你回来了……”
“我回来了。”
悬吊着那么久的心终于落下,她伏在他的胸膛流泪,不能自拔的哭泣,商关岁月,在她最绝望的时候,她曾跟老天祈愿,如果北堂逸可以回来,她愿意拿自己的命来换,哪怕只能再见最后一面。
“你说如果我死了,你就陪我。我找不到你,我以为你已经死了,我也想要去陪你。”
“我没有那么坚强,没有那么勇敢,我连离别都不敢承受,你答应我快去快回的,为什么还要让我等这么久……”
“对不起……娘子,对不起。”北堂逸紧搂着怀中的娇柔,心中的愧疚早已无法用言语道明。
他回归在开春的季节。
那一日风朗晴好,莫梨君哭了许久,终于在他的肩头睡着。
北堂小刀听不懂他们的话,她看着阿娘哭泣,阿爹难过,她也跟着哭了好久好久,清风拂过,夹带着山溪边上的各种草叶香味,这一日,他看着此生最爱的两个女人在他的身边安睡。
再没有比这更美满的事,他游走生死边缘,终于得来这最幸福的时刻,他愿终此一生来弥补他亏欠的泪水与辛酸。
从今往后,现世静好,岁月安稳,一切都充满生机的美满。
成帝十五年夏,京都城送出皇榜,成帝告谕,旨称赤鸣军护国有功,忠心可嘉,北朔朝廷将不再追杀苍古一脉,赐封渭水以南的曹岳给苍古侯,以示希望苍古一脉往后能继续巩固边防。
那年赤鸣军鞠躬尽瘁,好不容易打了胜仗,皇帝却将苍古一脉打发到北朔边缘地方,苍古侯君再无涉及北朔朝堂的参政权利,只是一处闲职而已,看起来是赐封,却是真正的贬职。
是北朔开国以来,第一次有了这么具有惩罚性质的封赏。
同年,被成帝囚禁的北堂景起兵反政,太子一手习练的靳军围困域华城,在北朔百姓都以为快要变天时,靳军却被赤鸣军突如其来的攻袭击破,北堂景被赤鸣军围堵在高高的钟楼上,他发了狂,大笑着纵身跃下钟楼,赶到钟楼下的太子妃何晚清正好看到这一幕,自那以后,她再没有开过口,人都说她是被太子之死吓傻了。
支持太子反政的幕僚悉数被擒拿囚捕,唯独丞相李豪被赦免,只是罢了官流放出京。
一年后的同一日,成帝在域华城驾崩,死前,他习惯性的伫立在钟楼下,一改平日的默然,他忽然自言自语的说话,“是朕没有教好他,朕救得了一个儿子,却救不了另一个,白发人送黑发人,到最后,朕还是亲手害死了自己的儿子。”
这话是从伺候成帝的大太监口中传出来的,是真是假,其中原委,至今无迹可寻。
二皇子登基,世称胤帝,其母董玉皇后谨封为皇太后。
北堂小刀三岁那年,被胤帝赐封为箐公主,她完全不知那是什么东西,只是照顾她的小婢忽然多出一堆,而且她那一年过得又开心又郁闷。
开心是因为她阿娘又怀了宝宝,她很快就会有一个弟弟或者妹妹;郁闷也是因为同一件事,自从知道阿娘怀孕了,外公与骆先生,还有云姨与四叔叔、五叔叔,他们好像都比较喜欢未来的弟弟妹妹,都不愿意跟她玩了。
干爹回了京都,胡叔叔又出去云游四海,她小跑着去找最疼她的阿爹,走进房,小肉团的身子直直的扑进她阿爹的怀里。
努力做哭腔状,“阿爹,你是不是也不喜欢小刀了?”
“怎么会?阿爹永远都喜欢小刀!”
“……可是外公和骆先生,还有云姨都不愿跟小刀玩了,他们不喜欢我了!”
“呃……”孩子他爹沉默,遵循不应欺骗孩子的原则,他默默说了实话,“那是因为你带着外公烧了骆先生的胡子,又害外公逃跑时摔了屁股,还连带撞伤了云姨……他们正在努力平复受伤的情绪,所以没空陪你玩……”
“哦,原来是这样!”
“小刀,你是女孩子,女孩子家就要学着温柔一点,乖巧一点,这样外公和骆先生还有云姨,就不会不理你了。”
“可是四叔叔和五叔叔也不陪我玩了呢!”
“呃……”孩子阿爹继续筹措,“下次四叔叔和五叔叔‘吵架’的时候,你不要忽然进去打断,他们就不会不理你了。”
“可是他们明明是一起躺在床上,那就是吵架吗?”
“……”孩子阿爹不知该怎么回答。
“那阿爹和阿娘也经常吵架啊!……”小刀姑奶奶不得了的觉悟了。
“阿爹和阿娘吵架是正常的,不吵架哪来你和你的弟弟妹妹呢?”孩子他爹厚脸皮的撇清。
“呃……是哦?”粉雕玉琢的小刀公主迷惘了,半晌才道:“那阿爹阿娘以后多多吵架吧,我还要更多弟弟妹妹。”
“好!”
“……”房门外,不小心听到这对话的莫梨君,她抚上自己怀胎四月的肚子,忽然有种凌乱到不知如何是好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