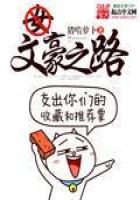符·普赫拉乔夫
我顺着山路翻过一个山岭,来到了彻马尔河峡谷。河对岸有个养蜂场,那里住着我的老朋友斯切潘·安托诺维奇,一个以养蜂为生的人。
这是炎热的八月里的一天中午,峡谷里一片寂静。只有彻马尔河在山谷间奔流着,一边流一边汩汩地欢唱。
我扯开嗓门叫了一声养蜂人的名字,可是安托诺维奇不知为什么离开他的养蜂场了,那只阿尔泰种狗,狼犬阿尔古特准是也跟他的主人一起去了。
这河道上不算太宽,可我知道这水冷得扎人,我不想游过去。我懊丧地望着河对岸那柳树下浓荫里摇晃着的小船,轻轻叹了口气,就在岸上的一棵杉树下等待我的朋友。
河对岸高高矗立的峰峦上的积雪,白得耀眼,一朵云飘过来,雪峰一下消失不见了,像皑皑的白雪在骄阳下忽然融化了似的。
渐渐地,群山披上了淡蓝色的云雾,于是这峡谷仿佛进入了梦境。这些山坡在阳光下无穷地变幻,一会儿一幅新图画,一会儿一个新景象,你看几个钟头都不会重样的。
吹过一阵微风,杉树就沙沙地摇晃起来,像是在谈论什么。它们深绿色的树梢衬托着蔚蓝色的天空,显得分外好看。白桦树的嫩叶在微风中颤动着,闪闪烁烁。树叶和嫩枝在阳光下泛着亮光,不断变换着自己的颜色。
我越看越觉得有意思。我甚至拿起望远镜来细细瞭望远山那终年不化的积雪,瞭望近处泛着淡青色的山顶,瞭望那山顶上一片翠生生的阔叶树,瞭望那黑魆魆的林带和长满枞树的岭岗。
时间不知不觉过了一分钟又一分钟。斯切潘·安托诺维奇还不见来。我又端起望远镜看了看彻马尔河那一边的一小块平地,在喧闹的小白桦林里,那儿置着一个蜂箱。看着看着,忽然,我差点儿失声叫起来。
一头母熊一会儿扭头看看这边,一会儿扭头看看那边,这样东张西望着,沿青青的山坡向养蜂场一步一挪地走来。在它一旁跟着的小熊也一步一挪地拐着它的小歪脚。母熊没有停住脚步,闻一闻,看一看,这样一步步向距离不远的小房子走近。没有觉察到什么危险,它就大起胆子朝蜂箱挨过去。小熊矮,它的头一会儿隐入了草丛,一会儿又从草丛里冒出来,用出吃奶的力气紧跟母亲往前走着。我在望远镜里一眼不眨地望着它们。
那两个畜生来到了置着头一排蜂箱的地方。一看母熊那样子就知道,它是个很老练的窃贼,它准是不止一次地偷吃过香甜的蜂蜜了。它不失时机地动起手来。它走到近处的一只蜂箱,用前掌抓住,高高把蜂箱举过头顶,接着使劲儿往地上一摔。我猛一下回过神来,跳起身子,大喝一声,想要制止它胡来。可是距离太远,再说风是从河对岸吹来的,我的断喝声被风吞没了。我只好傻呆呆地看着我朋友的蜂箱遭受洗劫。
蜂箱被掷到地上的头一下,并没有碎裂。那畜生就又用更大的力气一摔。这第二下奏效了——蜂箱经受不住,终于裂开,成了许多碎片。那些还爬动着的蜜蜂向侵扰它们的家伙猛扑过去。母熊一边用前掌驱逐着,一边舔吃起来。它双爪捧着蜡板,贪馋地舔着、吃着、吞着。小熊也学着妈妈的样子舔吃蜂蜜。它吮吸着蜡板上香甜的东西,一块一块地很快吃进嘴里,把蜡板舔得一干二净,接着吮吸起沾满了蜜的前掌来。
过了不多一会儿,第一个蜂箱的蜜吃光了。这一大一小两个家伙又走近第二个蜂箱,母熊用同样的办法打开了它。
现在,那两个家伙走了,走得非常慢。从它们那慢吞吞的样子,就可以看出它们吃得太饱了。所以好几次它们都已经离开了那些蜡板,可过了一会儿,贪吃欲又让它们挪不动步了,于是它们晃晃悠悠地又转回身来,捡起了那些蜡板。
两头畜生终于吃饱了,那母熊准备往回走了。可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个意料不到的情况:小熊走不动了!它才走了两三步,就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母熊于是只得转回来,它火爆地张开嘴,露出了一排獠牙,对它那笨拙的蠢孩子大发脾气。可是那小熊依旧赖在地上不起来。母熊于是就用前掌按住小熊的后颈,一把揪住后颈的皮,拎起来,拽着拖到河边去。
到了河边,母熊轻轻一甩,就把小熊扔进了河里。
小熊重重地打了个响鼻,从嘴里喷出了几口水,接着又喝起水来。它在水里打了几个滚。到这时,这个吃得发撑的馋嘴小家伙才恢复了气力,清醒了,于是又能够往前走了,虽然是颤颤巍巍地挪着小步,但总算跟在了母亲的身后走了。
大小两只熊很快隐进了密林,不见了身影。
过了个把时辰,小房子附近出现了斯切潘·安托诺维奇。他把我渡过对岸去,听我讲述我所见的熊强盗糟蹋他养蜂场的经过,他难过得直丧气地摇头。
“我不得不离开蜂场到旁边一个养蜂场去。那儿有人病了,我得过去照料一下。你瞧这客人就来了。”
我们疾步向养蜂场走去。狼犬阿尔古特愤怒地汪汪狺吠着跑在前头,它只管低头嗅着熊的足迹。被熊摔破的蜂箱板子撒满了一地。
“不行,咱们还得找地方躲躲,这畜生还会顺原路回来的。我们得防备着些!”他抚弄着他那支乌亮亮的猎枪说,“养蜂人不得不长年同这爱吃蜂蜜的客人打交道,大的死了,小的又长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