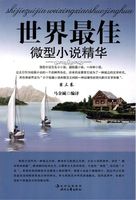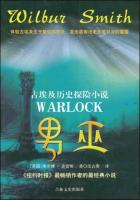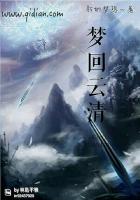当年某月的某一天,某地某茅屋,最好是能有一张古朴的床,如果没有床,一张破草席勉强可以躺着也算不错了。一个落魄的书生,脸色苍白,身子奇瘦,往日风采已消退殆尽,衣衫褴褛,身患重疾,已近弥留之际,躺卧在床上(或者是破草席上)。床头一脏破的碗中盛放着一些时日已久的水,水中甚至漂浮着些灰尘和几只不知名的水虫,在光线的映射下,清晰可见。落魄书生间或艰难地起来喝几口水,就重又倒卧在床了,他手中紧紧地抓着一张美人图,一有时间他就会把它展开,呆望着那张图,好像要把眼睛死死地钉在那张图上才会安心。每次他都看得入了神,浑然不知外界的一切变化,寒来暑往,乐此不疲。他甚至忘了自己的身世了,好像他来到这个世间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无非就是能够每天都能抓紧时间看望着那张美人图一样。外人都对书生这一奇怪的举动表示惊异,他们每有时间便聚在一起,把书生的举动作为谈论的焦点。每次谈论完,他们就都纷纷摇着头晃着脑,才以书生疯了、不要命了、神经有问题了、他的人生就此完了等等之类的话做结,然后才心安理得地离去。有时候,他们男女老少就干脆聚集在书生房门口的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下,亮开嗓子就不管不顾地谈论开了,直到他们的嗓子说哑了,才又有所得地三三两两安然散去,有的夫妻甚至回家了还在茶余饭后就当天的话题再次谈论开来。奇怪的是,他们也乐此不疲。当然起先,有几个妇人,还是会对书生的处境有所可怜,掉起了同情的眼泪来。但是过了不久,她们也就习以为常了,也不再流眼泪了,有的甚至还会说书生大概是疯了。
当然书生知道自己并没有疯,他只是无能为力了。他活得很累了,唯一的牵挂就是那已失去了的红颜知己。书生只想在余剩不多的日子里,能够把以前同自己的红颜知己所有的点点滴滴,不管是痛苦或者是快乐,再体验一次就已心满意足了,所以他争分夺秒地进行着被外人视为怪异的行径。书生对自己的遭遇无疑是最清楚的,这世上没有一个比自己更了解自己的人了。所以书生对外人的惊异并没有表现出什么惊异,他知道这世间像自己这么重感情、这么专一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书生不想对此分辩什么,他不想因此而浪费宝贵的一分一秒。他对隔些时日就要在自己房门口出现的各种各样的影子视而不见,至于说他们都谈论了些什么,书生更是充耳不闻。书生只希望能抓紧时间,把以前和红颜知己的点点滴滴,毫不遗漏地再回忆几遍。书生乐此不疲,全然忘记了时间的流逝和世事的变迁。
当然书生最希望的还是能在临死前见上自己的红颜知己一面,哪怕只是一眼,他就此闭目而亡,也就没什么遗憾了。书生发觉自己竟然爱美人如命,书生不禁自嘲起自己是当今的严监生,只不过他们所爱的不一样而已。
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书生刚喝完了一碗稀粥,那是隔壁一个好心的老大娘给书生送过来的。老大娘对书生照顾有加,像疼爱自己的儿子一样照顾着书生,大多时候都会把自己原本就已紧缺的饭粥施舍些给书生勉强填饱肚子。要不是有老大娘无私的关照,身患重疾的书生,恐怕早已一命呜呼了。好心的老大娘刚起身离去,书生捡起一根破草席上掉落的草枝,把床前即将被狂风吹熄的残烛费力又拨了拨,才把即将枯萎的烛芯重又挽救了回来,让它重又焕发出了光芒。现在书生已经很少看书了,随着生命力的一步步消逝,书生觉得自己所剩的时日不多了,没有时间再让他看书了。书生床头堆放的书籍,由于久未翻阅,业已蒙上了一层不浅不薄的尘灰,在烛火摇曳的亮光中,依稀可见。
书生原本是想看看那些久未翻阅的书籍的,因为当晚书生突然觉得精神百倍,人也舒坦了许多。但昨晚一个不祥的噩梦,让书生复又惆怅满怀。梦中书生衣衫褴褛地横尸在荒郊野外,一只凶恶的秃鹰,空着饿了多日的肚子,从高空中振翅直奔书生的尸首俯冲而来。当它坚硬、锐利的尖嘴,发了疯似的啄噬书生冰凉的肉身时,睡梦中的书生不由惊出了一身冷汗。书生甚至大叫了一声,才复归于沉静。后来,书生就清晰地听到了慈祥的母亲在自己耳旁埋头散发号啕大哭,震耳的啼哭声响彻在书生的周围,久久无法散去。母亲一直重复着这么凄凉的一句:儿啊!都怪你太早涉足红尘,才会落得如此下场啊……母亲的哭喊声此起彼伏,渐行渐远,直至最后才归于平息。翌日醒来,回想起昨晚梦中的情景,书生不禁惊诧于自己竟然还能一觉睡到天明,却未被险恶的梦境所惊醒。但这让书生更感到自己的时日恐怕不多了。书生直觉昨晚的梦肯定是一个明显的暗示,连日来不停的咳嗽,以及日渐虚弱的身体,更坚定了书生的看法。有一次,书生甚至还咳出了血来,那随之而出的斑斑血迹,瞬间沾满了书生的嘴角。当那冰凉的液体触及书生尚余温热的皮肤时,书生还高兴了起来。他以为这次他终于咳出了痰来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的病还有好转的机会。但当书生伸手去擦拭,看到手上沾染的斑斑红迹。他才知道自己白高兴了一场,才自嘲起自己的愚痴来。从那以后起,书生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就越来越了如指掌了,他更加明白自己的时日不多了,也就是从那次起,书生就几乎没有触及那些跟随他奔波半生的书籍了。
所以这次书生随手抽取出床头的一本老子的《道德经》,轻轻地拂拭去书皮上的灰尘,正欲翻开阅读时,想到了昨晚不祥的噩梦和自己每况愈下的身体状况时,他复又把业已摊开的书籍缓缓地合上了,然后独自沉思了一会,才决绝地把书物归原处。
他现在所需要的就是希望能抓住一分一秒看望时刻陪伴在自己身边的美人图,力争把以前所有的往事都回忆起来,才能安心地亡去。于是,借着微弱、随风摇曳的烛光,书生利索地从自己的衣襟中掏出了珍藏多年的美人图,小心翼翼地把它平展在自己的眼前,这张经由书生珍藏多年的藏图,虽然跟随着书生几经奔波,却依然保存完好,丝毫看不出有什么破绽,特别是图纸的颜色和里面的人物依然容光焕发、神采奕奕。书生此生所做过的事情中,把这张图珍藏得如此完美无缺是让他最为满意的。
此刻,窗外依旧风雨交杂的,并且风雨有越趋肆虐之势,不时有惊人的电闪雷鸣出现,一条弯曲的闪电像毒蛇一样刚从窗外蹿过,紧接着伴随着巨大的闷雷轰隆一声响,就又有几条盘旋纠缠在一起的闪电,好似被响雷活生生地劈开,轰地一下,四分五裂地也就硬生生地碎裂开了。书生不觉被这巨大的闷雷所惊,愣怔了一会,竟一时忘了去看那美人图了。他从小胆子就小,每逢遇到什么惊惧的事情,总是往父母的怀中缩,但那时候,书生却是快乐的,至少他还有依靠。一阵狂风,肆无忌惮地踢开了那扇摇晃不止漏洞百出的木板门,无情地席卷了整个茅屋,书生不觉浑身又一哆嗦。这时,他才记起隔壁那个好心的老大娘已经走了许久了。书生只得起身把那门重又关紧,顺带把接雨的盆罐中满了的水泼出门去,但书生的能力只能勉强顾及到那些漏水凶猛的地方,至于说那些相对微不足道却又步步紧逼的地方,书生是无能为力了。为此,梅雨季节可以说是书生最为难熬的日子了,长年累月地生活在阴湿的地方,使书生显得比常人浮肿了许多,苍白了许多。他甚至已经出现了老年人才特有的症状。他最近常常没来由地腰酸背痛,却又得慢慢地独自忍受着折磨,有苦无人诉说。特别是逢到刮风下雨的日子,疼痛也就更加肆虐地席卷了他身体的各个要害部位,有时,他甚至出现了难以挪动身子的情况。有一次风雨天,他拿着一只破碗去盛从屋顶滴落下来的清水喝,当水就快满了时,书生还算及时地移开了碗。但当他双手捧起碗喝到一半时,那手却不听使唤地剧烈疼痛了起来,钻心的疼痛瞬间迫使书生丢下了碗,余剩的水泼洒了一地。碗最终停止了骨碌的滚动,静止了,但书生的疼痛却丝毫不见减缓。他疼得龇牙咧嘴的,在地上打了好几个滚才稍稍缓息了下来。等他清醒了过来时,风雨也才稍稍止歇,书生已不知他到底躺倒在地上有多少时候了。
一阵滚雷猝不及防地从空中轰隆隆席卷而过,那巨大的滚动和声响,打断了书生悠远的回想。书生又再次凝望着屋里的一切,他发觉此刻他已分不清现实和过去了,这样的情形已不知多少次出现在他的眼中和梦中了。屋中的漏水处仍在滴滴嗒嗒不断地往下滴着水。那些水连绵不绝地往下滴落着,让书生看得入了迷。书生觉得自己的生命就像这正缓缓滴落的水一样,总有一天会滴完的,只是书生还不知道具体是哪一天?书生多么希望这水就这么一直缓慢地滴落下去,永不停息。书生觉得这样很诗意,慢慢地竟喜欢上了这不断滴落的漏水。如果不是漏得太凶,他也不再拿盆罐去接它们了,看着它们像小蛇一样在地上自由自在地蜿蜒游走,也不乏是一种消遣。书生觉得自己要是也能像它们那样自由自在地游走,那该有多好啊!书生突然之间感慨万千,好似有千丝万缕的情感把他紧紧地包围住了,让他有感却不能发。以前每逢这样的时刻来临时,书生一般会毅然地拿起笔,把千丝万缕的情感一一解剖了,条条理清了,然后理智地写下了一些感人的诗篇,当然书生写得最多的是对爱人的思念之情的倾诉。那些书生写过的满意的诗篇,书生理所当然地也进行了保存,现今就把它们完好地封存在一个精致的檀木盒中。那是他的母亲临终前,托付给他的唯一的遗物。听母亲最后艰难地说,那是他们家世代相传的宝物,要他好好保存,将来好传给自己的媳妇。母亲勉强把这句话说完,也就安然地闭上了自己的双眼,脸上甚至流露出了欣慰之情,没有丝毫痛苦的情状。平日,母亲常常告诉他说,这辈子受了那么多的苦,死了也要死得风光点,并叫他不要哭,要为她感到高兴。母亲以自己为榜样,说到并且做到了,她死了,但却面带着欣慰之情。书生本来是决定要完成母亲的嘱咐,不掉一滴眼泪的,但看着母亲慈祥的面容上那些刀刻般的皱纹和满头丝缕的白发,想起母亲平日里的音容笑貌,特别是母亲对他亲切的嘱咐,书生终于哇地一声哭开了。他像个不懂事的小孩一样,尽情地哭了,哭得泗涕横流,却不自知,好像他生来就是为了在那天哭个透彻似的。
但书生现在却不想再次提起笔了,那笔就搁在床头的笔架上。这笔跟随他驰骋了多年的考场,写过了多少诗文,依旧挺拔如昔,生气毕现。然而,现今书生往日那潇洒的英姿和英俊的神情却即将流失殆尽,只余下越发憔悴的神色掩盖下的一张苍白得可怕的面容。书生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时日没有照过镜子了,甚至已完全记不清自己的长相了,只记得从小到大,逢见过他的人都一致夸赞他长得眉清目秀的。在他还小的时候,他们说着说着,手大多也就不自觉地摸了摸他密发丛生的脑袋,然后才尽兴了似的离去。每逢那时,书生都觉得很温馨、很开心,乐开了花的脸上自然而然地也就溢满了笑容,当然受到别人的称赞谁不开怀而笑呢?但随着岁月的流逝和年龄的增长,书生越发感觉到俊美的长相,也给自己带来了不大不小的麻烦。
譬如,一次,一个圆月高照的夜晚,书生拿着一本书独自踱到离家不远的荷塘旁畅声朗读着。书生已完全沉浸在书的意境和周边宁静的氛围中去了,读到精彩处,甚至不觉摇头晃脑了起来。但黑夜中不知何时从何处冒出了一个浑身同样摇晃不止的人,只见那人颠颠地向书生所在的地方一路晃荡了过来,像在跳着一支即兴的舞蹈。那人的手上还拿着一只肥大的陶罐,罐上张贴着纸剪的鲜红的“酒”字,赫然醒目。那人显然是喝醉了,他踉跄着不稳的步伐,不时拿着酒罐往嘴上一阵猛灌,俨然一个不折不扣的英雄好汉。
起先,书生并没太在意醉汉的摇晃而来,倒是为醉汉如此走路是否会摔倒感到担忧,甚至想去扶摇晃的醉汉一把了。虽然他并没有真正行动起来,但还是放下了手中的书,注视着醉汉的到来,时刻准备着搀扶即将要摔倒的醉汉。未料,醉汉摇晃到了他身边,却并未见摔倒。醉汉好像已经掌握了如此走路的诀窍,并乐在其中,难以自拔了。书生也终于可以长长地吁一口气了。但醉汉却就此停住了脚步,不再继续摇晃着向前走了。他好像从此就不会所有的动作似的,傻痴痴地盯着书生看了许久,这让书生感到极为不自然。书生躲避着他目光的注视,假装不以为意,重又翻起手中的书,迈开优雅的步伐,边读边又踱了起来。书生刚踱了几步,就听到了身后传来了一声瓮声瓮气的话语:啧!啧!啧!好美的姑娘啊!紧接着醉汉就迅疾地颠到了书生的面前,喃喃着痴痴地又重复了这么几句。说完,他打了个满足的饱嗝,就轻缓地慢慢地跪倒在书生的面前了。本来,书生以为他说的是哪个美丽的姑娘,未料,那醉汉竟然把他当成了女人家。这让书生感到意外非常,他的脸上甚至瞬间飘飞起了红晕了,但转念一想,醉汉喝得醉醺醺的,一时认错了也情有可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