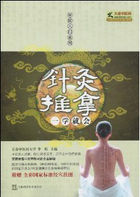此刻,天已大亮,但是天色依旧阴沉,只是先前微乎飘摇的斜风细雨,也已逐渐止息了下去。总之,前途显得渺茫且平静,只是不知是否蕴藏着更大的难测与风险?带刀者如铜像一般伫立在梅花祭台的中心,目光如炬片刻不敢怠慢地注视着广阔的祭台上父母的灵位,周围伴随着兄弟姐妹的灵位。带刀者双手持有如烟燃烧的檀香,心中暗暗与父母的亡灵进行默契的交流和沟通。然而每当他向他们询问起仇人李三的下落时,他们却总是以一副缄默的面孔面对他,仿佛他们已经瞬间失去了言语表达的能力,他们的表情同样变得怪异非常,似笑非笑,又略显不耐烦,仿佛是他们对他多年来执意地追寻,却依旧杳无李三的音训的无情的嘲弄。之后,他们就都露出了些微的愠色,这让他感应到了这必是他们知道了他前日错杀了许多无辜的人而对他表现出的深切责备。再后来,他们的脸色重又恢复了平静和慈爱,他知道他们必定是又要劝说他放弃这段仇怨,放弃追寻李三,娶妻生子,好好安定下来过平静的日子。他在父母的面前自是不想违背老人家的意愿,但是每每与父母分开时,那巨大的仇怨与愤懑就又如洪水一般紧紧地席卷着他,使他时刻不能安定下来,奔波于亡命的天涯海角,只是为了早日亲自手刃仇人,以求得心灵永恒的安宁和慰藉。也仅有在这样的时刻,带刀者才能如常人一般手持檀香祭拜祖先,而他那把如生命般的精致大刀此刻就平静地躺倒在地板上熠熠闪光,与越发明亮的天光交相辉映。然后,当他听到背后的响动,想即刻蹲下身来取刀护卫时,已为时晚矣,一只锐利的响箭早已刺穿进了他的左手臂。等他回过身来,梅花祭台广场中心依旧一片广阔,杳无人烟,整个场景就宛若是在梦中一般显得虚无缥缈。只有那些鲜艳傲霜的梅花依旧绽放如初,像烈火一样奔放、燃烧着。随后,它们仿佛就此蔓延到了地上,与带刀者滴淌而下的鲜血交相辉映,分不清彼此,燃放得更为艳丽动人。除此之外,四周一片死寂,只有带刀者的神情依旧坚定,寸步不移。他暗自度想,射箭者必是熟人,只是又令人料想不到。那么,此刻他到底在何处隐藏呢?
带刀者正欲忍痛离开梅花祭台之际,如霜却偕同贴身丫鬟小玉迈着款款莲步飘忽而至,在经历了昨夜充足的睡眠之后,如霜的脸色明显亮丽了许多。这更衬托出了她不凡的风采,只是忧伤的神色依旧若隐若现。如霜双手捧着洪秀的亡灵牌位,牌位的雕刻精雕细琢,只是凄清有余,只几个鲜红的楷书镌刻其上,宛如洪秀平常炯炯有神却又清秀有加的眼睛。带刀者目送如霜把洪秀的牌位安置在祭台上某个空闲的位置,然后拈香祭拜。带刀者不由也心生悲伤,随同如霜施礼祭拜。尽管他平时与沉默寡言的洪秀并无过多的交情,只草草见过了几面而已。但身为一个保镖洪秀对如霜尽职的保护,和此次为了探询李三的下落而惨遭杀害,都与他有关。于是,洪秀那张英俊而伟岸的脸庞再次在他的脑海之中浮现,只是多少显得有点虚无缥缈,不再似先前那般明朗动人。这时,如霜才回过身来对带刀者说,由于昨日太过悲伤,竟忘记了告诉他,负责与洪秀联络消息的是一个叫品章的人。此人是个街头乞丐,中年人,留有一把粗黑的大胡子,衣衫常年整洁如新,不像其他的乞丐一样衣衫褴褛,只是一条腿却不知为何瘸了,像是李铁拐一般拄一枝竹杖,常在南花街一带乞讨为生,故对整个凤凰城的地形地貌,人文景观也比较熟悉。于是,带刀者仓促地话别了如霜,嘱咐她回盈翠路的路上小心,就马不停蹄地踏上了前往南花街寻找品章的路程。
一只叫不出名字的飞鸟从带刀者的头顶盘旋一掠而过,喑哑叫了一声,像是一只海燕一般飞向另一个不知险恶的浪头。南花街就在不远方了,而此时天色却已向晚,又将是另一个隐伏着躁动的黄昏。暮色完全降临之际,红衣女在南花街的门口拦住了即将入街的带刀者,其时红衣女手上所持的鲜花在暮色昏黑的映衬下显得萎靡不振,早已失去了往日绝代风华的光彩,只是街内还未打烊的店铺所透露出的丝丝入扣的昏黄的灯光,让它顾影自怜,独自回味往日的风采。红衣女是江湖上有名的神女,据说她豢养了一只神奇的鹦鹉,从鹦鹉的口中几乎可以得知天底下所有不明之事,而此刻鹦鹉就神立于红衣女的肩上。红衣女一袭红装素裹,一手持一朵不知道名字的鲜花,另一手倒持一把红绣佩剑,只是不知为何她的面容被黑纱巾遮掩去了大半,只一双细长柔顺的眼睛显露在外,阅见天日。红衣女用女性特有的温柔的嗓音劝说带刀者此时不要进入南花街。她说,否则,南花街将有一场杀戮因他而起。在街口昏黄灯光的映衬之下,带刀者观看红衣女的脸庞,仔细聆听她的诉说,竟一时以为是如霜在他身边倾诉耳语。在他看来,红衣女的脸型以及轮廓,特别是她那双脉脉含情的双眼与如霜竟是如此相似,只是还不知道她具体真实的长相罢了。红衣女的声音同样充满了柔情,水波轻轻荡漾一般。但他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两个如此相像的女子竟会让他陷入了进退两难的维艰境地。最终他谢绝了红衣女邀约他暂时到街外农舍过夜的请求,在街口即将熄灭的灯光的映衬下,带刀者形单影只、坚定不移地进入了南花街的街门口,只余红衣女在街门口面对着他逐渐远去的背影无可奈何,顾影自叹。
在红衣女忧伤的眼光中,带刀者的身上隐隐发散着巨大的仇恨的力量,就是这股无以发泄的力量驱使着带刀者无所顾忌地一往无前,而竟忘却了人间自有真情在。带刀者刚强的外表下实则隐藏着一颗异常脆弱的心,在某些时刻,它竟将一触即碎。可惜的是,此刻这巨大仇怨,红衣女竟也无法使它软化下来,平静地面对又一个即将破碎的时刻的到来。
南花街果然热闹非凡,即使已经是入夜时分,依旧有继续做生意的店铺零散地分布在街两旁。带刀者行路匆匆,沿途认真找寻却并未能找到品章,此时,街上几乎无法找见任何一个乞讨者。于是,带刀者就势进入一家打铁铺问个究竟。只见打铁铺里火光通红,打铁声四下响起,火星四溅,打铁的几个赤身大汉都早已是汗流浃背、挥汗如雨,但他们都神情专注地盯着即将锻铸完善的铁器,轮番锤打,丝毫不敢怠慢,对周围的一切仿若熟视无睹。打铁者共有四个大汉,分成两组,中间一熊熊燃烧的大火炉,里面炭火正旺,有被锻烧得通红的铁器掩埋其中,隐约可见。不料,此刻,一支飞刀嗖的一声,直刺向带刀者的背部,带刀者闻声即刻仓促闪向一旁,飞刀顺势直飞刺向了其中一个白脸铁匠。眼见就要击中,白脸铁匠不慌不忙地扬起铁榔头,只听得当地一声,飞刀就顺服地躺倒在地,像是一只受伤的飞鸟,再也飞不起来了。带刀者不由心生敬佩,即刻向白脸铁匠施礼拜谢,并向他打听乞丐品章的下落。不料,白脸铁匠竟似闻所未闻,对带刀者的礼遇置之不理,继续低头锻造还未完善的一把短刀。短刀已逐渐锋芒毕露,只是还未嗜血成性。他对面的黑脸铁匠终于发了话,原来白脸铁匠是个哑巴。黑脸铁匠停顿下来,令白脸铁匠面生怨尤,但也无可奈何,只得蹲到屋角生起了闷气。黑脸铁匠抱拳还礼,回答道:“洁身乞丐品章明天刚好即将来此取订制的短刀,明天午时于此可见到他。”只是一个乞丐不知为何要打造一把如此锐利的短刀,难道乞丐也要用冷兵器来防身,不禁令人心生喟叹和疑惑。
于是,带刀者当夜只得在南花街的宜兰客栈暂住一宿。
翌日午时,阳光早已退散掉了正午时分的极度炎热,逐渐散漫了起来,温和了起来。此刻,带刀者方迷醉未消地起了床。由于昨夜不小心过度的痛饮,一时竟冲刷掉了满腹的哀怨和忧愁,带刀者竟一时忘却了今日将有重要的事情还要去办理,酩酊大醉沉沉睡得天昏地暗、不省人事,以致延误了关键的时刻。当带刀者匆忙赶赴打铁铺时,悲剧早已发生了。此刻,打铁铺早已消散了原先的火热氛围,那四个打铁的大汉也早已不知所踪。打铁铺人去楼空,空空如也,显得极度萧瑟,只余地上蜿蜒流淌的鲜血,鲜红得刺眼,还余温未消。看来,一场险恶的杀斗才刚刚结束不久。据目击的民众描述,血案就发生在阳光最为炎热的时分,那时太阳高悬在天空正中,连风也逐渐窒息了起来,阳光显得十分刺眼。乞丐品章一身洁净,拄着竹杖一拐一拐地进入了打铁铺取订制的短刀。由于天气晴朗,在外面可以清晰地看到品章满面春风,乞丐品章的脸上甚至漾起了平时少见的笑意。如果不是蓄着一大把胡子,乞丐品章可以算得上是一个清秀俊朗的汉子,特别是他一双细长灵动的眼睛充满了特有的光彩与灵性。但是由于大街上过分地热闹,谁也不知道在打铁铺里乞丐品章究竟为了什么和白脸汉子争吵了起来,听不清楚他们究竟说了些什么。只看见白脸汉子面露狰狞,不断冲着品章大吼着什么,他的耳根都红了,脸上青筋暴露。乞丐品章也不甘示弱,最后他忍无可忍拿起了竹杖敲打在了白脸汉子身上。就这样,白脸汉子顺势抄起了桌上早已锻造完善锋芒毕露的短刀,只一段耀眼的白光闪过,乞丐品章就应声踉跄倒地了。短刀不偏不倚正刺中品章的心脏部位,还来不及半声哀号,乞丐品章就一命呜呼了。当时,由于昨夜拼命地锻造还未完成的铁器,其他的三个打铁汉子还沉醉在甜蜜的梦乡之中一无所知。据目击的民众绘声绘色地描述,当乞丐品章的尸体被其他的乞丐从打铁铺里抬出来时,他们清楚地看到,那柄精致的短刀深刻地刺入了乞丐品章的左胸膛。由于失血过多,他的脸色早已煞白了,就好像死的是那个瞬间慌张逃窜无踪的哑巴白脸大汉一样,不断有鲜血从他的身上流淌而下,洒满了大街所过之处,到了最后竟飘洒成了朵朵鲜艳的梅花形状。这是当地民众最引以为豪的形容鲜血的措辞。在他们看来,用傲霜斗雪的梅花来形容不屈而亡的死者的鲜血无疑是最为适合的。除此之外,似乎鲜血只是鲜血,它就像是河流一样静静流淌着。然后,闻报而来的官兵抓走了还沉浸在甜蜜梦乡之中的其他三个打铁大汉。
这时带刀者可谓走投无路,如一只无头苍蝇一般在大街上随处晃荡,目光迷茫,眼神涣散,像没睡醒一样,又像是在对什么重大的问题深思熟虑。哑巴白脸大汉的畏罪而逃以及乞丐品章的死亡,几乎已经宣告了他寻找李三最后希望的破灭。突然,一个带着一副黑色面具的面具人挡住了带刀者的去路。面具人披挂着一件白色风衣,风衣迎风招展,随意飘扬,就像是一面遥指前路的旗帜一般无所禁忌。面具人伸手指向街心东南方的一条曲径小巷,用瓮声瓮气的话音对带刀者说道,前方小巷深处有一人已等候带刀者多时,请他即刻前往相会。由于面具的遮蔽,他看不见面具人嘴唇是如何蠕动的,只透露出两只灵动的双眼,不时闪耀着坚定的光芒。虽然看不出面具人整体的面容,但是透过面具人坚定的双眼,带刀者隐约洞悉到了面具人内心的一片真诚。面具人的眼神让他觉得似曾相识,就像是他一个失散多年的老朋友,可能是已多年不见,往昔熟悉的声音也变得虚无飘渺起来,难以辨别罢了;亦或是面具人遇到故交刻意的伪装和隐瞒,既然他不肯以真面目示人,料想必定是有难言之隐。未以真实身份示人的面具人也很有可能是带刀者继续前行的一个拦截者,但是此刻,带刀者却宁愿相信面具人是他的指路人、同路者。于是,深知江湖规矩和礼节的带刀者,也就不再多问,只是拱手答谢。随后,面具人依旧面无表情,再未发一语,就如同陌生人一般与带刀者擦肩而过,向远方而去,不知所踪了。恍若幽灵一般的面具人适时出现,并为带刀者指点迷津,使带刀者不得不只身前往街心东南方的小巷深处。或许,想见带刀者的那人能为陷入迷途的他带来“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别样感觉,而面具人真的只是一个起了穿针引线的作用的陌路传话人罢了。面具人总是给予人以既神秘又真实的感觉,关于他的真实身份,带刀者很难真正得知,除非他们拆除掉刻意装饰的面具。但是那就能显露他们的真实面目了吗?请不要忘了,心灵也有迷惘和混沌的时候!
寒冬的季节,虽有阳光的普照,但是寒意依旧逼人。这是一条幽邃的小巷,由红砖围砌而成。小巷围墙的周围散落着几株叫不出名字的树木,把小巷点缀得更为古典和幽深。有枯黄的树叶或者树花随风而降,逐渐洒落在小巷的过道之上,几乎铺满了过道,给人以丰满的感觉。树上的鸟巢偶尔传来几声凄凉的鸟叫声,划破了小巷静谧的背影。小巷名唤乌衣巷,不知道其名字的确切由来,但是有好几个版本在民间流传,其中最为可信的是有一个名唤乌衣的善良而美丽的女子在此处受仙人指点羽化成仙,故后人为了纪念这个热心帮助穷困民众的女子,把女子的名字定为此无名小巷的名字。带刀者的脚步逐步踩碎了树叶或者树花,它们在带刀者坚定且有些急促的脚步之下发出痛苦的哀鸣和呻吟,一路蔓延直至小巷的尽头,随后它们就停止了动静,可能已近弥留之际,再也无任何气力,做出任何的作为了。疼痛即将消逝,就无所谓生死了;过多的挣扎也就显得徒劳无益而可笑万分了。
此刻,在小巷尽头,所有的动静早已消逝,也就谈不上任何痛苦或者欢乐了。但是小巷的尽头依旧空无一人,这使得小巷仿佛是条迷宫般神秘莫测,它充满了无尽的诱惑和惊惧。但那股震撼人心的力量却远未发散出来,它似乎是潜伏在不远处屏息等待着某个爆发时刻的到来。然后,带刀者迷惘的目光终于看到了在红砖墙壁上的那排不大不小,但是却龙飞凤舞的连体草书:
李三已死
仇人李三是否真的已经死了?这让带刀者觉得自己从一开始就陷入了一场预谋的骗局之中,仿若自己是一颗受人任意摆布的棋子一般被无情地推入其中,从而陷入无法自拔的境地。而阴谋者就是利用了他报仇心切的心理,使他一步步步入这个万劫不复的迷途之中。那么,究竟到底是谁在背后主宰和操控着这个布局?幕后主使者最终的真正目的又到底是什么呢?那么,既然事已至此,带刀者是就此罢休,还是继续找寻仇人李三呢?这是个只能由带刀者亲自抉择的问题。或者是已经到了由不得他自主的境地,他只能继续被迫顺波逐流地追寻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