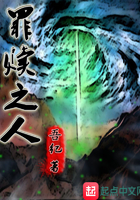都市书写与比较研究
试析老舍的中西都市文化观
吴永平
吴永平,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论文摘要:老舍的“文化”意识觉醒于上世纪20年代初“中西文化论战”第二次浪潮澎湃之时,其早期小说作品中留有该浪潮的深刻印痕。其后,老舍在伦敦生活多年,亲身体验到西方都市文化固有的强大的更生力,同时也获得了观察本土都市文化的更为客观的视角。老舍认为中西都市文化的最高境界都为“近乎自然”,其功能都在于满足市民“求真理与娱乐”的“人生享受”;他赞同中西文化互补,并认为,互补的结果无碍于中西文化葆有各自鲜明的主体性。
关键词:老舍;老伦敦;老北京;都市文化
作者:吴永平,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始终如一地注目于都市文化生活的作家本不太多,而在这本不太多的作家中能以世界性眼光对中西都市文化进行批判性审视的作家就更少了。老舍,便是这少之又少的作家中的一个。
由于老舍的一生几乎都在都市里度过,无论是前现代的北平、后工业化的伦敦,作为殖民地的新加坡,还是尚处中世纪的济南、半殖民地的青岛及现代化的纽约;又由于老舍的作品几乎全是对市民生活的描摹,无论是“京师德胜汛公私立官商小学堂”(《老张的哲学》)、“钟鼓楼后面”的“天台公寓”(《赵子曰》)、“戈登胡同门牌三十五号”温都寡妇的“三层小楼”(《二马》),还是火星上的猫城(《猫城记》)、西城护国寺附近的“小羊圈”胡同(《四世同堂》)、“残灯末庙”的九城(《正红旗下》),俱皆如此。据此,笔者认为,老舍作品中所言及的“文化”无不可视为“都市文化”。
细读老舍的作品,可以窥得老舍的都市文化观及其演变的轨迹。
一
老舍的“文化”意识觉醒于1919年至1925年间,即从走出北京师范学校的校门到走出国门。这五年,正是西方文化冲击中土文化的大震荡时期,中国的政府组织、社会结构及国人的思想观念、道德准则等均发生巨大的变化,老舍自觉或不自觉地被卷入该潮流之中,有意无意地在浪潮中打滚——他曾参与京师郊外北区的新教育运动、缸瓦市基督会堂本土化运动、京师中小学教员索薪运动、联省自治运动,曾被基督教会指派为出国任教人选——他曾多次面临人生抉择的关口,又多次自主地“小型的复活”。
如果强调指出老舍人生道路上的这五年正值中国近代思想史一个特定阶段,当更可见出此期的“文化”准备对于老舍即将开始的文学创作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
据日本学者后藤延子的观点,中国近代关于东西文化的论战共发生两次: 第一次发生于鸦片战争到戊戌变法时期,第二次发生在1915年至1925年间。在后一时期,参加论战的中国学者有梁启超、胡适、李大钊、陈独秀、梁漱溟等,外国学者有先后应邀来华的杜威、罗素等。概括地讲,当年这些中外学者为解救中国危局所开出的文化药方大致可归纳为“调和”论、“西化”论、“东化”论及“苏俄”论。梁启超、杜威等倡言中西文化“调和”,认为调和后形成的新文化既可挽救处于“没落”境地的西方文明,也可救治处于“衰亡”境地的东方文明;陈独秀和胡适主张全盘西化,前者颂扬法国文明,后者独钟美国文明;梁漱溟提出“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认为“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李大钊则认为,东方文明“颓废于静止之中”,西方文明“疲命于物质之下”,而把“创造新文明的希望寄托在以十月革命开创了世界史新阶段的俄国文明身上”。[日]后藤延子:《李大钊的东西文化论——在东西文化论战中的地位与思想史上的意义》,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李大钊研究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99年。
老舍当年是否关注过这场文化论战呢?答案是肯定的。1922年他在南开中学国庆纪念会上发表过著名的《两个十字架》的演讲,提到要“破坏,铲除旧的恶习,积弊,与像大烟瘾那样有毒的文化”及“创造新的社会与文化”。《赵子曰》中有多处关于“东西文化的高低”的议论,《二马》中也曾提到“东西文化的比较,这个题目现在很时兴”。
早年的“文化”准备,对老舍前期小说创作影响甚大。在《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三部长篇小说中,经常可以读到作者对上述各种文化观的点评。
他对“调和”论似无好感。《老张的哲学》中借描写“学务大人”形象对该论调进行了讽刺:“(他)穿着一件旧灰色官纱袍,下面一条河南绸做的洋式裤,系着裤脚。足下一双短筒半新洋皮鞋,露着本地蓝市布家做的袜子。乍看使人觉着有些光线不调,看惯了更显得‘新旧咸宜’,‘允执厥中’。或者也可以说是东西文化调和的先声。”《赵子曰》中借描写中式西餐厅的乱象对这一看法进行了挖苦:“这座饭馆样样是西式,样样也是华式,只是很难分析怎么调和来着。若是有人要作一部‘东西文化与吃饭’,这座饭馆当然可以供给无数的好材料。”《二马》中借描写老马的穿着对该论也有讥评:“老马先生把驼绒紧身法兰绒汗衫,厚青呢衣裤,全穿上了。还怕出去着了凉,试着把小棉袄絮在汗衫上面,可是棉袄太肥,穿上系不上裤子。于是骂了鬼子衣裳一顿,又把棉袄脱下来了……要不怎么说,东西文化不能调和呢!看,小棉袄和洋裤子就弄不到一块儿!”
他对“西化”论和“东化”论似也无好感。《老张的哲学》中这样表现二论的异同:“老张与小山所代表的时代不同,代表的文化不同!老张是正统的十八世纪的中国文化,而小山所有的是二十世纪的西洋文明。”而在小说中这两种“文化”的表现都是“吃人”。《赵子曰》讽喻的对象是一群“欧化成熟的新青年”;《二马》中则讽刺地谈到“到欧洲宣传中国文化的先生们”。
不过,尽管老舍对各种流行的“文化论”总体上均不看好,但这并不妨碍他对上述文化先行者的某些理论成果进行独具个性的吸收或改造。
老舍在《二马》中有对本土传统文化的精彩概括——“出窝儿老”——其来源似与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1年)中提出的中国文化“早熟”论有关。梁在其文中指出:“西洋文化的胜利,只在其适应人类目前的问题,而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在今日的失败,也非其本身有什么好坏可言,不过就在不合时宜罢了……(他)把以后方要走到的提前走了,成为人类文化的早熟。”
老舍早期作品中有对“主义”和“问题”的嘲弄——赵四坚持“无辈数主义”(《老张的哲学》);伊牧师崇尚“英国世传实利主义”,老马不懂“三民主义”,小马心仪“国家主义”,玛力“几乎要信”“社会主义”(《二马》);莫大年干脆说道:“什么乱嚷这个主义那个问题咧,全叫瞎闹!”他信奉“不傻蛋主义”,赵子曰崇拜“新武化主义”,武端则取“洋服主义”(《赵子曰》)。——这些都似针对美国哲学家杜威及其弟子胡适的理论而发。1919年4月杜威来华宣讲“实验主义”,同年7月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与之呼应。
这也不赞同,那也不赞同,老舍其时的“文化”观是什么呢?也许可以称为“实干”论。《赵子曰》中李景纯赴死前有番感言:“应当及早预备真学问……几时在财政部作事的明白什么是财政,在市政局的明白市政,几时中国才有希望;要老是会作八股的理财,会讲《春秋》的管市政,我简直的说:就是菩萨,玉皇,耶稣,穆哈莫德,联盟来保佑中国,中国也好不了!”《二马》中李子荣的理想并不高远,小马却赞扬他道:“他只看着事情,眼前的那一钉点事情,不想别的,于是也就没有苦恼。他和狮子一样,捉鹿和捉兔用同等的力量,而且同样的喜欢;自要捉住些东西就好,不管大小。李子荣是个豪杰,因为他能自己造出个世界来!他的世界里只有工作,没有理想;只有男女,没有爱情;只有物质,没有玄幻;只有颜色,没有美术!”
老舍早年的“文化”观似偏离时代主流甚远,却与稍早时候鲁迅在《文化偏至论》(1906)中的看法非常接近。鲁迅看到了当时中西两种文化的恶性嫁接,警觉道:“往者为本体之偏枯,今则获以交通传来之新疫,二患交伐,中国之沉沦遂以益矣!”他们的忧虑是相通的。
二
老舍对西方都市文化的体认(仅以老伦敦的文化为例)大致完成于1928年至1936年间,即从创作《二马》之时起至抗战爆发前夕。
由于作者在创作《二马》时有着明确的“比较中英两国国民性的不同”(《我的创作经验》)的动机,因此,要讨论老舍的西方都市文化观,不能不细读这部作品。
该小说“第一段”中再现的“礼拜下半天”伦敦海德公园“玉石牌楼”附近的“热闹”场面堪称作者对伦敦都市文化(英国国民性)的象征性的描摹。在这座“玉石牌楼”(大理石拱门)附近是海德公园著名的“演讲者之角”。19世纪末起,这里又成为英国各政党各阶层集会和示威游行的场所。在老舍的笔下,这里有各党派的激烈角逐,有不同政治主张的激情展示,更有各阶层人士的率意而为的个性表现。显然,作者有意借此场景浓缩表现伦敦市民对世界事务的参与意识、独立精神和个性追求,而这种进取的文化精神正是老一辈中国人如老马所匮乏的,也是小一辈中国人如小马所渴望的。
该小说对伦敦普通市民的生活及精神层面也有精彩的表现,如果撇开作者所深恶痛绝的英国人的种族偏见和殖民情结暂且不论,那么可以认为,作者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伦敦市民文化并无多少贬辞。当年英国经济正处于大萧条期,“成千论万的人”“抓不到面包”(《我的几个房东》),但在《二马》中,作者笔下的英国普通市民却自信且自尊地生活着,他们都有独立的经济来源,也都有独立的精神追求。反观老马和小马,前者虽吃穿不虞,却没有独立的精神追求;后者向往精神上的独立,却不能经济自立。尽管老舍在后来的散文作品中认定“(英国人)这种独立的精神是由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逼出来的”(《我的几个房东》),但仍掩饰不了内心的艳羡之情。
该小说对其时西方都市文化的新趋向有一段精彩的描述:“欧洲大战的结果,不但是摇动各国人民的经济基础,也摇动了人们的思想:有思想的人把世界上一切的旧道德,旧观念,重新估量一回,重新加一番解释。他们要把旧势力的拘束一手推翻,重新建设一个和平不战的人类。婚姻,家庭,道德,宗教,政治,在这种新思想下,全整个的翻了一个筋斗;几乎有连根拔去的样子……英国人是守旧的,就是守旧的英国人也正在这个怒潮里滚。”
这番评说只有放在当年的文化环境中才能看出其价值。钱理群曾撰文指出“20世纪初,西方工业文明自身的矛盾、缺陷已经越来越显露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一开始几乎是毫无保留地赞成和接受西方工业文明的中国人(知识分子),在更深入地了解西方工业文明后,发现并不是自己所想象的那么好,还有许多毛病、弊端,很多人就转变了态度。很多人都经历过这个由崇拜到反对,由崇扬西方文化到崇扬传统文化,由西方主义转移到东方主义的过程,最早是林纾、严复、梁启超等人”钱理群:《鲁迅的西方文化观》,《中州学刊》1999年第2期。。老舍在英国生活了五年,他对西方文化的了解显然比林、严、梁诸人更真切且“更深入”,他不仅发现了西方文化的“摇动”,更发现了其“守旧”表象下的强大的更生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