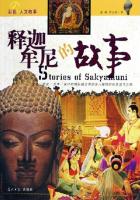“一辈子作艺,三辈子遭罪。”老舍借“窝囊废”之口,点出了旧艺人的悲苦命运。小说《鼓书艺人》真实深刻地刻画那些蹈入卖艺这一“贱业”、活在世上矮人三分的艺人们,细致描绘了旧时代底层艺人“被欺凌与被侮辱”的卖艺生活。年轻女艺人秀莲在方二奶奶的眼里,只有“卖钱”的价值,根据自己卖唱的家庭出身经验,秀莲一定要走上卖艺又卖身的低贱堕落的路的。所以在秀莲需要有人疼,希望有人能给她出主意、开导、安慰的时候,方二奶奶从来没有好脸色,并且总是粗声粗气地说“贱货”、“只有你那臭×值俩钱!”这样羞辱秀莲。姐姐大凤拒绝关怀秀莲,认为抱来的妹妹不过是男人的玩物,而她可是个有身份的闺女。只有方宝庆和“窝囊废”兄弟二人真正关心秀莲。方宝庆担忧秀莲受到不良风气的玷染,学坏了,对秀莲说:“从前人都看不起戏子和唱大鼓的,不过比奴才和要饭的好些罢了。可是如今改样儿了。只要我们行得正,坐得直,人家就不能看轻咱们。”老舍:《鼓书艺人》,《老舍全集》第6卷,第53页。虽然方宝庆和秀莲都坚定认为,只要不自轻自贱,人家就不能轻看,抵御来自旧习俗、旧传统和黑恶势力的压迫和凌辱;尽管方宝庆和秀莲等人本本分分地做人,认认真真地卖艺;可是,他们还是不能摆脱厄运:哥哥“窝囊废”被飞机炸死,书场毁于火海,亲生女儿大凤被副官骗去又抛弃,秀莲也被特务蹂躏。“而这,就是现实,就是社会对他的犒劳。他叹了一口气。他从来没做过亏心事,一向谨慎小心,守本分,一直还想办个学校,调教出一批地道的大鼓艺人。现在一切都完了。所有攒的钱,都给窝囊废办了后事。姑娘出嫁,他的病,花费也很大。钱花了个一干二净,连积蓄都空了。生活费用这么高,不干活就得挨饿。”老舍:《鼓书艺人》,《老舍全集》第6卷,第155页。“艺人都是贱命,一钱不值”,方宝庆只好以“今天脱下鞋和袜,不知明天穿不穿”的俗语来慰藉自己。
在《四世同堂》中,老舍塑造了一个一生只爱演戏唱戏、生活在“戏中世界”、不问人间世事的小文夫妇。他们一开始对日本人的侵略本质认识不清,参加了日本人举办的义赈游艺会。小文在舞台的演出极为投入,似乎忘了自己,“探着身子,横着笛,他的眼睛盯住了若霞,把每一音都吹得圆,送到家。他不仅是伴奏,而是用着全份的精神把自己的生命花在音乐之中,每一个声音都像带着感情,电力,与光浪,好把若霞死亡身子和喉音都提起来,使她不费力而能够飘飘欲仙”。老舍:《四世同堂》(下),《老舍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838页。杀人成性的侵略者因为文若霞没有满足他们的淫欲而在舞台上枪杀了小文夫妇。残暴的日本侵略者并未因为小文夫妇的顺从,而放弃对他们的迫害。柔顺、唯美、别无所求的小文夫妇也没有逃脱悲惨的艺人命运。
老舍如实地展现了不同时代背景下的旧艺人的生活,描绘旧艺人在新旧时代交替时期和轻视艺人的传统不良习俗中的悲剧性命运。不管是无奈的顺从,还是拼命的挣扎,也许他们能逃避肉体的苦难,但也摆脱不了与生活、命运紧紧连在一起的精神痛苦。
老舍对底层旧艺人的痛苦不仅是亲眼目睹,而且是感同身受的。老舍自称“写家”,从不以“作家”自居,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老舍本身就是旧艺人中的一员,是靠“写东西”卖文为生的艺人。自身就是“旧艺人”中一员的老舍以与旧艺人同甘苦、共命运的心心相通,审美观照下的为生存、为填饱肚子而挣扎的语言文字,字字皆是血泪之语、心痛之声。
五、“大杂院”里的无名穷人群像
作为一座古老都城,北京不仅有风景秀美的山光水色与堂皇富丽的高大宫殿,而且也有与它极不协调的贫民区——北京的老式住宅“大杂院”。在现代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大量无处安身的城市底层穷人和急剧增长的人口使北京这些四合院变成了成分复杂、多家杂居的“大杂院”。因此,四合院由本来单一的一家一户居住变成了几家,甚至十几家、几十家住在一所院子中,彼此没有了过去的亲缘关系。
大杂院,顾名思义,一是大,二是杂。“大”指的是地域,“杂”便是指居住者的成分。社会中上阶层的人在老北京住的是四合院或是单独的院子,底层穷苦人多半住在大杂院里。一家十几口窝在一间小房子里,转个身都会碰到人是常有的事情,但是他们的穷苦远不止是房子小的问题。大杂院里的人都是吃上顿没下顿、孩子多却养不起的,男人们白天出去挣“嚼谷”,可怜的女人们在家做一些洗衣服等辛苦赚钱的活,孩子们就自顾自地吵闹玩耍。等到晚上,男人们回来了,一天的劳累与不顺心总要拿这些在家的女人们当发泄出气的工具。
老舍出生于一个城市底层穷人家庭,在大杂院里度过艰难的幼年和少年时代。大杂院的日常生活,使他从小就熟悉车夫、手工业工人、小商贩、下等艺人、娼妓等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城市贫民,深知他们的喜怒哀乐。大杂院的艺术熏陶,使他从小就喜爱流传于市井里巷的传统艺术(如曲艺、戏剧)。“大杂院”铸就了老舍心灵世界的苦难的阴影,成为老舍一生都挥之不去的、烙入灵魂深处的精神记忆。因此,在老舍审美想象的世界里,老舍差不多在每一个作品里都写到“大杂院”或与“大杂院”相关的记忆与事物。“在中国现代作家中,老舍的出身十分特殊:与那些从书香世家、豪门大户、破落人家、小康家庭中走出的作家不同,他是从北京的小胡同、贫困的大杂院里走出来的贫民作家。套用老舍的话说就是,‘童年习饥饿’,少年饮酸辛;他看惯了下层市民的悲欢离合,听惯了劳动者痛苦的呻吟,经历了贫困艰辛的生活,对大杂院贫民的悲惨生活和悲剧命运有切身的感受,他的情感意识和审美心理、人生态度和创作追求大都与大杂院密切相关。”石兴泽:《平民作家老舍——关于老舍的一种阅读定格》,《民族文学研究》2006年第4期。老舍研究专家石兴泽先生在多年研究中分析出“大杂院”这一城市底层穷人居住空间对于老舍文学创作的重要意义。“大杂院”只是偌大北京城的一个小片断,老舍就在这个抛却不去的“片断”上展现出了老北京的风土人情,展示出北京城市底层的大多数穷苦人的生存状况——物质的、心理的、精神的挣扎与痛苦。
老舍在《骆驼祥子》中描写祥子在落入虎妞的圈套后就住进了大杂院。这也意味着祥子开始步入一个他从前一直回避的、最底层的穷人世界。从这里开始,老舍的审美观照不但是描写祥子的生活,而且是转向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社会底层各式各样穷人的描写——“大杂院”世界中的底层穷人。
祥子住进大杂院的空间转移,老舍的审美视线也随之发生了转向。老舍用饱含深切同情的笔触,尽量客观真实地展现了他记忆中的大杂院“最低层穷苦人群”的悲惨凄苦生活。相比较于《骆驼祥子》里的“祥子”、《月牙儿》中的妓女“我”、《我这一辈子》中的巡警“我”和《鼓书艺人》中的女艺人秀莲,这个“大杂院”中“有的拉车,有的作小买卖,有的当巡警,有的当仆人”,他们的生活命运更加可怜、更加悲惨,他们彻底地坠入万劫不复的苦难深渊之中,这里没有一线生机、一线阳光,有的只是无边无沿的“几代世袭的”、“头朝下”的黑暗。
1951年初老舍创作的话剧《龙须沟》上演,获得巨大成功。剧本通过大杂院几户人家的悲欢离合,写出了历尽沧桑的北京和备尝艰辛的城市穷人正在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是献给新中国的一曲颂歌。剧本中人物生活的空间依然是一个“大杂院”,第一幕开篇就是对“龙须沟”这条臭水沟及其两边的“大杂院”场景的描绘:“这是北京天桥东边的一条有名的臭沟,沟里全是红红绿绿的稠泥浆,夹杂着垃圾、破布、死老鼠、死猫、死狗和偶尔发现的死孩子。附近硝皮作坊、染坊所排出的臭水,和久不清除的粪便,都聚在这里一齐发霉……沟的两岸,密密层层的住满了卖力气的、耍手艺的,各色穷苦劳动人民。他们终日终年乃至终生,都挣扎在那肮脏腥臭的空气里。他们的房屋随时有倒塌的危险,院中大多数没有厕所,更谈不到厨房;没有自来水,只能喝又苦又咸又发土腥味的井水;到处是成群的跳蚤,打成团的蚊子,和数不过来的臭虫,黑压压成片的苍蝇,传染着疾病……遇到六月下连阴雨的时候,臭水甚至带着死猫、死狗、死孩子冲到土炕上面,大蛆在满屋里蠕动着,人就仿佛是其中的一个蛆虫,也凄惨地蠕动着。”老舍:《龙须沟》,《老舍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439页。这个臭水沟边的“大杂院”简直就是“人间地狱”!老舍详细展现了这个“人间地狱”里挣扎的穷人虽然时时刻刻受到臭水沟的“污染”,但是他们最迫切的问题还是来自最基本的温饱问题,他们最急于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填饱肚子,因此“臭气熏天”的环境在“王大妈”看来:“这儿不分男女,只要肯动手,就有饭吃;这是真的,别的都是瞎扯!这儿是宝地!要不是宝地,怎么越来人越多?”同上,第446页。在吃饭、填饱肚子就是天大的难事的穷人看来,房租最少、食物最廉价的“臭水沟”大杂院就是生存得以获得最低保障的“宝地”,显然这是生活在最底层穷人的最无奈的自我慰藉。
随着新社会的建立,“臭水沟”、“大杂院”和大杂院里的穷人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杂院已经十分清洁,破墙修补好了,垃圾清除净尽了,花架子上爬满了红的紫的牵牛花。赵老的门前,水缸上,摆着鲜花。丁四的窗下也添了一口新缸。满院子被阳光照耀着。”同上,第497页。“被阳光照耀着”的大杂院,具有浓重的象征意味,生活在黑暗的“人间地狱”的穷人们终于见到光明的新世界、过上新生活了。
比较于《骆驼祥子》、《龙须沟》这样的长篇幅作品,老舍在短篇小说中也精彩地描写了大杂院中的无名穷人。《柳家大院》就是一个出色的短篇。在《柳家大院》中,“大杂院”不仅是城市最底层穷人的庇护之所,而且也是病态的传统思想文化依旧顽固存留之地。“北京是800年故都,每个角落都渗透着中国传统文化;大杂院物质生活贫困,精神生活守旧,是传统文化最顽固的堡垒。”石兴泽:《从女性形像塑造看老舍文化心理的传统走向》,《聊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底层穷人一方面是病态的封建思想文化的受害者,另一方面他们又是这些病态的封建思想文化的坚定遵守者。封建思想文化与底层穷人就这样交错地结合在一起。
在《柳家大院》的“大杂院”里,老舍向我们展示一个几千年来在场而“失语”的受迫害者——女性被压迫者。王家小媳妇的死,不仅仅是因为穷困的逼迫,主要还来自传统封建思想文化对女性的压迫与毒害。“大杂院”不仅是穷人居住的庇护之地,而且也是封建思想文化的“藏污纳垢”之地。深受传统思想文化影响的底层穷人,也具有其病态的、非人性的思想意识,且会自觉不自觉地加入到“迫害者”的行列中去。
因此,老舍在对底层穷人如祥子、赵四、白巡长、方宝庆、秀莲、妓女“我”等具有美好善良品质的人物进行详细刻画描写、给予满腔同情热泪的同时,也对底层穷人中的一些丑陋思想、恶人进行深刻反思,描写了如《鼓书艺人》中的唐家、《四世同堂》中的“大赤包”、《柳家大院》的老王父女等人的丑恶嘴脸。“世界上不应当有穷有富。可是穷人要是狗着有钱的,往高处爬,比什么也坏。老王和二妞就是好例子。”老舍:《柳家大院》,《老舍全集》第7卷,第85页。这充分显示了老舍对“穷人”的深刻思考,不是基于某种片面的道德或阶级感情认知,而是在“人性”意义上的全面认识,是其“城市底层”叙述空间所生产的独特文学形象群。
“空间既是抽象的又是具体的,既是均质性的又是断离的。它存在于新兴的都市中,存在于绘画、雕塑和建筑中,也存在于知识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空间便成了这种再生产的场所,包括都市的空间、娱乐的空间、所谓的教育的空间、日常生活的空间等等。”[法]亨利·勒菲弗:《空间与政治》,李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3页。空间不仅是一个物理意义上的几何概念,而且是一个精神意识的、具有“生产性”文化存在其背后隐喻着更深层的精神、文化、文明的差异,隐含着秩序、权力与话语的等级区隔。老舍对“城市底层”空间的独特发现和审美书写,形成了想象城市的另一种形式和审美可能性,为新世纪中国城市文学提供了一种极为宝贵的、异质性的、属于中国也是第三世界的城市审美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