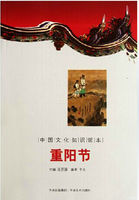再看郁达夫与王映霞的恋爱对其创作的影响。1927年春,郁达夫与王映霞陷入热恋。由于王映霞是杭州人,这段时间两人时常往来于上海与杭州,这在郁达夫笔下有生动的描述。4月13日,郁达夫搭上驶往杭州的客船,“晚上独酌白兰地酒,坐到天明”,只待与映霞相会。他在当日致王映霞信中这样吐露:“我们的运气真不好,弄得这一个韶光三月,恋爱成功后的第一个三月,终于不能在一块儿过去。不过自古好事总多魔劫,这一个腐烂的时局也许是试探我们的真情的试金石。映霞,我想我们两人这一回相见的时候,恐怕情热比从前还要猛烈,这是一定的。”
在杭州的这一个礼拜,是郁达夫最幸福的时光,他几乎天天都与王映霞行走在西湖的山水之间。既有山水美景,又有美人相伴,不由得使他诗意盎然:这一天天气又好,人又只有我们两个,走的地方,又是西湖最清净的一块,我们两人真把世事都忘尽了,两人坐在理安寺前的涧桥上,上头看着晴天的碧落,下面听着滴沥的泉声,拥抱着,狂吻着,觉得世界上最快乐,最尊贵的经验,就在这一刻中间得到了,我对她说:“好象在这里做专制皇帝。我好象在这里做天上的玉皇。我觉得世界上比我更快乐,更如意的生物是没有了,你觉得怎么样?”
她也说:“我就是皇后,我就是玉皇前殿的掌书仙,我只觉得身体意识,都融化在快乐中间;我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一个多月后,郁达夫将他与王映霞的事正式公开,但那时郁达夫的身体已经很差,对此王映霞也很清楚。事实上,郁达夫幼年就体弱多病,成年后又饮食作息极不规律,以至他日记里时常有头痛、胃痛、心散神迷种种记录,在其散文《王二南先生传》里也有这样的记述:在这一种四面楚歌的处境之下,孑然一身,逃到杭州的时候,我精神的萎顿,当然可以不必说起,就是身体,也旧疾复发,夜热睡汗等症状,色色俱全,痰里头更重见了点点的血丝。又因为在上海租界上乱避乱躲的结果,饥饱不匀,饮酒过度,胆里起了异状,胆汁溢满全身,遍体只是金黄的一层皮和棱棱的一身骨,饭也吃不进,走路也提不起脚跟来了。郁达夫与王映霞热恋时才三十出头,正该是年富力强的时期。郁达夫自己也很明白,所以不止一次要戒酒养身,他自言:“近来顿觉衰老,不努力,不能作出好作品来的原因,大半在于身体的坏。戒酒戒烟,怕是于身体有益的初阶,以后当勉行之。”只是话虽如此,实行起来却不免困难。
移家杭州以后,郁达夫除了照旧为报社写稿谋生之外,还接任杭州作协理事一职以及杭州《东南揽胜》的编委,日常交往自然也频繁起来。加之王映霞也喜欢交际,所以几乎每天都有客人来访:午后来客不断,共来八人之多,傍晚相约过湖滨,在天香楼吃夜饭。(1935年9月1日)
傍晚秋原来,与共谈此事,遂偕去湖上,痛饮至九点回寓。(9月3日)
晚上,过湖滨,访友二三人,终日不曾执笔。(9月5日)
晚上刘开渠来,请去吃饭,并上大世界点了女校书的戏,玩到了十二点才回来,曾请挂第一牌的那位女校书吃了一次点心。(9月6日)
午后学生丁女士来访,赠送八月半礼品衣料多件,我以《张黑女志》两拓本回赠了她。晚上在太和园吃饭,曾谈到上旅顺、日本去游历的事情。(9月7日)
晚上月明,十时后去湖上,饮酒一斤。(9月8日)
今晚又有约,丁小姐须来,午后恐又不能写作。(9月9日)
丁小姐去上海,中午与共饮于天香楼,两点正送她上车,回来后小睡。晚上月明如昼,在大同吃夜饭。(9月10日)
约开渠、叶公等来吃晚饭,吃完鸡一只,肉数碗,亦可谓豪矣。……晚上无月,在江干访诗僧,与共饮于邻近人家,酒后成诗一首。(9月12日)
中午有友人来谈,与共饮至三时;写对五副,屏条两张,坑屏一堂。晚上洵美自上海来访,约共去黄山,谢而不去。(9月14日)
晚上在湖上饮,回家时,遇王余杞途中。即偕至寓斋,与共谈别后事,知华北又换一局面。约于明日,去同游西湖。(9月18日)从郁达夫日记中可以看出,短短半个多月里他出门与友人吃饭喝酒次数就多达十多次,还时常独自跑去西湖边饮酒。郁达夫在杭州的这几年里,日常生活一直如此,尽管王映霞也多次劝其戒烟戒酒,但始终未能见效。1935年冬,正是郁达夫四十岁生日,他在日记里回忆说:“今天为我四十生日,回想起十年前此日在广州,十四五年前此日在北京,以之与今日一比,只觉得一年不如一年。人生四十无闻,是亦不足畏矣,孔子确是一位有经验的哲人。”同上,第312页。然而四十岁生辰时他内心却充满了寂寞与徘徊,应该是多少与他的身体和心理状况相关的。
像这样浓艳的暮春的下午,我居然能把放心收得下,坐在这冷清清的案头,记这一条日记,而预排我的日后的课程,总算可以说是我的进步;但反过来说,也未始不是一种衰老现象的表白,人到了中年,兴趣就渐渐杀也。(1936年4月1日)同上,第342页。
初春浓酣,一直带给他无限的创作灵感与爱情的回忆,然而此时却似有物是人非的惆怅之感,可以说,郁达夫四十之后所写的这段话,实在是他对人生无常的深沉感叹。
今天,当我们追溯杭州、西湖与民国时期浙籍文人之关系时,会发现每一位文人身后,都铺满了层层历史的痕迹,他们的日常生活为文学创作填充了风花雪月与柴米油盐的真实。一个时代已经过去,他们经历着战争与和平的考验,他们肩负着历史转折的重大责任,负担越是沉重也许越是让他们接近朴实的大地,越是让他们接近真实的存在。
此外,笔者以为,民国时期文人对于个人经济收入之所以如此重视,当与当时的社会动荡、物价高企,以及文人职业性质所决定的收入不稳定等因素有关。在浙籍文人群体中,本来在大中学校任教者很多。自民国初年起,伴随着现代教育制度的建立,教师在民国时期本应为收入虽然不高,却也不低,且相对稳定的一个职业。但长年的军阀混战所导致的社会动荡以及统治集团对教育的忽视,使得单纯依靠从教赡养家庭已经不可能,我们注意到当时很多文人都创作有表现民国时期各类教师生活的小说,而政府欠薪导致教师生活艰难往往是此类小说常见的内容。就浙籍文人而言,本书所论述的几个代表文人(除却柔石、殷夫等一切青年作家外)在当时整个文人集团中,大致属于生活相对稳定且比较优裕者。除却动荡时期和战争时期外,他们的日常生活还是较为从容的,这也自然会在他们的创作和学术研究中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