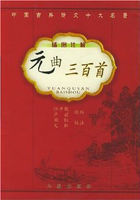《墨子·所染篇》云:“子墨子言:见染丝者而叹曰: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必而已,则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
此节下文即推言国亦有染,士亦有染,与《吕氏春秋》文略同。或谓此本《吕》氏所推说,非墨子之本文。汪中、吴汝纶说同。然此今姑弗具论,特墨子见染丝而叹,则必为事实。其寓意盖谓人之善恶由乎师友之习染,盖亦注意教育之论矣。
墨子之于教育,其对于受教者甚不主张盲从。故《法仪篇》云:“当皆法其父母奚若?天下之为父母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父母,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为法。当皆法其学奚若?天下之为学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学,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为法。当皆法其君奚若?天下之为君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君,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为法。”
此言虽非专为教育而发。然可见墨子之于受教者,对于家庭教育,学校育教,国家教育,均有仁不仁之辩,而无绝对服从之心要矣。而《荀子·致士篇》则云:“师术有四,而博习不与焉。尊严而惮,可以为师;耆艾而信,可以为师;诵说而不陵不犯,可以为师;知微而论,可以为师。”
《礼论篇》又云:“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
荀子之言如此。盖主张绝对服从者。此亦儒墨之所由大异也。然墨子之教人,亦力持干涉主义。《耕柱篇》云:“子墨子怒耕柱子,耕柱子曰:‘我毋俞于人乎?’子墨子曰:‘我将上太行,驾骥与羊,子将谁驱?’耕柱子曰:‘将驱骥也。’子墨子曰:‘何故驱骥也?’耕柱子曰:‘骥足以责。’子墨子曰:‘我亦以子为足以责。’”
则其督责教者之严,已可概见。证以《尚同·中篇》所谓上之所是,亦必是之;上之所非,亦必非之;则其干涉之精神,益可知矣。盖其主张绝对干涉,故其终也,虽与前说仁不仁之辩有矛盾,亦不自知矣。
然墨子之人格极高,其为孔老所不及者有二:一曰:兼爱精神。
二曰:牺牲精神。
“《孟子·告子篇》云:‘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陈沣云:‘墨子之学,以死为能。摩,犹糜也糜,烂也。糜烂而死之谓也。’”
“《荀子·富国篇》云:墨子之言,昭昭然为天下忧不足。”
此孟荀攻击墨子之言也。然墨子兼爱与牺牲之精神,可谓形容毕尽矣。《吕氏春秋·爱类篇》云:“公输般为云梯,欲以攻宋,墨子闻之,自鲁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于郢。”
则其牺牲一己以爱人,可谓勇矣。老子《道德经》第六十七章云:“慈故能勇。”
《韩非子·解老篇》释之云:“圣人之于万事也,尽如慈母之为弱子虑也,故见必行之道;见必行之道,则其从事亦不疑;不疑之谓勇;不疑生于慈;故曰慈故能勇。”
然则墨子其有得于老子之慈者乎:韩非其有见于墨子之勇者乎?不然,非之智盖不足以语此。然老子虽能言此,而老子之行事类此者却未之见也。至儒家则虽说汎爱,而行尚中庸,下者且以哗世取宠,不足语于牺牲也。
墨子之人格既如此,故其教育主义亦不外此二者。今其书各篇上自《亲士》、《兼爱尚同》诸篇,下至《公输》、《备城门》诸作,殆莫非欲贯彻其兼爱与牺牲之精神者也。然约其为教育之恉,尚有六端。兹举之如下:一曰:贵义。
“《贵义篇》,子墨子曰:万事莫贵于义。今谓人曰:予子冠履,而断子之手足,子为之乎?必不为。何故?则冠履不若手足之贵也。又曰:予子天下,而杀子之身,子为之乎?必不为。何故?则天下不若身之贵也。争一言以相杀,是贵义于其身也。”
“墨子之所谓义,盖即含有牺牲自己以兼爱人之意。故墨子本书义字,本皆作羛,从羊从弗。见说文。从羊与善字同意,兼爱之谊也。去我从弗,有排除为我主义,而以绳墨自矫,以备世患之意。《庄子·天下篇》语,弗古文拂字,即矫拂之谊也。今墨子书皆改羛作义,易从弗为从我,失墨子之本谊,甚矣。”
二曰:尚意。
“《耕柱篇》,巫马子谓子墨子曰:‘子兼爱天下,未云利也。我不爱天下,未有贼也。功皆未至,子独何自是而非我哉?’子墨子曰:‘今有燎者于此。一人奉水将灌之;一人掺火将益之;功皆未至,子将何贵于二人?’巫马子曰:‘我是彼奉水者之意,而非夫掺火者之意。子墨子曰:吾亦是吾意而非子之意也。’”
“此则凡事皆求其是,成败利钝,皆所不顾。董仲舒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者,其勇盖近此。而一尚实利,一尚仁义,则其大异也。”
三曰:尚分工。
“《耕柱篇》,治徒娱,县子硕问于子墨子曰:‘为义孰为大务?’子墨子曰:‘譬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然后墙成也。为义亦犹是也。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
然则事无大小,凡能尽己力以益于人者,均在所当为,而无贵贱之分矣,反是而较其大小,计其价值而后为之,则天下之公益事可为之者少矣。
四曰:尚独行。
“《贵义篇》,子墨子自鲁即齐,过故人,谓子墨子曰:‘今天下莫为义,子独自苦而为义,不若已。’子墨子曰:今有人于此,有子十人,一人耕而九人处,则耕者不可以不益急矣。何故?则食者众而耕者寡也。今天下莫为义,则子如劝我者也。王念孙云:如宇古或训为宜。”
此其特立独行之志,为何如邪?
五曰:尚实行。
“《耕柱篇》,子墨子曰:世俗之君子,贫而谓之富则怒;无义而谓之有义则喜;岂不悖哉?”
此则循名责实,不特察人用人当如此,自处亦当如此,不容有毫厘之文饰者矣。
六曰:尚创作。
“《非儒篇》,儒者曰:‘君子必服古言然后仁。’应之曰:‘所谓古之言服者,皆尝新矣;而古人言之服之,则非君子也。然则必服非君子之服,言非君子之言,而后仁乎?’又曰:‘君子循而不作。’应之曰:‘古者羿作弓,伃作甲,奚仲作车,巧垂作舟。然则今之鲍函车匠,皆君子也;而羿伃奚仲巧垂,皆小人邪?且其所循,人必或作之;然则其所循,皆小人道也。’”
此可见墨家创作之精神矣。
唯其如上六者所说,故其教育遂能收其大效。
《备梯篇》,禽滑厘事子墨子三年,手足肼胝,面目黧黑,役身给使,不敢问欲。子墨子甚哀之。
《吕氏春秋·尚德篇》,孟胜为墨者巨子,善荆之阳城君。阳城君令守于国,毁璜以为符,约曰:“符合听之。”荆王薨,群臣攻吴起兵于丧所,阳城君与焉。荆罪之。阳城君走。荆收其国。孟胜曰:“受人之国,与之有符。今不见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其弟子徐弱谏孟胜曰:“死而有益阳城君,死之可矣。无益也,而绝墨者于世,不可。”孟胜曰:“不然,吾于城阳君也,非师,则友也:非友,则臣也:不死,自今以来,求严师必不于墨者矣;求贤友必不于墨者矣;求良臣,必不于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义,而继其业者也。我将属巨子于宋之田襄子,田襄子贤者也,何患墨者之绝世也?”徐弱曰:“若夫子之言,弱请先死以除路。”还殁头前于孟胜,因使二人传巨子于田襄子。孟胜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人。以致令于田襄子,欲反死孟胜于荆,田襄子止之曰:“孟子已传巨子于我矣。”不听,遂反死之。
《吕氏春秋·去私篇》,腹为墨者巨子,居秦,其子杀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长矣,非有它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诛矣。先生之以此听寡人也。”腹对曰:“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此所以禁杀伤人也,夫禁杀伤人者。天下之大义也。王虽为之赐,而令吏弗诛。腹不可不行墨者之法。”不许惠王而遂杀之。
《淮南子·泰族训》,墨子服役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不旋踵,化之所致也。
凡此皆可见墨子教育力量之伟大。夫死者人之所至难,而墨子之徒,乃乐为之如此。墨子非有特殊感化力,曷足致此?观其百舍重茧以往求宋,预知公输般之欲杀己,而犹亲往焉。见公输篇其视死如归,墨子盖身自行之。故弟子亦相率而效之也。至其木木鸢车之巧,见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九攻九却之术,乃其技之小者矣。
虽然,墨子之教,虽能化于少数之弟子;而为之太过,决不能久。故《庄子·天下篇》云:“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法,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独能任,奈天下何?离于天下,其去王也远矣。”
然则《孟子》所谓“天下不之杨则之墨,”《吕氏春秋》所谓“孔墨徒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者,其说非邪?曰:此盖似是而非之墨。犹战国末似是而非之儒耳。不然,则真墨之众,充满六国,本墨子止楚伐宋之志以救六国;行禽滑釐等守宋之事以守六国;抱孟胜必死之心以忠六国;秦兵虽强,岂能灭六国如折枯推朽之易哉?老子曰:‘强梁者不可以为教父。’岂非墨子之谓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