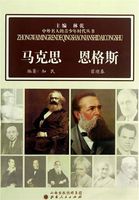我认为,只有在我们结婚以前那几个无上幸福的星期里我所十分珍惜、后来又丰富了我们在莫斯科的生活的那种和丈夫经常不断的精神上的交流才能使我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所向往的牢固与和睦的家庭建立起来。为了挽救我们的爱情,解除我的不安和苦恼,有必要离开大家一个时期,哪怕两三个月也好。我深信,在这以后,我和丈夫就会一辈子亲密无间,没有人能把我们拆散了。但是上哪儿去弄一笔钱,供我们去进行这次必不可少的旅行呢?我前思后想,蓦地,一个想法闪过我的脑海:“为了这次旅行,我是否能牺牲我的嫁妆呢?这样,我的幸福就可以保全了。”
这一想法逐渐制服了我,虽然把它付诸实现存在某些困难。首先我自己就很难下决心作出这样的牺牲。我已经说过,我虽然已经二十岁,但有许多地方还像孩子,对年轻人来说,像家具、服装这一类东西具有很大的意义。我特别喜欢我的钢琴,我的可爱的小桌和书架,我的所有那些漂亮的、不久以前添置的家具。我舍不得失掉这些东西,害怕它们再也不能收回了。
我还担心这会引起母亲的不满。我出嫁不久,还处在她的影响下,害怕使她伤心。我的一部分嫁妆是用她的钱置办的。我想:“如果妈妈责怪我的丈夫对他的亲戚过分偏袒,从而怀疑他对我的爱情,那可怎么办?她总是把自己孩子们的幸福看得重于自己的幸福,到那时候,她会多么难受啊!”
我在这种犹豫不决和疑虑重重中度过了不眠之夜。清晨五点钟响起了晨祷的钟声,我决定上我们家对面的升天教堂去祈祷。
跟平时一样,参加祈祷仪式使我大受感动:我热烈地祈祷着,哭泣着,从教堂里出来的时候,我的决心增强了。离开教堂后,我不想回家,而是前往我母亲家。妈妈见我去得这么早,又加眼睛带有泪痕,吓了一跳。在我所有的亲属中,只有她一个人知道我的家庭生活不顺心。她常常数落我没有能耐,无法叫帕维尔·阿列克桑德罗维奇对我持尊敬的态度,从而改变我的处境。还有一个情况也使她感到气愤:我过去一直忙于工作,在工作中寻找精神上的乐趣,而现在却整日无所事事,只是款待那些我所不感兴趣的客人,给他们解闷儿。她是瑞典人,总是用西方的、比较文明的观点看待生活,她担心我们俄国人那种杂乱无章、一味好客的生活会断送在教育中培养起来的真本领。妈妈知道我缺乏那种把一切事情办得恰如其分的能力和处世经验,因而对我们到国外旅行一举寄予很大希望。她打算在秋天我们回来以后邀请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移居到她的房子里。到那时,我们将有不用花钱的好住所,再说亲戚们由于路远,就不会每天来我们家。帕维尔·阿列克桑德罗维奇也不会想住在“穷乡僻壤”,——这是他对我们这个地区的轻蔑称呼,——自然会留在埃米莉娅·费奥多罗芙娜那里。这样,我们和帕维尔·阿列克桑德罗维奇分手,就不像是由于家庭不和,而是出于他本人的意愿。
我母亲听到我们的出国计划落空,我将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家的人在公用的别墅里一起度夏,吃了一惊。她了解我那独立不羁的性格和年轻人的执拗劲儿,怕我经受不住,以致造成家庭悲剧。
她立即同意我把自己的东西全部抵押出去的计划,这使我欣喜万分。我问,她是否为她送我那些嫁妆感到惋惜,妈妈回答说:“自然惋惜,但是你既有失去幸福的危险,不这样做又有什么别的办法呢?你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是两个很不相同的人,如果现在合不来,那就永远别想合得来了。必须在节日以前,趁新的复杂情况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尽快离开这儿。”
“不过,我们是否能在节日以前把东西抵押掉、拿到钱呢?”我问。
幸而我的母亲认识“大型动产”公司的一位经理,她答应立即去找他,请他明天派估价员来。我们的住房的租期到5月1日为止,家具可以在复活节以后运到仓库里。妈妈负责把押款按照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指定的数目分送给他的亲属。至于金银器物、彩票和毛皮大衣等,则在我们离开以前还来得及押出。
我高高兴兴地回家,终于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起身以前赶到。帕维尔·阿列克桑德罗维奇很想知道我整个早晨的去向,于是就立刻走到我在那儿为丈夫准备咖啡的饭厅里来,照例开始挖苦我。
“我很乐于证实,您是那么虔诚,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他开口说,“不但做完晨祷,还做了日祷,就像费多西娅告诉我的那样。”
“是的,我刚才在教堂里,”我回答。
“但您今天为什么这样闷闷不乐?请允许我打听一下,您那热烈的想象力究竟在哪些外国疗养地驰骋?”
“您不是知道,我们不去国外了?”
“我不是对您说过了吗?现在您根据经验已经相信,我会坚持自己的主张,不会放您出国旅行的!”
“是啊,我知道,知道!这还有什么可说的?”我回答,虽然心中对他的这些放肆无礼的话气愤已极,但我不想跟他争吵。
我面临着一项重大的任务——说服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同意我所设想的计划。在家跟他谈这件事不行:随时会有人来打扰我们,何况帕维尔·阿列克桑德罗维奇死守在家里,等候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家的年轻人,那些早晨来的常客。幸亏我丈夫必须出去办点事,我提出要陪他到附近的药房。走出家门,我要求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到升天教堂里的小教堂去一下。我们一起在圣母像前作了祷告,然后顺着沃兹涅先斯克大街和莫伊卡河的河岸走去。我十分激动,不知从哪儿说起。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帮了我的忙。他看到我精神愉快,便说:“安尼娅,你同意取消我们俩那么想望的出国之行,我是多么高兴!”
“不过,要是你同意我向你提出的计划,那么,我们还是走得成的,”我回答,马上开始叙述自己的计划。正如我预料的那样,我的丈夫立即否定了我的计划,他不愿意我放弃自己的嫁妆。我们开始争论起来,没有注意脚下的道路,一直顺着莫伊卡河的河岸往前走,最后到了城市中一个无人居住、我从未到过的地区。在我们的婚后生活中,我第二次坦白地告诉丈夫,我的日子不好过,央求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哪怕让我过上两三个月安静和幸福的生活也好。我断言,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不仅不能像我们过去想望的那样,成为知心的朋友,而且可能就此分手,无可挽回。我央求丈夫挽救我们的爱情、我们的幸福,临了,我放声大哭,哭得那么伤心,以致可怜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张皇失措,不知对我怎么办才好。他急忙表示完全同意我的打算。我欢欣万分,竟然不顾行人(在那个地区为数不多),热烈地吻了丈夫几下。就在这当儿,我抓紧时间,要求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到总督办公室去打听一下,什么时候可以拿到出国护照。办理护照总是给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带来麻烦。作为过去的政治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处在警察局的监视之下[7],除了办理通常的手续外,他还必须事先获得军事总督的许可。在总督办公室有一个我丈夫认识的官员——我丈夫的天才的热烈崇拜者,他希望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立即写一份申请书,并且答应明天就将此事向上级呈报。至于护照,他答应在星期五以前办好。
我记得,那一天我感到无上的幸福!甚至帕维尔·阿列克桑德罗维奇的纠缠也没有使我生气,因为我知道,这种情况马上就会结束。这一天我们对谁也没有谈起即将出国的事,除了母亲,她晚上来到我这里,把金器、银器和彩票带走,以便第二天把它们典押。
次日,星期三,公司的估价员到我们家来,对我们的家具作了估价,确定我们应得的款额。就在这一天晚上,当几乎所有的亲戚都集中在我们家吃饭的时候,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宣布我们即将在后天出国。
“请允许我提醒您一下,爸爸,”帕维尔·阿列克桑德罗维奇立即说,他听到这一消息慌了神。
“什么也不用提醒!”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突然冒起火来,“指定给多少,就拿多少,大家都别想多拿一个戈比。”
“但是这不可能!我忘记告诉您,我的夏季大衣式样太旧,我需要做一件新的,还有另外的费用……”帕维尔·阿列克桑德罗维奇开口说。
“除了指定给你的数目,你什么也别想了。我们出国花的是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的钱,我无权支配这些钱。”
帕维尔·阿列克桑德罗维奇两三次试图提出某些要求,但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连听也不听。
吃过饭以后,亲戚们鱼贯进入我丈夫的书房。在那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给每个人一部分钱,而另一部分则出字条于5月1日支付,届时,我母亲将负责从我们所得的押款中付给他们。
我说服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给帕维尔·阿列克桑德罗维奇做夏季大衣的钱,好让他不阻难我们。但是他并不见情,在告别的时候,还对我说,我采取这么诡谲的行动(出国旅行),他饶不了我,到秋天他要“跟我较量,还不知道胜利属于哪一方呢”。
我感到那么幸福,以致没有去理会从各方面纷纷向我袭来的挖苦话。
我们很快把行李收拾停当,想到我们此去时间不会很长,就只随身带一些必要的东西,把抵押家具和保存余下的生活用品委托我母亲办理。帕维尔·阿列克桑德罗维奇硬要帮她的忙,但是他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把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书房里的一部分家具和书籍搬到自己那儿,说他想读点书以补教育之不足。
我们准备出国三个月,然而过了四年多才回到俄国。在这段时间里,在我们的生活中发生了许多可喜的事件,我要永远感谢上帝,是主使我出国的决心更加坚定。在国外,我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新的幸福生活开始,我们之间的友谊和爱情得到了巩固,直到我丈夫去世,这种感情始终不渝。
注释:
[1]早在四十年代,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教师和作家亚·彼·米柳科夫就建立了友谊;即使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流放回来以后,他们之间的友谊也没有中断。(参阅陀思妥耶夫斯基1860年11月10日、1866年7月以及1867年2月13日给米柳科夫的信——《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第1卷,页299、443、456)但是,他们在精神上并不接近。不仅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引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句话(“根据叙述的那种庸俗的口气来看,干这件事少不了亚·彼·米柳科夫”)可以证明这一点;而且,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国外时期(1867—1871)给埃·费·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尼·尼·斯特拉霍夫、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的信中对亚·彼·米柳科夫的否定性意见也同样可以证明。然而,没有确切的资料足以证实,载于《祖国之子报》上的那篇文章正是米柳科夫写的。1890年,亚·彼·米柳科夫的著作《与作家们的会见和交往》一书问世,其中有整整一章写他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交往和友谊。
[2]不确。后来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本人也说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继子帕·阿·伊萨耶夫只比她小几个月。
[3]翻译家和新闻工作者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陀尔戈莫斯季耶夫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杂志《当代》和《时代》的固定撰稿人,是“根基派”最激烈、最狂热的拥护者。根据斯特拉霍夫的回忆,陀尔戈莫斯季耶夫之所以害固定观念病,部分地是由于他长期地、无休止地进行关于“根基论”的争论和思索。(参阅《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1卷——《传记、书信和札记》,页205—206)
[4]帕维尔·阿列克桑德罗维奇·伊萨耶夫生于1846年。
[5]1842年7月和1846年夏季,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往雷瓦尔(即塔林)看望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6]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66年在柳布林伊万诺夫家的别墅度夏一事请参阅Н。Н。冯福赫特的回忆录《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历史导报》,1901年,第12期,页1023—1033。Н。Н。冯福赫特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柳布林的逗留称为作家生活中幸福的时光,当时,他摆脱了写《罪与罚》的紧张工作,在游戏和娱乐中获得休息。
[7]关于警察局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监视请参阅Ю。Γ。奥克斯曼的《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秘密指令》,收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一书,敖德萨,1921年,页36—38,以及本书第七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