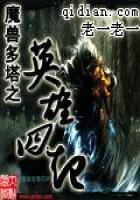“如果别人介绍一个人和你认识,你跟他讲了几句平平常常的话,难道你会记得他的脸?不记得,是吗?至少我是经常忘记的。这次也一样:我跟你谈话,看到你的脸,可是你一走,我马上就把它忘掉啦,要是有人问我你是金发姑娘还是黑发姑娘,我就答不上来。直到10月底,我才注意到你那双美丽的灰眼睛和善良、开朗的笑容。而且你整个面貌我都喜爱,越来越喜爱。现在对我来说,世界上最可爱的就是你的脸蛋!在我看来,你是个美人儿!不仅如此,在大家看来,你也是美人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天真地添上一句。
“你初次来访,”他继续回忆道,“举止得体,态度认真,几乎有些严厉,令我赞叹。我思忖:好一个严肃认真、精明强干的姑娘的典型!我为我们社会里出现这种典型而高兴。有一次,我无意中说了一个不恰当的词儿,你带着那样的神情望着我,使我开始斟酌自己的用语,生怕一不小心,就会伤害你。后来,你对我真诚的关切,得知我面临灾难而表现的同情,令我诧异,叫我动心。我想,我的亲友们好像也爱我。他们为我有可能丧失自己在文学方面的权利而惋惜,他们对斯捷洛夫斯基满怀愤懑,责备我跟他签订了那样的合同(仿佛我有办法不签订似的),他们给我忠告,安慰我,可我觉得这一切全是‘空话,空话,空话’。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关心这一点:我会由于丧失权利而被剥夺得精光,分文不名……而你这个陌生的、我刚刚认识的姑娘却一下子就同情我的处境,没有感叹,没有惊叫,也没有表示愤愤不平,而着手帮助我,不是用言语,而是用行动。几天以后,我们的工作上了轨道,我本来已经完全绝望,现在点燃了希望之火:‘要是以后一直这样工作,说不定我能按时完成呢!’我想。你保证我们一定能够完成(你可记得,我们一起计算你抄写的页数),这个保证增强我的希望,赋予我继续工作的力量。我常常暗自思忖:‘这个姑娘有一颗多么善良的心啊!她怜惜我,不是在口头上,而是表现在行动中,想使我从灾难中解脱出来。’我在精神上是那么孤独,能够找到一个同情我的人真是极大的幸事。”
“从这以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接着说,“我认为,我开始爱上了你,同时也欢喜你那亲切可爱的脸蛋。我常常发觉自己在想你;但是直到我们完成了《赌徒》,我明白此后我们不能再每天见面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没有你,我就不能生活。在那个时候,我就决定向你求婚。”
“但是你为什么不像别人那样直截了当地向我求婚,而要想出那么一个有趣的故事?”我好奇地问。
“你要知道,我亲爱的安尼娅,”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用十分激动的声调说,“当我意识到你对我来说是多么重要时,我陷于绝望,感到我想娶你的意图纯粹是妄想!只要思考一下,我跟你是多么不同的两个人!单是年龄的悬殊就非同小可!我差不多是个老头儿啦,而你呢,几乎还是个孩子。我又害上了不治之症,性情忧郁,容易激动;而你身体健康,精力充沛,愉快活泼。我几乎已到暮年,一生中经受了许多苦难,而你却一直过得很幸福,还刚刚开始生活。此外,我贫穷,负债累累。在各方面的条件如此悬殊的情况下,有什么可以指望的呢?要么我们的未来十分黯淡,两个人受了几年折磨之后终于分手;要么我们在有生之年一直情投意合,十分幸福。”
听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如此贬低自己的话,我感到很难受,就热烈地反驳说:“我亲爱的,你太夸张了!你所想象的我们之间那种条件悬殊的情况并不存在。如果我们彼此爱得很深,我们就会成为朋友,就会无限幸福。我倒是担心另一种情况:像你这样有才能,这样聪明、有教养的人却娶了个比你教养差得多的傻姑娘;她虽然在中学里得过一枚银质大奖章(我当时还十分自豪呢),但是各方面的水平都不能和你相比。我怕你很快就会把我看透,开始怨恨我,为了我不能理解你的思想而伤心。这方面条件的悬殊比任何不幸更糟糕!”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急忙安慰我,讲了许多赞美我的话,我们又回到我所感兴趣的、有关求婚的话题上来。
“我犹豫很久,不知怎么提出来才好,”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说,“一个上了年纪、长相难看的男子向一个年轻姑娘求婚而遭到拒绝,就会让人发笑,可我不愿意自己在你的眼里显得可笑。要是我向你求婚,而你却答复我说,你另有所爱呢?你的拒绝会使我们的关系趋于冷淡,这样,我们过去的友谊就会变得难以想象。我将失去你这个朋友,失去最近两年来唯一热诚待我的人。我再说一遍,我在精神上是那么孤独,如果失去你的友谊和帮助,我会感到十分痛苦。因而我就对你讲述新小说的提要,想借此了解一下你的感情。这样,如果遭到你拒绝的话,我会好受一些,因为我所谈的是小说中的主人公,而不是我自己。”
我也讲述了他通过文学作品向我求婚时我的感受:我对安娜·瓦西利耶芙娜的不理解、嫉妒和羡慕等等。
“这样看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十分惊奇地说,“我出其不意地向你袭击,使你措手不及,迫使你同意!可是,我明白,当时我所讲述的这篇小说是我过去所写的全部小说中最好的一篇:它立即获得了成功,产生了所期望的效果!”
十五
我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沉浸在新的欢乐中,不知怎的忘记了《罪与罚》的结尾工作,那时候,小说的整个第三部尚待写作。11月底,《俄国导报》需要小说的续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就想起了这件事。幸而在那几年,各种杂志很少按时出版,而《俄国导报》甚至误期出了名:11月号在12月底才出版,12月号则在2月初出版,等等;因此,我们的时间相当充裕。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把编辑部的来信带给我看,征求我的意见。我建议他闭门谢客,从下午两点写到五点,然后晚上来到我家,把原稿读给我听,让我速记、整理。
我们作了这样的安排:闲聊片刻,我就在写字桌边坐下,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则坐在我旁边,开始口授,在此过程中,口授间或被谈话、戏言和嬉笑所打断。工作进行得挺顺利,篇幅近七印张的《罪与罚》的末一章在四个星期里完成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向我肯定地说,他从未工作得这样得心应手过,而这次的成绩应归功于我的合作。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那饱满的、愉快的情绪对他的健康也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在我们结婚以前的整整三个月里,他的癫痫病不过发了三四次。这使我非常高兴,希望他在更安静、更幸福的生活条件下病情能够减轻。后来的情况果然如此:以前他几乎每星期都要发病,后来病情一年比一年减轻,发病次数也越来越少。要把癫痫病完全治愈是不可能的,何况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从来也不就医,认为他的病是不治之症。但是不论病情减轻或发病的次数减少对我们来说都是上帝的无上恩惠。它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摆脱了有时持续整整一星期之久的那种真正可怕的、忧郁的情绪,这是每次发病的后果;也使我得以免除在我眼见这种可怕的病发作时心惊胆战、直淌眼泪的痛苦。
每天晚上我们总是过得安静而愉快,但是有一次却出现了风暴。
事情发生在11月底。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照例在七点钟来到,这一次,他冻坏了。他喝了一杯热茶,问我这儿有没有白兰地。我回答,白兰地没有,但有上好的核列斯酒一种浓葡萄酒。——译者注,于是我就立即把它拿了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把酒倒在大的高脚玻璃杯里,一口气喝了三四杯,随后又喝了茶,到那时候才暖和过来。我感到纳闷,他怎么会冻得这么厉害,不知道这是什么缘故。谜底很快解开了:我到前室去取东西的时候,发现挂在衣架上的不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经常穿的那件皮大衣,而是一件秋季穿的棉大衣。我马上回到客厅里,问道:“莫非你今天没穿皮大衣来?”
“没——没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结结巴巴地说,“穿的是秋季大衣。”
“多么不谨慎!那么,你为什么不穿皮大衣呢?”
“我听说今天是解冻的天气。”
“我现在明白了,你怎么会冻得这么厉害。我马上打发谢苗把棉大衣送回去,拿皮大衣来。”
“不需要!真的不需要!”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急忙说。
“怎么不需要呢,我亲爱的?你回去的时候要着凉的:夜里更冷了。”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沉默不语。我还是坚持要这样做,最后,他终于说出了原委:“我没有皮大衣了……”
“怎么会没有的?莫非让人偷掉了?”
“不,没有给偷掉,而是给抵押掉了。”
我吃了一惊。在我的追问下,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显然不大乐意地告诉我:今天早晨,埃米莉娅·费奥多罗芙娜跑到他那儿,请求他解决燃眉之急:替她付掉一笔五十卢布的借款。他的继子向他要钱;还有他的弟弟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1831—1883),工程师和建筑师。特意写信来,说是缺钱花。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没有钱,他们就决定把他的皮大衣押给附近的债主,而且还竭力向他保证,今后将是持续的解冻天,气候暖和,在收到《俄国导报》的稿费以前,他可以穿秋大衣对付几天。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亲戚们这种冷酷无情的行为使我非常气愤。我告诉他,我理解他帮助亲戚们的心意,但是我觉得,他不能因此而牺牲自己的健康,甚至可能牺牲生命。
我起初比较平静,但是越说越气愤、越伤心;我完全失去自制力,像发了疯似的,讲话不择言词,一再说明他对我,他的未婚妻,负有责任,而且断言,如果他死了,我会经受不住。我呜咽,叫喊,号啕大哭,仿佛歇斯底里大发作。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非常难受,他搂住我,吻我的手,请求我安静下来。我的母亲听到我号啕大哭,就赶紧给我拿来一杯糖水。这使我冷静了一些。我开始感到羞愧,请求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原谅。他向我解释,去年冬天,他有五六次被迫把皮大衣押给别人,外出时只能穿秋大衣。
“没关系,这种典押的事情在我已经习以为常,这一次,我也毫不在意。要是我知道你把这事看得那么可怕,那我怎么也不会让帕沙去把皮大衣押给别人,”窘迫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我坚决地说。
我趁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后悔之际,要他答应我,以后不再发生这样的事。接着,我表示愿意支援他八十卢布,以便把那件皮大衣赎回来,可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断然拒绝。于是我便恳求他,在莫斯科没有寄钱来以前,要他待在家里。我答应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每天下午一点到他那里,待到快吃晚饭的时候,这样,他就同意“软禁在家”。
在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告别的当儿,我再次请求他原谅我刚才对他“使性子”。
“有祸必有福!”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回答说,“现在我深深地相信,你是多么热烈地爱我:要是你不爱我,你就不可能哭得那么伤心!”
我用自己白色的毛线围巾裹住他的脖子,强迫他把我们的毯子披在肩上。晚上整个余下的时间里,我一会儿痛苦地想着,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知道我会这样“使性子”,是否可能不再爱我;一会儿又担心他路上会着凉,病倒。我几乎彻夜未眠,清早起身,到十点钟就已经打响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家的门铃了。女仆的话使我定了心,她说,老爷已经起身,夜里一点也没有感到不舒服。
可以说,这是我们结婚前三个月中仅有的一个“不平静”的晚上。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软禁在家”持续了约莫一个星期,在此期间,我每天都到他那儿去,把《罪与罚》速记下来。有一次我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家的时候,他有个情况使我十分惊讶:在我们工作正紧张的当儿,响起了手摇风琴的乐声,演奏的是《弄臣》《弄臣》是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1813—1910)所作的歌剧。——译者注中有名的咏叹调《La donna est mobile》《女人的心是易变的》。——译者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停止念稿,留心倾听,突然唱起这支咏叹调来,把意大利词换成我的名字和父名:“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他用悦耳的、虽然有些压抑的男高音唱着。咏叹调奏完以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走到气窗跟前,投下一枚硬币,手摇风琴师就立即走了。我问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这是怎么回事;他告诉我,手摇风琴师显然发觉,他演奏了什么曲子以后,屋子里的人就会扔下钱来,于是他便每天走到窗下,只演奏《弄臣》中的这支咏叹调。
“而我呢,就总是合着这个曲调,吟唱着你可爱的名字!”他说。
我笑着,假装由于他把如此轻佻的词儿应用到我的名字上而生气;我断然说,我不是那种反复无常的女人,一旦我爱上了他,那就永不变心。
“咱们等着瞧,等着瞧吧!”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笑着说。
在随后的两天里,我又听到手摇风琴师演奏这支咏叹调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歌声,他的歌声与乐声是如此合拍,使我感到惊奇。显然,他的音乐听觉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