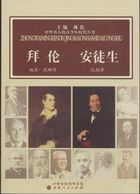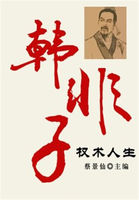殷海光对于20世纪60年代台湾社会的“自由”状况有过很痛切的揭露:“今日的台湾,在实际上早已成为一人一家一党的殖民地。这一个殖民地在骨子里完全被置于效忠私人的秘密力量严格控制之下。人民有吃、喝、玩、乐之‘自由’,更有腐化堕落之‘自由’。只要做得不破面,官吏大有贪污之“自由”。这些,都是网开一面的。然而,人民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自由,没有言论自由,更没有政治自由。”斯言至矣!
1966年,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五四以来的自由知识分子,自胡适以降,像风卷残云似的,消失在天边。我从来没有看见中国的知识分子像这样苍白失血,目无神光。他们的亡失,他们的衰颓,和当年比较起来,前后判若两种人。”痛哉斯言!
虽然屡次掉入政治漩涡,但殷海光却比学院里的教授培养了更多的人才。他有自知之明:他自己由于成长过程中颠沛流离,以及后来在报纸杂志上秉笔报国,花去许多时间与精力,所以尚未积累足够的资源做最根本、最艰深的研究。但他的独立人格、思想激情感染了几乎一代有青春理想的年轻人,如林毓生、李敖等。
1966年12月,殷海光在给林毓生夫妇的信中说:“你知道我在这个岛上是岛中之岛。在这样的氛围里,怀抱自己的想法的人之陷于孤独,毋宁是时代的写照。生存在这样的社群里,如果一个人尚有大脑,便是他不幸之源啊!”
这个犬儒时代的思想者因此在历史的纵深里成全了他作为一个启蒙者、思想大师的地位。
殷海光在台北市温州街18巷16弄1之1号的家位于小巷的尽头,是一座带花园的独立平房,如今已是一个被追思的景点。这个地址以及眼前的这片小巷景象,曾经在台湾现代政治与思想史上留下了一抹绚丽的色彩。
当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首先会想到的是无数个风雨之夜,在这个矮小、简朴的门口出出进进的呼吁自由的人,还有那些昼夜蛰伏着的监视者。“巷子的尽头是殷师的家。外面是一堵高墙,这便是被其他教授戏呼的有名的‘柏林围墙’。1966年开始在这围墙的附近,有监视的便衣出没。”殷海光的学生郭松棻在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
面对着这扇矮小、简朴、浅绿色的木门,水泥批荡的门柱上挂着一块长形木牌,上书“殷海光故居”。旁边爬满绿色植物的围墙上钉着一块刻着“市定古迹”字样的铝制铭牌,铭文中有曰:“先生任教于台大哲学系,毕生提倡自由主义,秉持‘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精神,勇于对抗威权、批评时政,启迪学术与社会良知,对推动台湾民主运动具有贡献。”这段话可以看作是对殷海光最浓缩的介绍和评价。在台北南港墓园,殷海光的墓碑上刻的是“自由思想者殷海光先生之墓”,这是依据他的遗嘱而立。
在殷海光,“自由思想者”是他对自己的盖棺论定;而对于所有思想者而言,难道还有比“自由”更重要、更高贵的头衔吗?
殷海光的确是毕生研究和提倡自由主义,至死方休。20世纪40年代后期,他以敏锐和深刻的洞见以及决绝的勇气,就自由与专制的问题撰文警醒国人,几乎是以天生的直觉老早就把一些最基本的问题都看清楚、讲清楚了,今天读来真令人有夫复何言之感。
毕生热心于现代逻辑的研究、教学和宣传,其原因在于他认为中国文化中认知因素极为缺乏,而这必须依靠西方实证论哲学的输入来补救。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认知因素不发达,从根本上说,归因于儒家文化的泛道德主义倾向和中国文化采取的“崇古”价值取向。于是,殷海光大力提倡“认知的独立”,强调“独立思想”。殷海光终生秉持科学民主自由的精神,是一位富有批判精神的自由主义者。
殷海光看到岛内知识分子大多处于麻木的“冬眠”状态,便利用开座谈会、写文章、出书等形式,积极引介哈耶克、卡尔·波普尔等人的哲学新思潮,大力宣传罗素哲学和五四精神,对广大知识青年及人民大众进行思想启蒙,鼓动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勇敢地起来与专制、独裁的统治作斗争。因而,他成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人民,特别是青年们最崇拜的精神领袖、抗暴旗手、民主斗士、启蒙大师。
殷海光的学生赵天仪说最喜欢找老师聊天,因为殷海光老师讲课,主要的是知识的介绍;他的演讲,比较会提出他对时事的感受与粗浅的看法;他的聊天,则比较会说出他深藏在心里的话。
殷老师下课的时候,有些同学会找他聊天,有的坐在高丽草坪上跟他说话,有的在椰树边一起走一边跟他谈话。最令人难忘的是,一位历史系的学生马大勇,他抬头挺胸;另一位是哲学系的学生汪竞雄,他低头沉思。他们两位陪殷海光散步,是台大当年一个令人回味的风景。
但是受到殷海光的熏陶,同学们也变得“反动”了。同学汪竞雄以“历史漩涡论”的论文,获得台大哲学研究所的硕士学位。不幸的是,在他毕业不久,就因所谓的“思想问题”被关到牢狱,因他不承认自己思想有问题,也被关到绿岛的监狱。出狱后不久,他已丧失了认识别人的能力,连他的好友马大勇都不认识了,不久就病逝了。这是当年国民党制造白色恐怖的又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殷海光这个人的悲愤心情跃然纸上:“现在,我可以说,任何书房外的热闹不能动摇我;任何无端的侮辱不能刺激我;任何现实的利益不能把我从追求真理的路上引向别处。”因此他会在信里对朋友和学生说:“愿我们终有一天在一起煮茗,论学,抱小孩。”
南宋杨万里那首有名的绝句:“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真可看作是对殷海光出师未捷的最恰当的注脚。
殷海光不仅是一位傲骨嶙峋的批评家,而且是一位思想敏锐的学问家。他的批评以他的学问作基础,所关注的是自由、民主、科学与社会正义,所钻研的是分析哲学与文化问题。他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他将自己的学问活用于批评工作。他的文章尖锐深刻,语言流畅简练,逻辑性强,论据有力。李敖夸说:除了思想指向以外,殷海光的政论文章光芒万丈,出色得使敌人和朋友都为之失色,而且至今无人超越。
殷海光以台大学术殿堂为传道之所,在教育上以自身的学养为日后台湾培养了一批笃信自由主义思想的生力军。在言论宣传上,以《自由中国》为传媒,向广大的台湾知识青年介绍自由主义思潮,即便在国民党铺天盖地的迫害压力下,亦不改初衷,永不放弃自己坚信不疑的自由主义信仰。
他去世后,他培养的弟子有的成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台湾反抗国民党暴政的风云人物,有的成为著名学者、作家、名记,如林毓生、颜元叔、陈鼓应、柏杨、李敖、龙应台、司马文武等。
“中研院”胡适纪念馆馆长潘光哲说,殷海光是反映台湾政治社会变迁的一面镜子,期待台大出版的《殷海光全集》能为理解殷海光斯人斯行提供比较完美的史料基础,殷海光的精神遗产可以成为台湾走向更自由、民主社会的道路上生生不息的思想资源。
台湾中正大学哲学系教授陈瑞麟表示,重新评价殷海光的思想成就,并不打算把殷海光抬举成完美或无可挑剔的思想家,殷海光没有为学术而学术、为思想而思想,他是为了解决所面对的时代问题而独立运思,他并不知道自己的思考所得预示了后来许多新发展。
李敖说,有人攻击说:“殷海光是“文星集团”的大法师。在这位“法师”面前,排列着5个咬牙切齿的金刚:绰号“人权牧师”的李声庭、绰号“恶法克星”的陆啸钊、绰号“西化大少”的居浩然、绰号“西化义士”的韦政通、绰号“小疯狗”的李敖。”殷海光作为台湾自由主义的精神领袖,在台湾撒下了自由主义的火种,终于酿成了燎原之势。
桀骜不逊的李敖生平没有佩服过谁,但是他认为“殷海光的骨气胜于学问”。
李敖唯一批评恩师的是,殷海光一辈子标榜自由思想、自由主义,到了晚年,他受捧之余,不免自负是大师,这是与自由主义矛盾的。他相信一个学说,就相信到崇拜的地步,这也不是学术应该有的态度。可是他与专政作抗争,这是李敖佩服他的地方。
同时,李敖认为殷海光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也有不足之处。他对中国文化的批判,有些东西是相当有问题的。他对史料不熟,对发展过程也不清楚。他以为搞数理逻辑的王浩是世界上重要的数学家,佩服得五体投地。殷海光自己教逻辑学,以为数理逻辑是逻辑学的登峰造极,可是他的数学造诣并不够用,这就是他的盲点。但是李敖说:“我们不能去责备他,他有他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