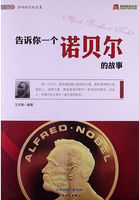殷海光教授是台湾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期间非常著名的自由主义学者,却因不能见容于国民党蒋介石政权,而被以极为卑劣的手段围剿,最后他被迫离开已任教十余年的台湾大学,成为当年最轰动、最受海内外瞩目的学术迫害事件。
1殷海光其人
殷海光(1919—1969),原名殷福生,海光是其在抗战结束后踏入出版界时使用的笔名。五四运动爆发时,他还在他妈妈的肚子里。1919年12月5日,他降生在湖北省黄冈县(今黄冈市)回龙山镇殷家楼村的一个传教士家庭。
十三岁那年,他由其伯父、辛亥革命志士殷子衡带到武昌,进入武昌中学念书。初中时代,殷海光不是一位独占鳌头的好学生,而是一位桀骜不驯的“坏学生”,读书非常任性,有几科功课不及格。他自幼年起,就是一位非常喜爱自由且任性发展的人。在武昌的中学念书时,他往往对喜欢的功课孜孜不倦,因此成绩特别好,反之则常不及格。为了这件事,他的父亲曾经一度认为他“不堪造就”,决定把他送到外面当学徒。就这样,殷海光被带到汉口去,在一间食品店开始学徒生涯。
起初,他以学徒的工作甚感羞愧,深怕旧日的同学看见;没想到,某一天他旧时的同学们恰巧结伴光顾了这家食品店,顿时使他无地自容。
历经八个月之久,殷深知“自己不是走这一条路子的人”,于是决心离开。终于,他努力打工存够旅费后,不辞而别地离开汉口,回到老家黄冈。
由于受张申府主编的《世界思潮》的影响,殷海光醉心于西方学者的思想,也爱屋及乌地惊羡于逻辑的力量。当时,一位在清华大学念书的同乡从北平带给他一本厚厚的逻辑书,书中弯弯曲曲的符号让这位少年着了迷。这就是由金岳霖为清华大学哲学系学生编写的讲义《逻辑》。因此,可以说殷海光的学术生涯开始得很早。殷海光从小喜欢思考与写作,十六岁那年,他曾在名气甚大的《东方》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这是受到当时的哲学大师金岳霖的影响。
仔细分析他对哲学的探索,也算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吧。当时“受一股求知热望的驱使,受一种对金先生景仰之情的驱策”,他直接致信金岳霖,希望有更多收获。结果远远超出他的期待,大教授不仅回信答复了他的问题,还表示欣赏其见解,同时告诉他有哪些书可以寄来供他阅读。这段学术史上的佳话开启了金、殷二人以后长期的师生之谊的大门。
金的长者风范极大地鼓励了渴望求知的殷海光,他更加着迷于介绍逻辑和哲学的书籍。1935年,十六岁的殷海光订购到查普曼和罕勒合著的《逻辑基本》,如获至宝,仔细读完这本书后,他决心把它翻译成中文。一个中学生,在几门功课不及格的情形下,居然要翻译一本与高中功课毫无关系的大学用书,这种举动自然遭到家人的一致反对。还好,他中学的老师很支持他。于是,在漫天飘雪的日子里,他开始了平生第一次学术上的尝试。经过历时半年的努力,他将这本厚达417页、总共约40万字的书译成中文,并写出了15000字的“译者引语”,于1937年由正中书局出版。
1936年高中毕业,殷海光便到北平,亲自向金岳霖、熊十力等人问学。不过,直到1938年考入西南联大,他才正式师从金岳霖。
殷海光师从金岳霖的故事非常曲折离奇。第一次到北平金岳霖的书房时,殷海光相当诧异:金的书架上歪歪斜斜地放着二三十本书,心想为何如此而已?这和他所想象的学者藏书应该是堆积如山的情形大不相同。等到两人日渐熟稔后,殷海光鼓起勇气谈起此事,金岳霖才向他说:“时下流行的书,多是宣传,我是不会去看的。”
我们一提到殷海光,首先想到的是自由主义。确实,殷海光已经成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一个象征。这当然没错,但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殷海光转向自由主义是很晚的事情。此前,他的学术兴趣完全在逻辑学上,尽管他在逻辑学研究上并没有作出像他的老师金岳霖那样惊人的成绩。
在此之前,他还将“译者引语”的主要内容改写成《逻辑和逻辑学究竟是什么》,由金岳霖推荐发表于张东荪主编的《文哲月刊》。难能可贵的是,面对各位前辈,十七岁的殷海光毫无惧色,对大学者金岳霖、吴士栋、沈有鼎、张东荪等人的著述逐一进行了点评。
1936年秋,高中毕业的殷海光在金岳霖的鼓励下北上求学。由于没能赶上当年的入学考试,他只能住下来等来年再考。他所带的旅资极为有限,在北平的生活差不多全靠金岳霖维持。但他在北平这一年的经历对他人格的塑造有着重要意义。他每周和金岳霖见面一次,一起吃饭,谈学问。不知不觉中,大师的风范已经深深地感染了这位刚从小县城走出来的少年。
与金岳霖相知甚深的冯友兰曾这样评价金岳霖:“金先生的风度很像魏晋大玄学家嵇康。嵇康的特点是‘越名教而任自然’,天真烂漫,率性而行;思想清楚,逻辑性强;欣赏艺术,审美感高。我认为,这几句话可以概括嵇康的风度。这几句话对于金先生的风度也完全可以适用。我想象中的嵇康,和我记忆中的金先生,相互辉映。”
殷海光一生都记得他第一次和金岳霖见面时的情景。但是,他以年少者的轻狂,谈起话来满口都是“我认为一定怎样……”、“我敢说如何……”,但金岳霖在陈述自己的看法时总是说“如果怎样,那么怎样”,“或者……”,“可能……”。大学者的谦逊令年少的殷海光大为感动。在一次聚会时,有人提起始享大名的哥德尔,金岳霖说要买他一本书看看,他的学生沈有鼎对金先生说:“老实说,你看不懂的。”金先生闻言,先是“哦哦!”了两声,然后说:“那就算了。”殷海光在一边听到他们师生两人的对话,大为吃惊,师生之间竟可以这样相处!今天,当我们展读殷海光和他的学生林毓生的书信集时,我们常常会感叹他们师生之间率真的情感流露和亦师亦友的平等关系。殊不知,这种融洽、真挚的种子早在殷海光还是一个少年时即已种下。
就在1937年夏天殷海光准备报考清华哲学系的时候,抗日战争爆发了。在隆隆的炮声中,他的大学梦化为了泡影。金岳霖给了他50元钱,作为返乡的路费。就这样,在北平住了差不多一年后,殷海光回到了故乡。次年春天,当获悉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南迁昆明,合组西南联大时,殷海光又决定前往昆明求学,继续追随金先生。
1938年,殷海光入读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之后他在西南联大度过了七年漫长的岁月。这期间,他接触最多的人当然还是金岳霖。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此后的岁月,殷海光提及金岳霖时更多的是老师对自己人格的塑造,而不是学业上的帮助。其实,这中间包含着他说不出的无奈。
殷海光终生引以为憾的,是在这段宝贵的青年时代,他没有能静下心来苦做学问,守护学术理想,相反,却因为政治上的浮动,卷入校园内的种种政治活动。他曾经感慨道:“当时在昆明西南联大校园内,真是‘各党各派’‘异说争鸣’。我当时几乎事事反应,简直静不下心来苦攻学问。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是一个浮动分子。”
2从讴歌者到诤友
殷海光大学毕业后,曾于1942年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研究所专攻西方哲学。1944年底,蒋介石发表《告知识青年从军书》,1945年当时已是研究生的殷海光却投笔从戎,加入青年军,成为一个热血青年投身抗战,远赴印度学习军用汽车驾驶技术。但在八个月后因为不适应军队生活回到了重庆,转业到重庆独立出版社任编辑。1946年秋,他被同乡陶希圣拉入国民党阵营,先后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中央”日报》任职。抗战结束初期,殷海光由于以言词激烈的“反共”著作,深获国民党内高层注意,经徐复观的引荐,他曾一度蒙蒋介石召见。
殷海光不是当兵的料,他的士兵生涯很快就结束了。抗战胜利后,他没有回到校园,而是来到了当时中国的政治中心重庆。1946年,都城回迁南京后,他又来到了南京。很明显,这段时间殷海光的政治热情压倒了他对学术的兴趣。
前面说过,因为同乡陶希圣的关系,殷海光被延揽进《“中央”日报》,不久任主笔。《“中央”日报》是国民党中央的机关报,殷海光能进入国民党中央的喉舌,并担任极重要的主笔一职,这显然与他当时极端的政治立场有关。
但是,他在《“中央”日报》的工作经历,却让他逐渐由国民党的赤诚讴歌者转变为国民党的诤友。据殷海光自己的回忆,1948年底徐蚌会战时,他以《“中央”日报》主笔的身份亲临前线。由灯红酒绿、六朝金粉的都市走向战场,面对的是“赤野千里,庐舍为墟”,心动神伤之余,他开始“体认到中国的问题满不是派系口号所喊得那么简单”,并且“开始了解党派偏见如何有害于中国问题之适切的解决”。这时的他“对国事的态度,大为改变”。他的同学的傅乐成回忆道:“他写的文章,对政府时作尖锐的批评,甚至对他从前所最崇敬的人,也有微辞。”
由于殷海光如此右倾,他年轻时为左翼青年所不齿。一般来说,人在年轻时,总会表现得激进一些。但在西南联大求学的时候,殷海光是一位较为保守的“右翼青年”,与“一二·九”运动中那些激进的“左翼青年”在政治上大相径庭,如台湾的徐高阮,如祖国大陆的李慎之。
左翼愤青李慎之晚年提到殷海光这个人,说那时他们这些“左派”自视甚高,“昆明西面联大有一个叫殷福生的人,年龄大概与我们差不多,专与学生运动作对。十来年后,他在海外华人中以殷海光的大名,被推为提倡民主的一代宗师。不过在那个时候,他是根本不入我们眼中的,因为无非是一个‘反动学生’而已”。
“反动学生”这顶帽子扣在殷海光头上似乎过重了点,其实严格说来,殷海光在祖国大陆时期纯粹是“书生论政”。1946年,国民党政府复迁南京,殷海光亦追随东下,进入《“中央”日报》。由于工作表现良好,经历过短暂的卖文生涯。同一年殷海光获聘为《“中央”日报》主笔,不久又兼任金陵大学讲师,讲授“哲学与逻辑”课程。
在从事新闻工作的过程中,殷海光接触到一般大众所不清楚的真相,渐渐对国民党统治产生的疑虑,成为日后他对其政权勇于批判的远因。然而,殷海光没有忘记自己的出身与血性。1948年11月4日,他在《“中央”日报》上发表《赶快收拾人心》的社论,猛烈抨击豪门贵族和国民党的内外政策,受到蒋介石的怒斥,并险些丢职。“反共”的立场虽并未改变,但国民党这尊政治偶像却已破灭。尤有甚者,殷海光对“第三条道路”也不看好。路在何方?殷海光在苦苦地思考。
殷海光怎敢在党报写如此“放肆”的社论?他不知道严重的后果吗?他当然知道,但是殷海光在良心与思想的煎熬中写下《赶快收拾人心》一文,作为社论刊登在《“中央”日报》。文章痛陈:国家的风雨飘摇和老百姓的痛苦万状,国民党特权阶级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呼吁“赶快收拾人心,只有这一个机会了!”据说,此文经《大公报》转载后,士林传诵一时。
其实,就殷海光自己而言,他是在借批判国民党来拷问自己以往的政治信仰。但他此时并没有完全抛弃对国民党的期望和支持,因为就在解放军渡江前,殷海光随着《“中央”日报》一起去了台湾。
但这个年轻的国家主义者并不是狂热的法西斯分子,而是有着坚定的个人主义为支撑的爱国者,因此,他在祖国大陆的时候,就已经跟国民党不太合拍了。
在到台湾之前,殷海光就明白“国民党政权是建立于党阀、军阀、财阀和政阀这四大阀之上的”。到了台湾之后,他更目睹“国民党是由一班职业党棍组成的”,“是无根的人,为了苟且偷生,他们只有依附权势”。
1949年3月,殷海光随《“中央”日报》到台湾,仍任该报主笔,并曾代总主笔,同时兼任《民族报》总主笔。他离开祖国大陆的原因,除了一贯的“反动”外,还有对国民党寄予了重生的希望。他和不少年轻人都天真地以为,国民党因全面败退而该痛定思痛了。因此,他自居改革派,对政治指指点点。5月12日,殷海光在《“中央”日报》上发表社论《设防的基础在人心》,说跟随蒋介石逃到台湾的军政人员为“政治垃圾”,再次触怒了蒋介石,受到国民党的围攻、批判,并被迫离开《“中央”日报》,去台湾大学哲学系任教。
1949年迁台后,他一方面开展了对自由主义的理论研究,选择性地吸收了边沁、罗素、哈耶克、伯林、弗罗姆、奥本海默、波普尔等人的思想,尤以研读和翻译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为核心工作;另一方面以创刊于1949年11月的《自由中国》杂志(半月刊)为阵地,与同仁一道抱着“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信念,以呼唤自由民主与台岛政治的专制极权对决,他也因此声名大震。殷海光在前往台大教书的同时就介入了《自由中国》的筹备工作,随着刊物的成立,他列为编辑部成员之一。尽管在加盟《自由中国》的初期,殷海光并未超越原有的党派偏见,仍将自己的命运和国民党联系在一起,所写文章的主题也未逸出“反共”的主轴,但这一时期他确实开始注意自由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