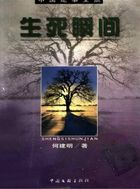不久前,我接到王璞同志的电话,问我身体好不好,问我有什么困难事需要帮助解决,还说他过些天要到学校来,到时会到一村来看望我。我真是非常高兴,也为自己好些年没主动去拜望他感到惭愧。
怎能料到,他竟在10月31日清晨突然逝世!
往事一件件浮现在心头……请允许我在这里叙述其中的一件:那是二十几年前,我去外校做一次报告,人家给了十元钱的报酬,寄到我校财务科,通知我去领取。但我去了财务科却领不到,说是要教研室主任签字,证明我不是私自外出去赚钱。我找到我们教研室的主任,一番问询之后,她签字,但仍是领不到,说是还要系主任签字。我便又去系里找到系主任徐中玉先生,他又签了字。但还是领不到,说是还必须有教务长的签字才行。这时我的确恼火了,就把那个叫我领钱的通知撕成碎片,装在信封里寄给学校党委,又写了一张纸条附上,大意是这样的官僚制度只能妨碍和压抑学术事业的发展,大概还说了什么“这钱我不要了,你们拿去吧,但这是我应得的正当的劳动报酬”等等并不恭敬的话。
我出过气就忘记这件事了。几天以后,一位年纪比我大的同志来敲我家的门,他手上拿着他的保暖杯,温和而含笑地问了我的名字,再问我能不能让他到家里坐坐。我问他有什么事,他从容地从衣袋中掏出那封我写给党委的信和那些撕碎的纸片,我才知道他是校党委的人。这时,我根据过去的经验,只觉得他定是来“兴师问罪”的,至少是要来对我批评教育一番,我有了一种抵触情绪,可能已经形之于色了。而他却并不在意我的态度,仍然微笑着,并自我介绍,说他就是党委书记王璞,来找我聊天的。
我于是不好意思了,请他坐下,给他的杯子里添了开水,心怀忐忑地等他说话,准备着挨几句批评。然而王璞同志开口说的话却是:“你的意见的对的。这种做法的确不好。我们立刻就改,以后不会再有这种事情了。不过这钱,你还是去领了吧,是你自己应得的正当的报酬嘛。”
这就让我更不好意思了,连忙承认了自己的脾气和态度不好。接着我们便亲切而随意地交谈起来。
自此,我们便成了朋友,我在他的鼓励和帮助下,更加努力地做好教学工作。一年后,我申请入党,并且得到批准,我们更成为进一步的同志。我们的交往和友谊,就像是一位县里或省里的领导和一个乡下种地的农民间的交往和友谊一样。我从他那里可以得到许多有益的启发和教导,而他通过我也可以及时了解到许多底层的意见和需要,知道许多与他在学校的领导工作有关的东西。
他退休以后,每次到学校来,往往会来我家坐坐。我也和我的老伴去泰兴路他家里探望,有时还跟中文系的老书记杨达平同志一同去。这样,我们间的友谊便日益发展,成为很要好的朋友。
我写过一部描写我国西北农村在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悲惨情况的长篇小说,他读后非常喜欢,要我给他两本,他把一本寄给了在中央工作的他的老战友,他说必须让上面的领导了解这些情况。他就是这样时时心怀着大局。后来,一家出版社要把我的小说翻译成英语出版,需要企业资助,他又积极地为这件事四处努力。他的热心让我和我的一些作家朋友们很是感动。
回忆我和王璞同志的相处,我深深感到,如果我们所有做领导工作的同志都能够诚恳、真实、平易、虚心地,没有任何官架子地和自己下面的普通人,尤其是和其中所谓的“弱势群体”打成一片,就好像王璞同志和我这个普通教师这样打成一片,并且成为好朋友,那么,我们国家每一个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定会极大地调动起来,我们的国家定会在和谐稳定的局面下,迅速而高效地走向富裕、安康和强盛。
我的书橱里有一本王璞同志拿给我看的记录反右斗争如何荒谬的书(他知道我曾是个“右派”),还有一瓶他送我的老酒。我要永远珍藏它们。看到这本书和这瓶酒,就好像见到他本人,就好像他还时时站在我身边,教我如何工作,如何处世做人,鞭策我继续不断地为我们党和国家作出贡献。
但是,王璞同志却永远地离我们而去了。
我的好同志,好领导,好朋友王璞,愿你安息!
2005年11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