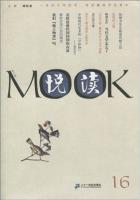这时工友群中又有一个人挺身而出,接着金大姐的话说:“对,不是破坏!你们就不该让他干这个!”
我认出来,说话的是一位平时不吭声,也从没跟我交谈过的人,我原先以为他不愿理睬我这样的人,偶尔遇见他便绕开走。这人在群众中显然很有威信,他一说话,马上许多人都纷纷说话,都跟随他为我辩护。
这时我的车长小刘站出来,他向大家证明说,我的劳动态度的确很好。事故的原因是我没有干这种活的经验,也怪他没有好好教过我,他说他有责任。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说,那只框架本身是扭曲变形的,没有经验的人很难把它摆放稳当。但是这绝对不可能是故意破坏。
副主任在众人面前没有再说话。他和在场的几个干部交换一下眼色,便丢下我,一同往小天井外面走,去另找个地方商议问题,人群跟随着他们走去。金大姐没有走开,她和另一位女工留下守在我身边,她们叫我不要怕,要我把一瓶盐汽水喝掉,又去给我找来一瓶。
第二天,我调换了工种。叫我去清扫边脚废料,是极肮脏也极易伤手的工作。高温营养汤没有了,糖水橘子没有了,工钱也降低到一块四毛钱一天。比在漂染厂还少两毛。我奇怪,他们为什么不开除我?
游街示众
我并没有逃脱那位副主任的手心掌。他们留下我是为了派更大的用场的。
几天后的下午,我正在扫垃圾,忽然喇叭响起,宣布全厂暂时停工。大家正在纳闷,只见一队头戴藤帽手持梭镖的“造反派”冲进了车间。他们直向我扑来,把我一巴掌打翻在地,立刻用一根粗绳把我五花大绑起来。这时喇叭里正在大声地宣布说,我不仅前几天制造了重大的生产事故,而且是本市一个暗藏反革命集团的重要成员。幸亏现在被他们挖了出来。喇叭里说:“这不仅是本厂,而且也是全上海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重大战果,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怎么?我是什么“反革命集团”的成员,抓出我来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尽管这时我正被五花大绑着往外推,全厂的工人都拥在两旁观看,我心里却真是不怎么恐惧。因为我明明知道,他们声嘶力竭地喊出来的那些话,全都是胡说八道。我怎么会是什么“反革命集团”的成员?!这一点做人的自信我还是有的。这一辈子,无论走到哪里,无论遇到什么事,就凭这一点自信,我从不曾自暴自弃。在这一顷刻间,也是这种自信在支撑着我,没有被吓倒。我在人群中看见了金大姐惶然不解的面容,真想走过去对她说一句我不是反革命,请她放心。
然而他们制造的那股声势的确是很“浩大”的。当我在一大群头戴藤帽的人的蜂拥下被推出厂门时,我看见,那条弄堂和那条小街的居民都已经涌出来看热闹了,弄堂的路上和那条街上已经用白粉涂上了巨大的标语字:“揪出现行反革命分子(这里是我的名字,三个字上都划上红叉叉)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把我这样一个“分子”揪出来,竟然也是“伟大的胜利”!我这时没有觉得害怕,反而觉得滑稽。我的倔强的坏脾气这时反倒给我了强大的精神支撑。我不觉扑哧一声笑出来。
“你还笑!你个反革命!”
跟在我身后扭住我手臂的那个藤帽人大声训斥我,同时在后脑勺上给了我一拳。
我被推上一辆停在弄堂口的大卡车,命令我直立在正中央,仍然五花大绑着,上半身露出在司机棚的上方。我的两旁威风凛凛地站立着八个藤帽梭镖的“战士”。车子沿着大街一路向前开。街上的行人都在对我观看。我生平第一次被这样游街示众,倒也是一次新鲜的体验。
大概是在车子开过“大世界”游乐场门口的时候,猛然间我问自己:这不就是押赴刑场去枪毙吗?这本来是无稽的想法,但让我突然忍不住地潸然流泪了。我不是怕去死,的确不是,而是想到我年幼的一儿一女和我七十多岁的爹娘。他们以后怎么办!
片刻之间我头脑昏眩,不能思索。古往今来那些绑赴刑场的犯人大概都是这样感受的。
卡车继续缓缓向前开,既是游街示众,当然不能开快了。这“示众”的游行不仅是为了让人民群众看清一个反动分子的模样,推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而且更是为了让群众看见并记住卡车两旁的大红布上标出的这家工厂的名字,因为这是他们为“文化大革命”做出的“伟大”贡献。
而就在这缓缓行进之间,我的头脑渐渐清醒起来。我想到:应该不会是去枪毙。因为枪毙人,是要经过审判,判决,宣判等等手续的。而且一定会有警察军队之类的参加,不会是如此地草率。车子越往前开,我越觉得不像是去枪毙。而那八个梭镖大汉互相之间的交谈,更是为我证实了这一点。我听见他们在说:快到厂部了吧?……今天晚上把这个人关在哪里?……
原来我被揪出的地方只是这家工厂的一个小分厂,由于总厂的运动老是开展不起来,需要有一个用于批斗的“对立面”,他们在那天我惹祸后并不立即开除我,原因就在这里。现在,总厂的革命造反派便来抓我到那里去。既然不是去枪毙,我的心放下了,我便高昂起头,观看着街上观看我的人群。
车子开到总厂,停在办公楼前。
批斗
当天召开对我的批斗大会。全厂为此停工。
一阵“打倒某某某!”“某某某死路一条!”的口号声中,我被带进批斗会会场,双手反绑着,头上戴着为我特制的高帽子,足有两尺多高,上面写着“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划上红叉叉的我的名字。走进会场后,藤帽们又把一块很重的,也写着“现行反革命×××”的木牌用很细的铅丝挂在我的头颈上(那根铅丝勒出的伤痕大半年都没有消退)。这时我想抬头也抬不起来,只能“低头认罪”。
主席宣读我的罪状时,我才知道,为什么他们找到理由最终把我定性为“现行反革命”。
我的一个中学同学那时正在一条远洋船上做大副,在他们那里的运动中,他被指控为组织反革命集团,阴谋驾船逃跑,背叛祖国。他被隔离审查,同时全面调查他的社会关系,其中便有我。我是一个学外语的,于是有了这样的推理:此人要叛逃,一定要用上外语,我这个懂几门外语的同学一定是他“反革命集团”的成员。他们恰好这时前来调查我,也恰好给了那位副主任一个最佳的认定我为“现行反革命”的机会。我不是刚刚有过一次破坏生产的“反革命行动”吗?这一定是我和我同学的“反革命集团”全部破坏计划的一部分。于是,他们安排了这次揪出我的重大的“革命行动”。
声势是很大的。但是,既然没有被枪毙,而是这样来“批斗”,我的自信心又起作用了。会上的发言都是事先安排的,说什么,我是一个企图驾船外逃的反革命集团的“外交部长”,我每个月拿外国人多少美元等等,他们嘴里吐出来的这些话全是狗屁,连他们自己也不会相信。这就是他们这个工厂在“清理阶级队伍”的“伟大运动”中所取得的“伟大成果”。拿我一个临时工做牺牲品,为他们自己向上级报功请赏。如此而已。那些安坐在会场里的工人群众其实是什么也不知道的。我从他们望着我的眼睛中,看不见什么“阶级仇恨”的目光,而只看见某种不敢形于言的同情。尤其是当造反派代表介绍我的“北京大学教师,高级知识分子……”等等履历时,我还听见台下不断有人发出啧、啧的叹赏声。这些生活在我们国家最底层的广大劳动群众,是最可爱的人。
批斗会在黄昏时结束,他们把我关进一间地下室。里面什么也没有,地上铺着一张稻草席子。我心想,今天,还有以后不知多少天,我就要以此处为家了。已经九月下旬,晚上会很冷,没有被褥怎么办?……
想不到,半小时后,我被领出地下室,带到厂部人事科。两个干部和我谈话。态度虽不像刚才斗争会上那样凶恶,但是也并不和善。他们向我宣布决定说:“经过研究,也是出于对你的信任,我们决定,你还是回家去,但是每天早上必须到这里来报到。在这里考虑问题和交代问题。每天的一块四毛钱工钱照发。”
这很出我意外,也很让我满意。因为每天一块四毛钱照发,这对我是最重要的。而且还不要我上工。至于交代问题嘛,我一点也不害怕,因为我根本没有任何他们所谓的问题可以交代。但是我很愿意让他们养着当一个专职的“对立面”,每天来“交代问题”。只要给我那一块四毛钱的工资就行。最好这样的日子能长久延续下去。
我“欣然同意”后,马上起身要回家。这时那两人中间的另一个郑重对我说:“你不要想不通,做出什么傻事情。我们正式告诉你,你离厂以后,出任何事情,都是你自己负责!”
他们是怕我回家去自杀。我听了只觉好笑,甚至已经笑出声。我回答说:“我不会去死的!我又不是你们说的什么‘反革命’。我的父母儿女还要我养活呢。”
我的倔强令他们吃惊。那你们就吃惊去吧。我转身就走。
再次失业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来到离家很远的那个总厂。先是去毛主席像前“请罪”,然后进入关我的地下室,那是我专用的“办公室”。人事干部给我一大摞纸和三支笔,叫我“写交代材料”。吃饭时,他们怕我和工人接触,只许我在开饭后一小时去厨房买饭,而且只许买一毛钱以下的菜,因为好菜只能给好人吃,坏人不配吃。这些管人的人哪里知道,那几天里,厨房的大师傅们每顿都给我吃一块,有时还是两块大排骨,并且按上面的规定,只收我一毛钱。
我被这样关押了半个多月,日子过得很舒服,既不要干活,也不会再有什么人来抓我去当“对立面”,或者接受“批斗”。因为我已经是这里的每天一元四角钱买下的专用“对立面”了。唯一不好的是,每天要多花几毛钱的车费。他们指定要我“老实交代”我那天在烘房里“搞破坏”的经过和动机,还交代我和那个大副同学的关系。这很好办,我用他们提供的纸和笔,详详细细地陈述了我那天惹祸时的身体状况,心理状况,动作过程,以及外在的环境,温度,钢板的重量,小车的滑动,框架的变形等等。反正全是百分之百的真话,完全经得起调查。我给自己做出的结论是:我根本没有搞过任何的破坏,这次没搞过破坏,这辈子无论在哪里都没有搞过破坏。至于我和我那个同学的关系,就更有可写了,我像写小说一样,把我和他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同读了六年中学的日子,好好地描写了一通,我们之间在上海的交往,也“交代”得十分仔细,全都是绝对的实话,完全经得起调查。我对批斗会上所说的,我是个什么“反革命集团成员”,“外交部长”,我每月拿多少个美元的话,提出我的抗议,要求他们在调查清楚以后对我公开道歉。我每天都在那里不停地写,每天交上去,总共不知写了多少页。
我在我的专用办公室里过了半个多月以后,这一天,他们把我叫到人事室去,宣布对我的“决定”。
还是那两个人事干部。他们的决定是:经过初步调查,有些事情“基本弄清楚了”。从明天起,我不用到他们这里来了。他们“开除”了我,我的临时工身份没有了,从此与他们厂无关,他们要把我送回街道,去“继续交代其他问题”。
我立刻问他们:“哪些事情弄清楚了?那天烘房的事是不是我搞破坏?我是不是什么反革命集团的成员?是不是什么‘外交部长’?我到底拿过谁的美元报酬?”
两个人相互望一望,然后其中一个故作严厉地对我说:“怎么?你要反攻倒算吗?这是搞运动,你知道吗?运动里面,群众革命积极性高涨的情况下,说几句过头话是很正常的事。你如果能站在正确的立场上,就能理解这一点,就不会像你现在这样耿耿于怀地计较!”
“那总要有个明确的结论!我不能背上个反革命的名义回家去!我到底是不是现行反革命?”我要他们回答我。
“不是告诉你,基本上搞清楚了吗?你还要怎么样!”
“那我到底是不是现行反革命?”我非要他们回答我。
他们躲不开我的问题,只能回答说:“现在可以说不是。”
“那你们当初为什么说我是,凭什么揪我,打我,关我,批斗我?”
他们发怒了,两人不约而同地拍案而起。其中一个对我喊叫着说:“你太猖狂啦!就凭这点就能再关你几天!‘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这两句话你听见过没有?”
我听见过这两句话的。这是那个年代里流行的一种似是而非的逻辑。听说是从哪个大人物嘴里出来的,后来被下面的人奉为经典。其实,既然后来“查无实据”,那么前面那个“因”就是个错误的因。凭错误的“因”产生的“事”必定是错误的事。但是错了就必须加以纠正。我把这个明白的道理说给他们听,并且要求他们就他们对我个人所做的种种侵犯向我道歉。
他们好像从来没遇见过我这样大胆狂妄的人。两人中的那另一个再次把桌子一拍,忽地立起身来,吼叫着说:“这些道理你回去对你们街道的人说去!你和我们没有关系了!走!”
说着便把我往房间的门外拉。办公楼外停着一辆吉普车,他们不由分说把我拉上了车。我无力和他们挣扎,但是我能说话,我问:“这是到哪里去?”
“送你回你们街道。”原来我今天有专车坐。真是荣幸得很。后来我知道,当时有这样的规定,凡是有问题的人,必须一层层有人管着,他们开除了我,就必须把我移交给街道和里弄。
到达我所在的街道办事处以后,再由我所在的里弄来接管我。下面就发生了那位里弄小组长魏大姐挺着她高耸的前胸向我逼来,大声骂我“你个反革命!”的那一场戏。
我又再一次失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