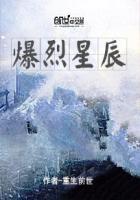正是由于对别人痛苦的麻木不仁,在巨大的苦难中仁慈大度就总是显得如此圣洁高雅。一个人能在大量的小灾小难中保持轻松愉快,他的行为就总是体面而令人愉快的了。他似乎比能以同样的姿态承受最可怕的灾难的人还要更高一筹。我们能感觉到需要做出多么巨大的努力才能使处在他的那种环境中必然要激起的那种狂暴的感情平静下来。我们惊讶地发现他竟然能够完全控制住自己。在这个时候,他的坚定与我们的麻木完全吻合一致。他并不要求我们同样具有那种高度的敏感。而且我们痛苦地发现我们全然不具备那种敏感。于是在他的情感和我们的情感之间存在着一种最完美的默契;而且正因为那一点他的行为显得那么适度,而且它也是一种我们根据人类天性的弱点没有理由指望他能保持的适度。我们惊讶他的心灵竟然具有如此巨大的力量,能够做出如此高尚的行为。混合看惊讶地完全同情和赞赏的情感构成了我们不止一次看到过的人们通常恰如其分地称之为钦佩的情感。加图在遭到敌人四面包围,无力抵抗的时候,他坚守那个时代所推崇的高尚的格言,他不屑向敌人屈服。他从不在不幸中退却,也从不用不幸者的悲痛欲绝的声音来恳求我们平常极不愿流的同情的泪水。相反,他用男子汉的坚定武装自己并且在他执行其最后的决策前的一分钟用他惯常的平静为了他朋友的安全发出了所有必要的命令。看来,对那个冷漠的伟大的布道者塞内加来说,这是众神都会怀着愉快和钦佩的心情来注视的一个场面。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每当我们看到这种高尚的英雄行为时,我们都是极为感动。与那些为了些许的悲痛便痛不欲生的人相比,我们更倾向于为这些把个人痛苦置之度外的人而流泪。在这种特殊的场合旁观者的同情性的悲伤反而显得超过了当事人的原始激情。当苏格拉底吞下最后的一口毒药时,他的朋友们都哭了,而他自己却表现出了极度愉快的宁静。在所有这样的场合,旁观者没有,也没有必要去做出任何努力来克制其自身的同情的悲伤。他丝毫不担心他会有什么表现得过于夸张和不得体。相反,他为他自己的内心感觉感到愉快,对自己内心的感觉感到满足和赞许。因而,他愉快地沉溺于对他来说可能必然产生的最使人抑郁的想法,关于他朋友的灾祸也许他从来没有感觉得如此细腻,如此温柔和令人流泪。然而,当事人则恰恰相反,他却必须尽可能把自己的眼光从在他的处境中显得恐惧和令人不快的东西上移开。他害怕过于严肃地注视那些东西会使他狂暴,会使他再也无法保持冷静,换句话说会使他无法成为旁观者完全同情和赞同的对象。因此,他把自己的思想完全集中在令人愉快的事物上,集中在他将赢得称赞和钦佩的豪迈的英雄行为上。在感到自己有能力做出如此高尚和慷慨的行为,感到在如此可怕的境况下仍能像在做自己所愿做的事情那样时,他就充满朝气,陶醉在快乐之中,并能保持仿佛在战胜自己的不幸中获得胜利的那种欢乐。
相反,那种由于个人的灾难而陷入悲伤和沮丧中的人,则总是显得卑劣和可鄙。我们不可能使自己有他的感受,甚至不可能使自己有万一自己处于他的境地的感受;也许,有什么情感可能被视为不公平的话,那也是天性不公平使我们无法抗拒地决定了的。悲伤的弱点从来就没有显得令人愉快过,除非是在我们为别人,而不是在为自己而悲伤的时候。一个儿子在溺爱他的并且值得尊敬的父亲去世的时候,可以大量发泄他的悲伤,而不受到任何指责。因为他的悲痛主要是建立在对他死去的父亲的一种同情之上。因之我们也乐意进入这种人道的情感。但是如果他仅仅只是由于自己个人遭受到了什么不幸,而沉溺于这种弱点,他就将得不到任何这种宽容。如果他因此而沦为乞丐和毁灭,如果他面临极端可怕的危险,甚至将被公开处决,而在断头台上流下了一滴眼泪,那么在所有勇敢而豪迈的人们的心目中则将永远是一种耻辱。虽然他们对他的同情将是十分强烈的,也是非常真诚的;但是无法原谅他把自己这样暴露在世人眼中。他的行为将使世人感到羞耻,而不是感到悲伤。而且他这样给自己带来的羞辱将成为他不幸中最可悲的事件。那个在战场上曾无数次勇敢地面对死亡的坚强无畏的比朗公爵,当他看到他的国家毁灭时,当他回忆起只是由于自己的轻率,而为此不幸地被爱戴和荣誉所抛弃时,他在断头台上流泪了。而这一软弱给他的名声带来了多大的耻辱啊!
(第二章)论野心的起源以及社会阶层的区分
因为人类乐于同情我们的快乐,而不大乐于同情我们的悲伤,所以我们炫耀我们的财富,而掩饰我们的贫困。没有什么东西比被迫在公众面前暴露我们的贫苦更加令人感到羞辱的了,虽然没有什么东西比把我们的处境公开在所有世人的面前令人感到更加难堪的了,然而没有比无人能想象出我们所受的痛苦的一半更加令人感到难过的了。而且,主要是出于对人类这种情感的考虑,我们追求财富和回避穷困。这个世界上的劳碌和奔波究竟是为了什么呢?什么是贪婪和野心,追求财富、权势和至高无上的最终的目的呢?是为了满足天性的要求吗?那么一个最卑贱的劳动者的工资就可以满足了。它足可以为他提供一个家庭的衣食住。如果我们严格地考察一下他的开支,我们定会发现其实他大部分的工资都是花费在了生活便利品上,而且那些东西都可以被视作是多余的东西。同时我们也会发现在某些特殊的场合,他甚至会花费一些钱在爱慕虚荣和获取名望上。那么我们对他的境况感到厌恶的原因又何在呢?那么为什么在上层社会里受过教育的人要把他的处境——甚至无须劳动,同他吃一样简单的伙食,住在同一低矮的屋檐下,穿同样朴素的衣服——视作还不如死呢?是他们认为他们的胃比较高贵,或者在宫殿里他们要比在茅舍里睡得更香甜呢?而人们常常所见的正好相反,而且显而易见确实也是如此。虽然从来没有人说出过,但是没有人不知道这个事实。那么贯穿所有不同阶层人们间的那个竞争又是怎么产生的呢?我们通过我们称作的不断改善我们生活条件的人生伟大目标而想得到的好处又是什么呢?受到注视、受到关注、受到重视以及同情、自我满足和赞同,所有这些都是我们能够指望从中获得的。然而吸引着我们的是虚荣,而不是安逸或快乐。但是虚荣总是建立在深信自己是关注和赞同的对象的信念上的。富人为自己的财富而感到荣耀。因为他感到他的财富自然会引起世人对他的注意,他感到人们都乐于附和他的所有这些令人愉快的激情,而这些令人愉快的激情正是他的地位极其容易在他身上所激发的。想到这一点,他的心仿佛都膨胀大了并扩大到了他的全身。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对他的财富比对他所能获得的其他好处更加热爱。相反,穷人为自己的贫困而感到羞耻。他感到穷困要么使人们根本就不理睬他,即或他们对他有什么关注,他们对他所遭受的悲惨和苦难也不会有什么共同感。由于上述两个原因他感到受到了屈辱。因为被忽视和不被赞同尽管是两件全然不同的事情,然而如同朦胧遮住了荣誉和赞同的阳光,使它们照耀不到我们一样,感到我们自己的被忽视必然使人性中最令人愉快的希望发潮,使人性中最炽热的欲望感到失望。穷人走进走出无人注意,当他们处在人群中时也是处于同样的朦胧之中,宛如把自己关在自己的陋室里一样。给予处于他的境地中的人们的任何卑微的关切和讨厌的照料不能给放荡的人提供任何乐趣。他们不再看望他,或者如果他的极度的困苦使他们不得不看他一眼时,那也仅仅是为了把如此令人不快的一个事物从他们中剔除出去。那些幸运的和得意的人对这种不幸的人竟敢出现在他们的面前所表现出的这种无礼,并且用自己令人厌恶的惨状来扰乱他们幸福的宁静而感到惊讶。相反,有地位和有身份的人为世人所尊重。每一个人都渴望去看看他,并且想象一下(至少是通过同情)他的处境必然会在他身上激发出的那种快乐与狂喜。他的一举一动都是公众关注的对象。他说的每一句话,他做的每一个手势都全然不会被人忽视。在盛大的群众集会上他是所有的眼睛注视的焦点。他们把视线集中在他的身上,他们期待着,希望能从他给他们的印象中得到指点;而且,只要是他的行为不是全然荒谬的,他就时时刻刻有机会吸引着人们,使他自身成为关注的对象以及他周围每个人同情的对象。虽然伴随着这一点会给他加上一种限制,使他丧失自由,然而这一点更使大人物成了羡慕的对象,并补偿了在追求它的过程中他所必须经历的辛劳、焦虑和苦难;而且更重要的是为了得到这一点他必须永远丧失所有的悠闲、安逸和无忧无虑的安全感。
当我们用想象所乐于使用的那些虚妄的色彩来描绘伟人所处的条件时,他的生活条件几乎显得像一个完美和幸福状态的抽象概念。这正是我们在所有的白日梦和懒散的梦想中给自己描绘出来的最终目的所处的那种状态。因而,我们对能处于那个状态中的人的满足抱有一种独特的同情。我们赞同他们所有的爱好,支持他们所有的愿望。我们认为任何破坏和损坏一个如此令人愉快的环境的东西都是一个极大的遗憾。我们甚至希望他们能够永恒不死,而且对于死神将最终给如此完美的一种享受画上句号似乎感到难以接受。我们认为造物主把他们从显贵的位置驱赶到造物主为他所有孩子准备的那个卑贱然而好客的家里去实在是太残酷了。“伟大的国王万寿无疆!”是按照东方的奉承方式讲的一句恭维话。如果经验不曾告诉我们那是荒谬的话,我们将会很乐意说这种恭维话。降落在国王们身上的灾难,对他们身上的每一个伤害,在旁观者的心中所激起的同情和愤恨要比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别人的身上时所激起的同情和愤恨大十倍。正是国王们的不幸才为悲剧提供了适当的题材。在这一方面它们类似恋人的不幸。这两种处境都是戏剧中引起我们极大兴趣的主要东西。因为尽管理性和经验能告诉我们相反的东西,但是想象力的偏见热衷于给予这两种状态一个其他任何事物所不可能有的幸福。因而去扰乱或终止这样一种完美的享受就显得是所有一切伤害中最残酷的了。阴谋杀害君王的叛徒被认为是比所有其他杀人犯更为可恶的魔鬼。在内战中所有无辜者所流的鲜血引起的义愤都不如查理一世的死所激起的义愤那么强烈。一个不了解人类本性的人,在看到人们对他们下属的悲惨所表现的冷漠和看到人们对地位比他们高的人所遭受的不幸和伤害所表现的遗憾和义愤,将会以为上层人物的疼痛和临终时的抽搐要比地位低下的人们的疼痛更加剧烈,抽搐更加可怕。
人类正是在对富人和有权势的人的所有激情的认同的倾向上建立起了等级的差别和社会秩序。我们对地位高的人所表现的谄媚更多是出于我们对他们地位的优越的羡慕,而不全然是出于指望从他们的善意中得到什么个人好处。能够受到他们的恩惠的人只有少数几个,而他们的财富却几乎引起了所有人们的关注。我们愿意帮助他们实现一系列十分接近完美的幸福,我们愿意为了他们的满足而为他们服务,除了表示我们施恩于他们的一种虚荣心和荣誉外,并不要求其他任何补偿。我们对他们的意愿的遵从,并不主要是或者说完全是建立在对这种屈从的效用以及主要由其支撑的社会秩序的考虑上。甚至当社会秩序看来要求我们反对他们时,我们都很难接受这一点。国王是人民的公仆,根据公共利益的需要应该服从他们、抵制他们、废除他们或者惩罚他们,这是理性和哲学的原理,但不是造物主的旨意。造物主教导我们为了他们的原因去屈从他们,在他们至高无上的地位面前战栗膜拜,把他们的微微一笑视作一种足以补偿所有效力的奖赏;同时唯恐他们不满,尽管他们的不满并不会引起别的什么不幸,却把他们的不满当作最大的耻辱。在各方面要把他们当作一般人来看待,在通常场合与他们理论和争论需要极大的勇气,恐怕没有人有这种气魄能够敢于这样做,除非他们具有某种家庭和亲属关系。最强烈的动机,最狂暴的激情,害怕、憎恨和愤恨都不足以抵消这种对他们的天然的尊敬的倾向。他们的行为不论是公正的或不公正的,必然是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已激起了极大的不满,广大的人民群众才会起来用暴力对抗他们或者希望看到他们受到惩罚或废黜。甚至即使达到了这个程度,他们时刻都可能手软,旧病复发,习惯地遵从那个他们一贯视为天生高于自己的人。他们不能接受对君王的侮辱。同情马上就替代了愤恨,他们忘记了他过去所有的恶行,他们旧的忠君的天性复活了,于是他们又用他们从前用以反对旧主的暴力去重建他们旧主的被破坏了的权威。查理一世的逝世带来了皇室的复辟。当查理二世在船上企图逃跑被逮捕时,对查理二世的同情几乎阻止了革命,使得革命进行下去比以前要更加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