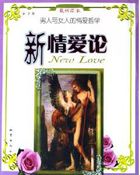但是对于一个聪明的人来说,对于一个其激情完全屈从于其天性中占统治地位的本性的人来说,在所有场合完全遵循这个适度是同样容易的。如果他处于兴盛时期,他就会为他能够与易于掌握而且没有任何做坏事的诱惑的环境融为一体而答谢丘比特。如果他处于危难之中他同样答谢人类生活的这个场景的导演,把一个健壮的田径运动员置放在他的对立面,要战胜他虽然竞争可能会更加激烈,但胜利却更加光荣,而且同样具有把握。如果我们自己没有任何过失,而且我们的表现又是十分得体,对于在这种情况下降临我们头上的灾难,我们能有什么可感到羞耻的呢?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有什么邪恶,相反,只有最大的善和最大的好处。勇敢的人为被卷入并非出于他个人的鲁莽,而是由命运的安排而被卷入的危险而欣喜。它为表现英雄的坚忍不拔提供了机会,这种坚忍不拔的努力使他感受到一种从对自己高度的适度和应该得到赞美的意识而宣泄出来的欣喜。一个运动大师绝不会不乐意去与最强壮的人较量自己的力量和敏捷。同样,一个能够掌握各种激情的人不会害怕宇宙的主宰把他放置在它认为适合于他的任何环境之中,神的恩惠使他具备了能驾驭各种环境的美德。如果处境是快乐的,他就用节制去约束他;如果处境是痛苦的,他就用坚贞去忍受它;如果处境是危险或死亡,他就用宽宏大量和坚忍不拔去蔑视它。他对人类生活中的各种事件都不会束手无策,或者茫然失措,不知如何保持情感和行为的适度。在他的理解里正是这种适度同时也就构成了他的光荣和幸福。
斯多亚学派的人似乎把人类生活视作一种竞技游戏。不过,在这个游戏中混杂着一种机遇,或者一种庸俗地理解为所谓机会的东西。在这种游戏中赌注通常是微不足道的,游戏的全部乐趣来自玩得好,玩得公平,玩得有技巧。如果,一个好的参赛者使尽了他的全部技巧,然而由于运气不好,输了。那么,输也应当是一种乐事,而不是一件值得伤心的大事。因为他没有一次失手的地方,他没有做任何应该感到羞愧的事。他充分地享受了整个游戏的全部乐趣。相反,如果他是一个不好的参赛者,尽管他有过很多失策的地方,同样,由于偶然的机会他赢了,那么他的成功也只能给他带来极小的满足。因为一想起他所犯的全部过失,他就会感到羞辱,甚至在游戏的过程中,他也享受不到游戏所能提供的那一点乐趣。由于对游戏规则的无知,几乎在他每走一步之前,他都会产生恐惧、怀疑、犹豫——这些令人不快的情感。当他玩完了游戏之后,当他发现那是一个大的失误时,羞辱通常会把使他不快的情感推到顶峰。人类生活连带与其伴随而来的所有好处,照斯多亚学派的看法都只应视作一个仅仅两便士的赌注,一个远不值得任何严重关注的小事。我们唯一应当关注的是游戏的适当方法,而不是赌注。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幸福押在赢得赌注上,我们就把幸福放在了超越我们能力之外和我们所支配不了的原因之上了。那样,我们必然会使自己面临长期的恐惧和不安,甚至常常面临令人悲伤和令人羞辱的失望。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幸福放在玩得好,玩得公平,玩得机智巧妙上,简而言之放在我们行为的适度上,我们把它放在通过适当的纪律、教育和用心完全能够在我们的能力之内,在我们的指挥之下的什么东西之上,那么,我们的幸福就是完全有把握而与命运无关的了。如果我们行为的结局超越我们能力之外和我们的关注之外,那我们就绝不会为它感到恐惧或焦虑,我们也不会有什么悲伤或什么重大的失望。
斯多亚学派的人说,人类生活本身就如同伴随生活而来的各种不同利弊,随着环境的不同,它们可以是我们的选择的适当对象或者摒弃的适当对象。如果在我们的实际处境中,使天性感到愉快的情况多于令其不愉快的情况,可作选择的对象的情况多于可摒弃的对象的情况,在这种场合生活整个来说就是选择的适当的对象,而且行为的适度要求我们继续留在这个处境里。另一方面,如果在我们的现实的处境中不可能有任何改善的希望,违反天性的情况多于令天性感到愉快的情况,作为我们摒弃的对象多于作为我们选择的对象,在这种场合,生活本身对于一个聪明的人来说已成为了摒弃的对象,他不仅有权摆脱它,而且行为的适度、诸神为了指导他的行为而为他制定的准则也都要求他这样做。爱比克泰德说过,神命令我不要住在尼科波利斯,我就不住在那里;命令我不要住在罗马,我就不住在罗马;命令我住在多石的杰尔小岛上,我就到那里去住。杰尔小岛上的屋子里冒湿气,如果湿气冒得不厉害,我忍受得了,我仍将待在那里。如果湿气冒得太厉害,我就会搬到一栋没有什么暴君能够把我赶走的房屋里去。我总记着的是门是开着的,在我高兴的时候我就可以走出去,而且还可以隐退到时刻向世上所有的人都敞开着大门的那栋好客的屋子里去。因为除了我的内衣、除了我的躯体,没有一个活人有任何权利可以支配我。如果你的处境基本上是令人不快的,斯多亚学派说,如果你的屋子对你来说湿气冒得太厉害,你就尽一切方法走出去。但是你走出去,不要发牢骚,不要咕咕哝哝或者抱怨。冷静地往前走,心满意足地、快快活活地,感谢诸神,出于它们的无限的恩惠它们打开了通向死亡的安全而平静的港口,时刻准备接受从人类生活中充满风暴的海洋漂来的我们,它们准备好了这个神圣的不可亵渎的伟大的避难所。它总是敞开着大门,随时可以进出,人类的狂怒和不义对它全然不能有所作为。而且它大得足以容纳所有愿意和不愿意进去隐居的人;它夺走了所有的人抱怨的所有借口,甚或幻想的借口。以为人类生活中除了由其自身的愚蠢和软弱所招致的伤害以外,不可能还有其他的邪恶。
在斯多亚学派流传给我们的一些有关他们的哲学的片段中,斯多亚学派在谈到死亡时有时带着一种欢乐甚至轻浮。如果我们认真思考这些片段,他们可能诱使我们相信他们以为我们在任何时候只要我们下了决心我们为了一点最细小的反感或不安就可以毫不负责地和任性地去死。爱比克泰德说,当你同这样一个人共进晚餐时,你会抱怨他给你讲述的有关他在迈西恩战争中的故事太长了。他说:“我的朋友,现在我已经给你讲完了我是怎样在这样一个地方占领一个高地的,这会儿我该跟你讲我是怎样在另一个地方陷入包围的了。”但是,如果你决意不去忍受他的冗长的故事的烦恼,你就不要去吃他的晚餐。如果你要去吃他的那顿晚餐,你就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对他的冗长的故事进行抱怨。对于你所称作的所谓人类生活中的邪恶,情况也是这样。不要抱怨你自己随时可以有能力摆脱的东西。是选择死还是生,尽管说起来可以带有这种欢乐和轻快,但是照斯多亚学派的看法,仍然是一件值得最严肃和最慎重思考的事情。在我们得到最初赋予我们生命的那个主宰明确的召唤之前,我们决不应放弃生命。但是,我们也应当考虑到在人类生命的指定的无法避免的期限以内,而且随时都可能被召唤去这样做。任何时候,当那个主宰的天意使我们生存的条件大体上变成了我们应该摒弃的对象,而不是选择的对象时,主宰为我们制定的指导我们行为的伟大准则,那时也会要求我们放弃生命。那时就可以说我们听到了那个神的威严而又仁慈的声音明确地在召唤我们那样做。
照斯多亚学派的说法,正是基于这个原因聪明人即使在他完全幸福的时候也可能认为自己有责任放弃他们的生命;相反,软弱的人虽然他处境十分痛苦,他可能认为自己仍有责任继续活下去。如果在聪明人的处境里作为该摒弃的天然对象的情况比作为选择的天然对象的情况多,那么整个环境就变成了摒弃的对象。同时诸神为他制定的指导其行为的准则就要求他摒弃生命,而且像特定情况所允许的,越快越好。不过,即或是在他可能认为他适宜于继续活下去的时候,他那样做仍是完全幸福的。他把他的幸福不是放在获得所要选择的对象里,或者放在避免他所要摒弃的对象里,而是总是放在准确适度的选择和摒弃之中;不是放在成功之中,而是放在他所做的各种努力的恰当之中。相反,如果在软弱的人的处境里,作为天然选择对象的情况比作为摒弃对象的情况多,于是他的整个处境变成了选择的对象,因而他有责任留在那个环境里。不过,他会由于不知如何去利用那些情况而感到不快。哪怕他的牌再好,他不知道如何玩,不论是在玩的过程中,还是不论以什么方式可能产生的游戏的结局中,他都不可能享受到什么真正的满足。
也许,斯多亚学派比古代哲学中其他任何学派更加坚持在某些场合自愿死的适宜性,不过这种适宜性也是其他所有学派,甚至包括主张和平和懒惰的伊壁鸠鲁派的一个共同主张。在古代哲学所有主要学派创始人的活跃时期,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及其结束后的许多年之后,希腊所有不同共和国内部几乎都是被极其激烈的派别斗争弄得人心惶惶。而国外,它们又相互进行最血腥的战争。每一个国家不仅寻求特权或统治权,而且还要彻底消灭其所有的敌人,或者也是同样残酷地,把他们驱入最坏的状况,变成家庭的奴仆,把他们(男人、女人和孩子)像牲畜一样,出卖给市场上叫价最高的人。那些国家大部分都非常狭小,这种狭小使得它们中的每一个都可能陷入那种也许它过去实际上常常遭受过的,或者至少是企图使其某些邻人遭受过的灾难。在这种混乱的状态中,即使最清白无辜加上最高的地位和最大的公共职务也不能保证任何人的安全。甚至自己的家里和自己的亲属和同胞中的任何人的安全。而在某个时候,由于盛行的激烈的敌对的派系斗争,他也不能保证自己不会被判以最残酷和最不光彩的刑罚。如果他是在战争中被俘,或者他所在的城市被占领,可能的话,他还会要遭到更大的伤害和侮辱。每个人自然而然地,或者说必然地会想象或经常地想到和预见到他的处境可能使他面临的灾难。一个水手不可能不常常想到风暴和船只失事沉没在海上,同时也常常会想到在这类情况下他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和行动。同样,一个希腊的爱国者或英雄不可能不使他的想象熟悉他意识到的他的处境必然会时常或者长期地使他面临的所有各种灾难。如同一个美洲野人在准备他的丧歌时,他考虑着当他落入敌人的手中,敌人在通过慢慢的折磨把他处死,以及当他处于所有旁观者的侮辱和嘲笑之下时,他应当怎样行动一样,一个希腊的爱国者或英雄不可避免地会时常思考当他沦为奴隶,当他受拷打,当他被带上绞刑架时,会遭受到什么样的痛苦,在被放逐和被俘时他应当做些什么。而所有不同派别的哲学家们都把美德,那就是聪明、公正、坚定和有节制的行为不仅表述为通向今生幸福最有可能,并且是可靠而且绝无错误的途径。然而,这种行为不一定总是能使奉行它的人免除面临伴随国内不稳定的局势而产生的各种灾难。因而,他们竭力表明幸福或者全然或者至少是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命运无关的。斯多亚学派的人认为全然无关,而学院派和亚里士多德学派的哲学家则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如此。首先,明智、谨慎和良好的行为是最可能保证每项事业成功的行为。其次,即使没有获得成功,但人心也还是得到了安慰。有道德的人仍然可以享受其内心的完全的赞同,而且仍然可以感觉到不论外界的事务是如何不顺利,内心却仍然是平静、和平和和谐的。通常他可以感到安慰的是他深信他得到了每个明智的和公正的旁观者的热爱和尊敬。他们必然会赞赏他的行为,而为他的不幸感到遗憾。
同时,那些哲学家还竭力表明人类生活中易遭的最大的不幸比通常想象的要更容易忍受得多。他们竭力指出当一个人沦为贫穷,被放逐,受到群众的侮辱,在极端衰老和接近死亡时,双目失明和耳聋的情况下还要劳动时,仍然能够享受到的安慰。他们也指出在疼痛与折磨的极端痛苦的情况下,在疾病,在为失去儿女、为朋友和亲属的死亡等悲痛中也许能有助于支撑他的坚贞的一些思考。古代哲学家有关这些主题所写的东西中流传至今给我们的一些片段也许构成了古代文化遗产中最有教育意义和内容最精彩的部分之一。他们学说中的那种精神和刚毅的气魄与现代某些哲学体系中的沮丧、哀怨和哀哭的语调形成了一个极好的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