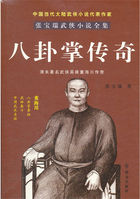我的心揪着,虽然我已经没有了心,我只能这样形容。我说没有心,是不想把献的心当做自己的心。孩子们究竟去了哪儿?我让献加快步伐去曹北家,可是我的灵魂并不能左右献,它不太愿意听我的。走到门口,它停下了。它朝着院子低声叫一声,小花听到了。它也呻吟了一声,算是回应献的呼唤。我听出来,小花受了重伤。献想不顾一切地冲进去,可它刚走到门口,就听到了令它恐怖的脚步声。于是,它又停下来,后退两步。大门吱扭一声开了,闪出一个身影。献夹着尾巴跑了,它知道那是曹北的表哥。
献惶惶如丧家之犬,不停地跑着。它实在跑不动了,才放慢了脚步。它跑过一个小区,路过一个开着门的小院,它太想停下来歇会儿。按理,它随便卧哪儿都可以,它不过是只流浪狗。可是,我的灵魂附在它身上之后,它似乎有些讲究了。
它怯生生地进了院子。我惊呆了,我的女儿项东,儿子曹西,跪在那里。他们面对一床花被子而跪。
我陡然觉得自己要哭了。可是,我没有眼泪,因为我是个灵魂。我用献的爪子碰了碰我的孩子们,他们厌恶地拍了它一下。献的眼泪流出来了,不是因为我,而是因为小花。
我知道这是宗剑的家,我来过一次。
宗剑家里的人都走了。夏柳和宗剑本来就准备离婚的,只是夏柳正竞争副院长,不便闹腾罢了。他们早已分居,况且又发生了这种事儿。
其实,公安局已经对我实施了尸检,结论也出来了。可是,曹北的表哥还是怀疑我和宗剑的关系。因为我死时,只有宗剑一个人在场,他要求宗剑赔偿。
项东和曹西已经接受了我的死亡,他们已经没有多少悲痛了。他们跪在那里,一句话也不说,可能是哀伤和羞辱让他们麻木了,毕竟他们还都未满十八岁。公安局已经通知曹北几次,要他赶紧把我葬了。都是曹北的表哥出面周旋,条件也是他提的。他确实是为了曹北和孩子们以后的生活着想的,他从来就没有想过会给我带来什么伤害。可笑!我已经死了,还讲什么伤害不伤害的?一切应该为了活着的人,这当然是曹北表哥的思维方式。
曹北表哥走近宗剑家大门时,献慌忙站起来,躲到垃圾桶后面。我笑它没出息。不过,它如果不躲,肯定会是一顿暴打。这叫“好汉不吃眼前亏”。献——“好汉”?我可笑,如果献都可以称“好汉”,那“好汉”就不是好汉了。
曹北的表哥还是进来了。他说:孩子,起来吧,别守她了,回家歇会儿,反正她走了,也不顾你们了。作孽!
项东和曹西跟他走了,我心里塞满了生离死别。我多想和他们再待一会儿啊,虽然我只是个灵魂,可是我爱我的孩子们。也许,我将永远也见不到他们了。我觉得眼泪已经滂沱而出,可是,献却无动于衷。曹北表哥的出现,已经使它收起了眼泪。于是,我愤怒了,朝着献。献也愤怒了,朝着曹北的表哥。我的愤怒加上它的愤怒,使献一跃而起,张开了大嘴。可它并没有上前去,大吠一声曹北的表哥,更不用说咬他一口了。献合上张开的嘴,从嗓子里发出一声低沉的呜咽。我和献沮丧地望着他们出了大门。
献已经感到危险离它而去,便想找点东西吃吃。它掀翻了垃圾桶,找到了一块已经发霉的蛋糕,津津有味地吃起来。
献勉强填饱肚子,走到花被子前卧下。这是我死后的第三天,第一次有人(或者是狗)为我的尸体守夜。我感谢献,它为我孤独的寒尸增加一丝暖意。是的,花被子下面盖着的就是我的尸体,那苍白的脸上更加暗沉的黑记,那剖开的胸膛和腹腔,还有被钳子插进插出的阴道,都是我曾经生存过的最后的证明。当然,伴着冰凉尸体的还有绯闻,它已经像空气一样灌满了小城。
是曹北的表哥坚持把我的尸体停放在宗剑家里的。献虽然静静地卧在我身旁为我守灵,可是,我知道它其实在想它的小花。
凄冷和悲哀漫过我的思维。我庆幸我还有思维,还能追忆生前的往事……
九 宗剑
从宗剑给我电影票那时起,我对宗剑的看法一直很好。他是那种很讨女孩子喜欢的男人,英俊大气,出身又好,父母都是县里的干部。可惜,那时他已经和夏柳谈上了。不过,我从来也没有想过会和他有点什么。
我和他真正的交往是我到妇产科上班后。那天,他表嫂分娩,正好我值班。他送了很多糖果、花生、瓜子之类的东西。他一直守在那儿,我跟他开玩笑说:宗主任,你对表嫂这么上心,什么意思啊?
他反击道:项医生,我可不和你开玩笑啊,你要是主动出击,我可就不客气了。
我笑着说:急了吧?
晚上十一点多,宗剑的表嫂生下了一个男孩儿,他们一家人欢天喜地。送走了他们一家,我准备上床休息。宗剑敲开了我值班室的门,送来了一饭盒热腾腾的鸡蛋茶。他说:项医生,辛苦了。其实,这是农村的风俗,孩子生下来,主人会给接生婆做一碗放上红糖的鸡蛋荷包茶。热腾腾的红糖鸡蛋茶,表示主人的谢意和喜兴。
我看着他倒出的红糖鸡蛋茶,觉得很可笑。对他说:你把我当成接生婆了。
他笑着说:你不是吗?我是遵我姑妈的命令,专门给你做的。
我还真没吃过这东西,我生儿子时,曹北的母亲也给我弄了这样的鸡蛋茶,我闻到那种腥味就反胃。
我说,我不吃这东西,怕那种腥味。他说:我做的保证不腥,不信你尝尝。我吃了,还真是不腥。我问他有什么诀窍。他说,你若是想吃,我天天给你做。我笑着说:夏柳还不把我骂死,只要告诉我做法就可以了。
提起夏柳,宗剑脸上掠过一层阴影,他旋即说道:其实,很简单,滴几滴麻油就行了。
吃完鸡蛋茶,我说:谢谢你,回去休息吧。我看你比产妇还辛苦。
宗剑说:我姑妈家几代单传了,知道表嫂怀的是男孩儿,姑妈一刻也不让我离开。怎么,吃完鸡蛋茶,就想撵我走?
没有,你要是真不困,就坐下来聊一会儿,反正有几个待产的孕妇,我也睡不成。
宗剑拉把椅子坐下。
我们一时没有了话题。我竭力地寻思着一个合适的话题,可脑子混混沌沌的,想不出一句得体的话,气氛很尴尬。他站起来,把门带上。我心里陡然一震。他又坐下来背对着灯光,一脸晦暗。他说:项南,你和曹北怎么样?
我没有说话,眼里有些潮湿。他说:我知道你心里很苦。我不该把电影票送给你。我很后悔,我甚至想,如果那电影票是我自己送的多好。
我觉得眼泪快要流出来了。我把脸往上仰着,以免泪水流下来。
说这些还有什么意思?
是的,我不该说这些。项南,你虽然不是个漂亮的女人,可你是让人尊敬的女人。你靠自己的勤奋和刻苦争取到自己的一切。从你自费进修起,我就对你另眼看待了。你的气质和能力,是你人格魅力的体现。你外表看起来柔弱,骨子里却很坚强。其实,你是个非常优秀的女人。
是,又怎么样?
其实,你可以重新选择。
痴人说梦。那时,我儿子曹西该上小学了。我知道很多问题少年都是家庭造成的,为了孩子,我不能。
从此,宗剑在我心里成了一缕阳光,想起他,会有种温暖的感觉。这种感觉一直持续着,有事儿时我会找他帮忙,包括科室里奖金分配、物料领取。
直到有一天,宗剑打电话,要我去他家里一趟。我虽然不想见到夏柳,但是,我想,既然宗剑邀我,肯定有事儿,我不能太小气了。
到了宗剑家里,我很意外,就他一个人。不过,我也放松了很多,不再担心和夏柳见面的尴尬。
宗剑在家里置办了酒菜,他说,家里就剩下他一个人了,想跟我聊聊。
我心里一热,有些惶然。我喜欢和宗剑相处,但这和男女之间的爱情无关,也和夏柳跟曹北无关。我们之间似乎还有一种难以诉说的情愫,那是一种晦涩而隐痛的东西,它让我们心灵相通。不过,他和我,在他家里,这样相处还是让我感到有些不安。
他打开了一瓶洋酒,说是他的朋友送的。开始,宗剑只是劝酒,并没有说什么。一瓶酒喝得差不多时,他说:我得到一些信息,你们科的刘主任要调走了。你可以争取一下副主任。
我?凭什么?我疑惑地说。
凭你的技术和服务态度。不过,这事儿得院长拍板。
我说:算了。我不想去争什么。我只想平平淡淡地活着。
这不是你的性格。你不去争,是害怕失败。项南,我可以帮你。
你为什么要帮我?夏柳会同意吗?
千万别提她。人家自己有本事,没有她办不到的事儿。
我眼前又晃动者曹北和那个女人的身影。我觉得自己在膨胀,是的,酒精起了作用。我不能再喝了,不然,我会控制不住自己的。
宗剑又倒满一杯,他说:项南,你知道曹北那天晚上是怎么摔伤的吗?
你知道?
我知道。他不是自己摔伤的,是我打的。我还知道,他肯定说是摔伤的。不过不怨曹北,是夏柳约的他。那天,我出差本不该回来,因为事情办得顺利,就提前回来了。我没有把他们摁在床上,他们已经穿好了衣服。可是,安全套还没有扔掉,床上还没来得及收拾。我一拳打在曹北的脸上,把他推出门外,他和自行车一起倒下。
宗剑说:夏柳不承认他们的关系。她说,她让曹北来,是说我弟弟承包工程的事儿。她想让曹北牵线认识一下他们的局长。我弟弟确实找过夏柳,当时我不在家。那个工程也确实是曹北牵的线。
那时,曹北已经是局办公室主任了。他肯定能为她提供不少有用的信息,而且,还可以帮他们运作。我知道,夏柳是个漂亮的女人,也是个有心计的女人。她真的什么事儿都能办成。我有些醉了,没头没脑地问宗剑:你难道就不能满足她吗?
她是个永不满足的女人。
这就是你要和我聊的?
项南,其实我不想伤害你,我实在撑不住了。我们做邻居时,夏柳和曹北就……
别说了。我眼前又出现了那年“十一”我回家时的情景。曹北那次喝多了就跟我说,夏柳找他有事儿,他们才……是啊,有事儿,有事儿就上床,也太让人恶心了吧。我端起酒杯喝完了酒杯里的酒。宗剑在抽动我心里那根钢针。
我的手开始抖动,我竭力控制想要喷射而出的胃容物。我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说:宗剑,我得走了,我喝多了。
宗剑站起来,抱住了我。他说:项南,我不是报复曹北,也不报复夏柳,我真的喜欢你。你是靠自我奋斗的女人,我喜欢你的清高和骨气。项南,我知道你需要,我抱你上床好吗?
不,我要吐了。我无力地挣扎着。
宗剑把我抱到床上,他解开了我的衣服。我难受得要命,实在控制不住,就喷射而出。我想,我弄脏了他家的地板。待我的胃里空空如也,那种劫后重生的感觉好舒服。我有些冲动,有些神志不清。我躺在宗剑的床上,渴望着事情的发生。
宗剑给我倒了一杯水,搬起我的头让我喝下。那杯水下肚,整个胃里顷刻便有了热辣辣的感觉,那种感觉在刺激着我。
宗剑继续脱我的衣服。我的意识有些模糊,我觉得脱我的衣服的人不是宗剑而是尚浩。我迷迷糊糊地说:尚浩,你不是不喜欢这样吗?你真虚伪。
宗剑已经伏在了我身上,当我说出尚浩时,他停了下来。吃惊地问我:尚浩?尚浩是谁?
我猛然醒了。
我推开宗剑,穿上衣服,摇摇晃晃地走了。我需要性,可是,宗剑不是我想要的男人。我不能让自己后悔。曹北和夏柳,我和宗剑,这不是太可笑了吗?世界不至于小到只剩下我们四个人了吧?
我走到家门口,无论如何也走不动了,眼前一黑,蹲了下来。天已经很晚了,我差不多看不清自己的家门。我吐出了宗剑给我喝的那杯水,觉得轻松了许多。
曹北也回来了,有人把他送回来的。自从他当了办公室主任,几乎天天喝得烂醉,我不知道他是在逃避我,还是在逃避他自己。
他歪歪斜斜地回了家,并没有看到蹲在一旁的我。我没有吭声,我知道他很快就会进入梦乡的。我要等他睡了之后才回家。
回到家,我却清醒得出奇。是的,宗剑找我是说科室副主任事儿的,怎么就成了这样的结局?宗剑,像长在我心里的苔藓,湿乎乎的,透着油绿。他说得对,我不是一个轻易放弃的女人。我会靠自己的能力去争取应该属于我的东西。我不怕失败,不怕!我躺在床上,想着怎么去找院长……
十 曹北
不知从什么时候,曹北的腿有些跛。他说腿有些疼,有时候会软。我让他去医院检查一下,他说没什么大碍。他仍旧是应酬,仍旧是喝酒。那天,他说,他大腿的肌肉有些萎缩,坐骨神经也疼,我怀疑他得了股骨头坏死。
曹北的病越来越厉害,后来几乎不能走路,必须靠拐杖才能行动,自然也不能上班了。我跟他一起去省城一家专科医院,确诊是股骨头坏死,已经是晚期了。我们找到了一个曾经在我们学校任教的老教授,他是这方面的专家,他给曹北开了许多中药。他说:在服药期间,不能喝酒,不能同房,而且相当一段时间阳不能举。以后会慢慢恢复,千万不能着急。
医院里要集资盖房,要一套大一点的房子是我奋斗的目标。我不想失去机会,即使现在不住,将来也可以卖掉,说不定还能赚些钱。我和曹北商量,他说,算了,孩子还要上学,我们没钱,就不要了。可我实在不想放弃,找人借了钱,把预付金交上了。
孩子开学了,去了“素质班”,要收一千二百元的赞助费。曹北说,上普通班算了,普通班免学杂费的。我说:不行,再苦不能苦孩子。我咬牙坚持让他们进“素质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