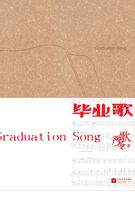柳铁锨遇上这事儿,肯定得找我。他娘的脾气,我比他还清楚。
那年过年的时候,馍匠柳已经死了,倭瓜也娶了媳妇。老太太还活着,他们还没有分家。没有分家是我干娘执意不分,她觉得一家人在一起热热闹闹地好。因为没有分家,一家人的生计重担都落在葫芦和我干娘身上。葫芦没有接手馍匠柳的生意,而是零零星星地干点别的。今儿贩点粮食,明儿贩点香油,顺便贩点钉头、锅碗瓢勺,偶尔还会在柳老歪家的码头上坐船,往返陈州城里贩点洋玩意儿。反正是啥能赚钱就贩啥,比光靠蒸馍多点活便钱。葫芦做点小生意勉勉强强地过日子。那年大年三十,葫芦掂一块“刀头”(猪头下面的头一刀肉,泛指上供用的猪肉)回来,顺手把“刀头”挂在箔篱子上。下来时,大衫子撕了个大口子,他这大衫子实在太破了,缝都没法儿缝。这大过年的,出去拜个年、迎个客,怎么也得有件能出门的衣裳吧。
葫芦沮丧地说:十来年了,俺连一丝子半寸都没添过,眼看都出不去门了。
我干娘从腰里摸出几文钱,说:你去街上洋布铺里扯丈把蓝士林布,俺给你缝件大衫子。
葫芦笑了:说你不着调不亏你,你也不想想,都大年三十了,谁家还不打烊歇业?就是有布,你能缝好了?
你只管去买布吧,俺有办法。
葫芦说:你也是“老和尚娶媳妇——说了当了”。俺不去,花那钱干啥?
我干娘“嘿嘿”一笑说:嗨,要不,你去咱娘屋里,她那儿有半匹蓝棉布,留着送老的。她身体好着呢,赶明儿(以后)咱有了,再给她老人家买好的。你去吧,说不定,你跟倭瓜一个人能做一件呢。
疯了你,娘会愿意?
你就说向她借的,过了年就还她。到时候,她想要棉布,俺给她织;想要洋布,咱给她买蓝士林布;要绫罗绸缎咱也给她弄,反正日子长呢,总会有的。
葫芦揣上那几文钱,去他娘那里拿来了半匹土蓝布。他拿回布扔在我干娘跟前说:俺看你能让俺明儿穿上大衫子。
不信咱输点啥。
输点啥?
就输俺给你的那几文钱吧。
葫芦心想,几文钱已经给了他娘。一则过年老人腰里不能空着,二则一晚上累死她也缝不好,就应下了。明天果真能缝好了,到时候再说。
等到一家人都睡下了,我干娘点上油灯,把柳葫芦的破大衫子找出来,比葫芦画瓢地一剪子一剪子地裁好,缝起来。过了二更天,她就开始困了,拧了一下大腿,又缝了几针。刚缝了几针,眼皮子就打架,眼皮子一打架,手就不当家了。手一不当家,针就咬她的手。手上血在蓝棉布上留下许多黑点点。实在困得慌,她就起身舀了一瓢凉水,拍拍头。这时,倭瓜的媳妇月桂起来解手,看她屋里亮着灯,走过来说:嫂子,你咋不睡觉?
月桂,来,帮俺拉着那个角,缝得快些。你哥跟俺赌几文钱哩,赢了钱,俺给你买油果子吃。一听说吃,月桂也来了劲儿。可是,熬了一个时辰,她也架不住了。
我干娘抬头一看,箔篱子上挂着“刀头”。她“嘿嘿”一笑说:月桂,你想吃肉不想?
一听说吃肉,月桂马上有了精神。她说:肉谁不想吃,要得有啊?
你看箔篱子上挂的是啥?
那不是俺哥割的“刀头”吗?那可不敢吃,天明还要烧香敬神哩。
管不了那么多,咱俩吃了再说,俺在这里缝着,你去熬肉,明儿你啥都不说,该干啥干啥。月桂遵旨去熬肉。我干娘在肉香的诱惑下继续做大衫子。
大年初一,是女人们最享福的一天,女人们可以睡到男人做好饭再起床。男人天不亮就起早开门、做饭、放炮、敬神。
葫芦早早地起来,看到我干娘歪在外屋睡得正香,一件崭新的蓝布大衫子就在她的旁边。他悄悄地拿起来,高高兴兴地穿在身上,除了有点肥大,还能凑合着穿。
他做好饭,去浸“刀头”。上供的“刀头”,只要在滚水里浸一浸就行了,不需要煮熟,上完供撤下来再熬着吃。当他走到挂肉的箔篱子跟前时,揉了揉眼,以为自己的眼睛出了毛病。他使劲儿地挤了挤眼,还是看不见那块“刀头”。他心里生疑也不敢吭声,倭瓜媳妇还没有分家,家里要是少点什么东西除了她还有谁呢?可又没有抓住她,不好乱猜,以免闹得生分。月桂正闹着分家,如果这事儿声张开了,还不是个分家的好因由啊?老爹走时把一家人托付给他,他咋也得把家操持好了,不能有啥事端。
一连几天,葫芦老站在箔篱子底下发愣。他心里憋得慌,也不敢跟我干娘说。他知道我干娘没心眼儿,有啥说啥。不确定的事儿,说出去了就不好收场。过“破五”(初五)了,家里总得动点荤腥吧?不知道葫芦从哪里又割了一块肉。吃完饭,葫芦又站在箔篱子下发呆,他真希望一眨眼,那“刀头”又回来了。他把眼挤得生疼,可那里还是空荡荡的。
我干娘到底憋不住了。她说,你咋不问问那“刀头”哪儿去了?葫芦说:算了,别声张了。我干娘“嘿嘿”一笑说:俺吃了。
你吃了?你一个人能吃完几斤肉?还恁肥。俺不信。
不信,你再割一块,俺吃给你看。
葫芦信了,他知道我干娘会干这事儿。他嗔怪道:你也留点啊,一家子人就恁些肉。
留点?留点,你蓝布大衫就穿不上了。没有那肉顶着,谁能一夜给你做件大衫子。你输俺的几文钱哩?
割肉了。
割肉了?我干娘掰着指头一算,她吃的肉,远远超过那几文,不吃亏,就得意地“嘿嘿”笑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