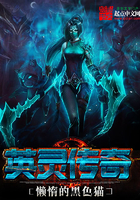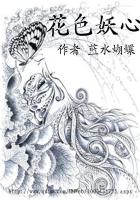“这会儿你怎么又把眼睛瞪这么大?”玛瑞拉问。安妮刚从邮局跑回来。“难道你又找到个知音?”
安妮周身洋溢着兴奋,眼睛亮闪闪的,脸上容光焕发。她像一阵风似的一路蹦蹦跳跳,穿过八月傍晚暖洋洋的阳光和懒洋洋的阴影。
“没有,玛瑞拉。嗨,你猜怎么着?我被邀请明天下午去牧师家喝茶!阿伦太太在邮局给我留了封信,你看看,玛瑞拉。‘安妮·谢利小姐,绿山墙。’这是第一次有人叫我‘小姐’,让我激动得发狂!我要把它跟我最心爱的宝贝放在一起,永远珍藏起来。”
“阿伦太太跟我说,她打算请主日学校她班里的学生轮流去喝茶。”玛瑞拉说。对这件了不得的大事,她倒是非常冷静。“你用不着激动成这样,要学会冷静地处理事情,孩子。”
对安妮来说,冷静地处理事情就意味着改变她的天性。像她这种关注“灵魂、火焰、露珠”的人,生命中的欢欣和痛苦要比常人浓烈三倍不止。玛瑞拉觉察到这一点儿,隐隐有些担心。她意识到,对这个冲动的心灵来说,人生的坎坷有可能是难以承受之重,但她却不明白,安妮感受欢乐的能力同样强大,足以弥补这一切。因此,玛瑞拉认为自己的职责是把安妮培养成性情平和的人,这就像是要把一束跳跃的阳光融入一条浅浅的溪流,既不可能,也同安妮本人格格不入。玛瑞拉也颇为遗憾地承认,她的进展不大。某些殷切的希望或计划一旦落空,安妮会跌入“痛苦的深渊”,要是实现了,安妮又会欣喜若狂。玛瑞拉本想把这个流浪儿塑造成理想中那种娴静端庄的模范姑娘,现在基本上已经绝望了。而且,她不能相信的是,自己其实更喜欢真实的安妮。
那天晚上安妮上床睡觉时愁眉苦脸、一声不吭,因为马修说东北风刮起来了,恐怕明天会下雨。房子四周的杨树叶沙沙作响,听起来多像是滴答滴答的雨点啊,真让她焦虑不安。从海湾那儿远远传来沉闷的海浪声,听起来就像是一场暴风雨的前奏,这对一个一心盼望好天气的小姑娘来说,无异于一场灾难。而平时她总是愉快地倾听,很喜欢那奇异响亮、久久回荡的韵律。安妮觉得黎明永远都不会来临了。
然而,凡事都有结束的时候,去牧师家喝茶前的漫漫长夜终于过去了。虽然马修预言会下雨,但这天早晨的天气却很晴朗,安妮高兴得飘了起来。
“哦,玛瑞拉,今天我是满怀深情啊,我爱身边的每一个人。”她边洗早餐盘子边说,“你不知道我有多开心!这种感觉要能长久就太棒了,是不是?如果每天都能被邀去喝茶,我相信我会成为一个模范少年的。但是,哎呀,玛瑞拉,这也是一件隆重的要事,我好担心哪,要是我举止不够得体怎么办?你知道我以前从没在牧师家喝过茶,虽然自从来到这里我就一直在学习《家庭先驱报》的‘礼仪’专栏,但我可不能肯定自己已经了解了所有的礼节规矩。我担心会犯傻,或者丢三落四的。要是特别喜欢一样食物,再吃第二份算不算失礼呢?”
“安妮,你的毛病就是过多地考虑自己。你应该考虑考虑阿伦太太,想想什么对她最好、最能让她高兴。”玛瑞拉平生第一次提出这么简明扼要的建议,安妮马上意识到这是个好建议。
“你说得对,玛瑞拉。我要试着完全不考虑自己。”
薄暮时分,辽阔的天空悬挂着一条条金黄色和玫红色的云彩,分外壮丽。安妮满心欢喜地踏着暮色归来,坐在厨房门边厚厚的红砂岩大石板上,疲惫地把长着卷发的脑袋靠在玛瑞拉穿着条纹棉布的膝盖上,幸福地向她讲述做客的过程。显然,安妮圆满完成了她的拜访,没有犯任何“礼节”性错误。
一阵冷风从西边冷杉密布的山丘边吹过来,掠过收获季节的广阔田野,穿过杨树林呼啸而去。一颗明亮的星星挂在果园上空,萤火虫在恋人小道上飞来飞去,在蕨草和沙沙作响的树枝间进进出出。安妮一边说话,一边欣赏着这景色,不知怎么,只觉得这风、星星和萤火虫合在一起,变得说不出来的甜美可爱。
“哦,玛瑞拉,我度过了一段最销魂的时光。我觉得没有白活,哪怕以后再没人邀我去牧师家喝茶,我也一直都会这么觉得。我到的时候阿伦太太在门口迎接,她穿着最可爱的浅粉色中袖薄纱裙,上面有好多褶边呢。她看上去真像个天使啊。我真的认为长大了我会乐意嫁给一个牧师的,玛瑞拉。牧师可能不介意我的红头发,因为他不会考虑这类世俗的东西。不过,牧师的妻子当然要天性善良啦,而我绝对不是,所以,光做打算是毫无用处的。你知道,有人天性善良,有人不是。我就不是。林德太太说我身上充满了原罪。不管有多努力,我永远也不会像天性善良的人那么优秀。我想,这差不多跟学几何一样难。不过,这么艰苦的努力应该也有点儿价值吧,你觉得呢?阿伦太太就是一个天性善良的人。我热爱她。你知道,像马修和阿伦太太这样的人,爱上他们毫不费力。还有一些人,比如林德太太,非得很努力才会爱上。你也知道应该爱他们,因为他们懂得多,还是教堂的积极分子,但得时时提醒自己这些,否则就会忘得一干二净。还有一个小女孩也在牧师家喝茶,叫洛蕾塔·布拉德利,从白沙镇的主日学校来的。她很好,算不上是知音,你知道,但也挺不错。茶点很讲究,我觉得自己严格遵守了所有礼节。吃过茶点,阿伦太太就弹琴唱歌,她还让我和洛蕾塔也唱呢。阿伦太太说我的嗓音很好,还说以后我一定要参加主日学校的唱诗班。你不知道,这件事光是想想就能让我多么激动。我一直渴望跟戴安娜一样参加主日学校的唱诗班,不过那时我担心自己永远都没有这种荣幸。洛蕾塔得早点儿回家,因为今晚白沙旅馆有一场大型音乐会,她姐姐要登台朗诵。洛蕾塔说,为了资助夏洛特敦的医院,旅馆里的美国人每隔两个星期就办一次音乐会。他们邀请了许多白沙镇的人登台朗诵。洛蕾塔说她期望自己有一天也能受到邀请。我只剩仰慕她的份儿了。她走了之后,阿伦太太和我推心置腹地聊天,我把所有的事一股脑儿都告诉她了——托马斯太太和她的双胞胎们,还有凯蒂·莫里斯和维奥莱塔,还有我来绿山墙的经过以及学几何时的困难。你能相信吗,玛瑞拉?阿伦太太告诉我她学起几何来也笨得很。你不知道这给了我多大的鼓舞啊。就在我要告辞的时候,林德太太来了,你猜怎么着,玛瑞拉?理事会请了一位新老师,是位女士,叫穆丽尔·史黛西小姐。这个名字真浪漫,不是吗?林德太太说,艾文利以前从没请过女老师,她认为这个改变很危险。不过,我觉得有个女老师挺好的。离开学还有两个星期呢,我真不知道该怎么熬过去,我迫不及待想见到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