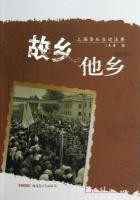单从人均纯收入这个指标来看,与大红柳峡搬迁点同步达到小康标准的新生村已有五六个。火石泉、西戈壁、疙瘩井等几个搬迁点人均纯收入均在2000元以上。到1996年底,全地区有组织、有计划地迁移贫困农牧民1614户,8878人,开荒3.2万亩,见效2万亩,80%已经脱贫致富,人均收入在千元以上,冒尖户人均收入在5000元以上。
对这些搬迁下来的农牧民未来的生活影响最大的并非只是地理环境的改变,实际上新的交往环境,新的生产方式才真正算是“革命性”的变化。交往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在一定程度上,生产的进步正是扩大了交往的结果。搬迁牧民在以血缘、族缘为纽带的交往之外增加了生产和信息交往的分量和频率,旧有的心理围墙崩溃了,这些农牧民的生活、生产观念、情感、思维正潜移默化地朝着新的模式变迁,并由此正在缔造新型的民族关系。
站在林带环绕的葡萄园里,萨尔乔克乡牙吾龙搬迁点村长恰德提汗,这个从刚学会走路就和畜群厮混的牧人指着不远处的陶家宫乡牙吾龙村对记者说:“我有很多汉族朋友,我们从山北过来,棉花、玉米、葡萄都不会种,是汉族朋友教我们种地的技术,我现在快和一个老农民一样了。”由山区到平原,是农牧民内部分化的过程,是生产手段更新的过程,是产业模式转换的过程,与它们并行的还有一个看不见却能感受到的对市场经济的心理适应过程。
从哈密市大泉湾乡东端到火石泉农场,原国道312线70公里长的道路两侧,随处可见新开垦的土地。行序整齐的新民居,大小搬迁点有10多个,在它们当中,巴里坤农牧商服务公司是一个异彩独放的景点,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在市场经济中如鱼得水的新农村。1992年,34岁的陈培社带着大河乡商户村52户农民迁居哈密市火石泉,开地2500亩。刚来的时候,有80%的家庭欠账。干过包工头的陈培社自己垫支一部分资金,又从银行贷款为每户购置了一辆小四轮拖拉机,组成一支运输兼劳务输出的“农民军”。每年3月底,男人们驾车离家,四处揽活,留在家里的女人和老人则开荒种田搞养殖。地分家,但管理不分家,他们借鉴兵团模式,搞大条田统一种植。2500亩地细划分为葡萄园、果园、棉田、麦地4大块。按最佳效益设计各自的规模水平。5年来,他们靠建筑业、运输业、种植的同时,先后建起了养猪场、奶牛场。5年工夫,在戈壁滩上建起了一个接近小康标准的新村落。到1996年底,集体固定资产160多万元,人均纯收入2800多元,80%的人家住上了使用面积169平方米的砖房。
记者问陈培社,为什么叫农牧商服务公司?陈培社说:农村在解决温饱以后,要继续发展必须增强集体的功能,不然的话,单个家庭不仅很难承受大的风险,还会失去在生产以外的利润,发展速度就会慢下来,把大家拢在一起组成公司,统一经营管理,农牧商综合发展,就能保证实现共同的奋斗目标。可以说,巴里坤农牧商服务公司为搬迁点组织化问题破了题,它是一个农民自己的合作经济组织,有三重角色,既充任市场及技术经纪人,又是集体资产的经营者,还是社区事务的管理者。家庭与组织的分离在这个仍然带有传统气息的新村落里发生了,家庭开始纯化为消费生活的单位,经营功能逐渐弱化,经营体以组织的形式走出了家庭。公司作为一个经营组织,不同于村落的正是在于:目的是限定的、明确的,为有效率地实现共同的目的而把成员的活动合理地组织起来,并进行必要的分工。而村落在目的上是模糊的,基本不存在什么分工。
走共同富裕之路,组织的问题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
五:从生路到富路
如果说10年前的搬迁开发还只是在生存危机的威逼下冲撞出的一条生路的话,那么,现在再看搬迁开发,则是一条布满了理性标识的富路。首先,它从改变生存条件、提高家庭分散生产水平起步,又从形成有区域特色的优势产业的角度入手引导群体经营,跳出了发展传统农业的束缚,在大农业上迈出了坚定的步伐。
大农业是新疆的优势产业。哈密有荒地500万亩,现在只开了100万亩,开发潜力足以让人神往,可谓“潜龙在渊,蓄势待发”。1996年10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张文岳来哈密考察时指出:哈密水土条件十分优越,大规模的水土开发将为哈密经济全面发展带来强劲的动力。从淖毛湖、牙吾龙、黄土场三大扶贫搬迁开发区的建设开始,哈密拉开了大规模农业开发的序幕。并且把“农牧结合、种养互促,形成区域特色”的产业思维引入了搬迁开发,在致力于转移贫困山区劳动力,解决贫困家庭温饱来源的同时,也正在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畜牧业在扶贫开发中是一个特殊的兴奋点。
1996年9月,哈密召开了近20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畜牧业专题会议。地委书记黄昌元在会上强调指出:如果不搞农牧结合,到20世纪末,哈密的多数农牧民绝不可能致富奔小康。会议提出:种植业要由粮经二元结构迅速向三元结构调整,畜牧业要草原、农区、城郊并举。两县一市必须坚定不移地走牧业强县、牧业富民的路子。
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在搬迁开发中,牢牢把住农牧结合,实际上是在资源、能力、利益之间建立了很好的平衡杠杆,它有优越的资源背景,面对的是巨大的市场空间,而且适应面广,家家都能干,户户可受益,这就意味着牵住了同步解决温饱问题和发展问题的牛鼻子。
在白石头牧场所属的西戈壁农场,张场长告诉记者:白石头牧场这个国有牧场计划采用公有畜作价归户的办法实施牧改。这已经被前山盐池牧场证明是成功的牧改方案,谁知牧民坚决不要。他们说:宁可将羊全部卖了,也要来开地,有地就会有羊,没地要羊有什么用?地委书记黄昌元了解到这一情况后,高兴地说:“白石头牧民的观念真正转变了。”从游牧到定居到搬迁开发,劳动生产率逐步提高,回报更趋稳定、风险递次降低。牧民从空间距离乃至心理距离上离“市场”都更近了。
搬迁开发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山区经济获得新的生机的过程,山区由于部分人口外迁正在减轻人均有效资源稀缺的压力。据有关部门调查,移民人数占原村人数1/3以上的村,每搬迁一户可以使留居山区的一户脱贫。当然,山区经济的最终出路取决于能否把人的经济活动和山区自然生态环境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重新设计。从山区与平原同获生机来看,搬迁开发是区域内农业资源优化配置的过程,是山区人力资源与平原区自然资源有机结合产生更高生产率的过程。
不同的扶贫方式会有不同的结果,10年来,哈密搬迁开发的实践留给未来的启示或许是:如果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吃透本地最大的区情,着眼于发挥比较优势,解决自己的特殊性问题,并且能够排除各种干扰,坚定不移地追求专业户既定目标,则必能创造辉煌的景观。
“行百里路半九十”,哈密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虽然在减少,但解决贫困问题的难度却越来越大。从时间表来看,1985年到1996年,哈密年均解决2000人的温饱问题,要实现2000年以前解决4267户22041人的温饱问题的目标,今后必须以每年6100人的速度进展,而且前10年的搬迁开发循照的是“先易后难、先强后弱”的原则,很少触及贫困程度最重的下线人口,尤其是人均收入在300元以下的8000多名特困人口,难度之大可想而知。最难不过基础建设资金问题,仅把必须搬迁的2800多户贫困户搬下来,就需资金上亿元,不仅这些贫困农牧民很难达到,占搬迁费用15%左右的自筹住房标准,地县市财政面对的也是一个望而生畏的数字。
1997年春天到来的时候,哈密地委、行署再次承诺:绝不让贫困跨世纪!
今天是明天的种子,明天是今天的果实。为了明天,我们需要今天再加把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