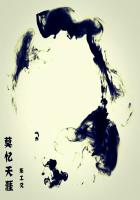回到墨菊山庄后,我对着镜子感觉自己又消瘦了不少,我估计八层是被灿桑的婚礼给折腾的。在吃午饭时,我颇有兴致地向奇少爷和吴婶讲述在灿桑婚礼上的种种趣事,特别是讲到唐泽秀那段趣事时,心里抑制不住的亢奋,大抒特抒。也不知道为什么,尽管我讲得很起劲,但就是提不起奇少爷任何的兴趣。我看着他那副冷冰冰的样子,心里不禁有些失望。
第二天,华太太突然回到墨菊山庄,给我们来了个措手不及。从她走进大门的第一步开始,我就感觉到她今天的步伐有些沉重,不像往常那样势气凌人,不可一世。她的眼睛里锁着一丝惆怅,好象满腹心事。
由于我害怕见到华太太那种挑剔的眼神,所以她每次来,我都尽量离她远一点,免得她看我不顺眼,惹一身麻烦。今天也不例外,我一个有躲在厨房里,漫无目的地东擦西蹭,表面上看我是在忙,其实我是为了逃避华太太那一连串的责难装出来的。巧的是,华太太今天好象忘了我这个人的存在似的,直到她走时,也没有传唤我过去向她汇报最近的工作情况。
她走后,我像只刚从案板上解救下来的鸭子,松了一口气地从厨房里跑出来。吴婶一个人站在大厅里,满目忧伤地左叹息一声,右叹息一声的自言自语。我看她那副魂不守舍的样子,心生好奇,便上前问她出了什么事,弄得如此紧张兮兮的。
吴婶神伤地望了我一眼,挑了一下嘴角说:“还不是因为他。”她说着,手指了指楼上。
我顺着他的手指向上望了望,有些困惑。
“他——又怎么了?”我小声问,心里有些忐忑。
“下个星期是他爸爸的生日,他妈今天来是想劝服他这次能回去为他爸爸贺60大寿。”
“什么,少爷他有爸爸,我来这里这么长时间,怎么从来没听他提起过?”我一脸愕然,大感意外。
“那你有问过他吗?”吴婶瞪大眼睛问。
我摇摇头,说:“但我从来没见过他爸爸来看望过他。”
“少爷那副凶脾气,他爸爸哪敢来。”吴婶说着,叹了一口气。
“为什么?”我听她这样说,更不解了。
“还不是那场车祸。”吴婶说得咬牙切齿的,好象那场车祸历历在目。
“车祸?他爸爸跟那场车祸有什么必然联系吗?”我向吴婶刨根问底。
“三年前,少爷出事的那辆车,其实是李先生的。”吴婶深吸了一口气,咬了咬嘴唇,回忆说:“还记得那时,他出这事以后,整天都是寻死觅活的。后来闹得日子久了,等他渐渐平息下来的时候,他就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那辆害人不浅的车上。我猜想,也就从那时起,他的心理就已经开始发生了扭曲。找不到人撒气,索性就把心中的那股恨全撒在他爸的身上。我看他八层是认为如果那时他开的不是他爸的那辆车,今天坐轮椅受毁容之苦的人就应该是他爸而不是他了。”她说着,鄙夷地哼了一声。
“我不相信,少爷他绝对不是那种人。”我又坚定又激动地说。
吴婶望着我那副坚定的神情有些惊讶,她拍了拍我的肩,一脸苦笑地对我说了声“但愿如此”,说完后,便和我擦肩而过,去厨房做饭去了。
正在这时,楼上突然传来一阵剌耳且又熟悉的声响,我很快意识到奇少爷又在房间里闹脾气。当我赶到楼上时,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屋内又被他弄得乱七八糟,带血的茶杯碎片散落一地。“血——”我心里猛然一惊,把目光转向了奇少爷。天啊,他的手上沾满了血,而且血还不断地从他所戴的露指手套里渗出来。我立在一旁吓得浑身发抖,手舞足蹈地不知所措,脑子里一片空白。他看起来到好象没有丝豪感觉,不知疼痛似的,仍静静地坐在窗台前痴痴对着窗外的满园菊花发呆。
没过多久,吴婶也赶了过来,她看到眼前的景象,自然不用说,吓得魂飞魄散。她连忙冲上前去,心疼地欲拽住奇少爷的手,检查他手上的伤是否伤得严重。但没想到,就在这时,奇少爷朝她大吼一声,顺手将他一把推开,吴婶顿时向后连退几步,由于重心不稳,狠狠摔倒在地。
我看到吴婶被他推倒在地,一时间,心中的怒火倾刻爆发。我气得忍不住朝奇少爷大嚷:“你有几个臭钱了不起呀,吴婶虽然是你们家请来的佣人,但她好歹也是大你几十岁的人,也算是你的长辈,难道你就连最基本的尊重都不懂吗?”说完,我气愤地转过身,冲到吴婶面前,将她扶起,把她掺扶回了房。
吴婶这一摔,还真摔得不轻,她躺在床上痛苦呻吟了老半天,直喊腰痛。我看她那样,真的很是着急,深怕她有个什么散失,毕竟她也是一把60岁的人。我想帮她在腰部擦一些药油,按摩一下,但被她拒绝了。她拽住我欲给她按摩的手,满面痛楚地对我说:“你快……快去看看少爷,他的手还在流血呢?”说着,她拼命地猛推我去隔壁。最终我拗不过她,只好怀着忐忑的心情,出了她的房间。
待我回到奇少爷的房间时,他仍旧冷冰冰地坐在那里,手上还在淌血。我很想冲上前去为他包扎伤口,但我知道,我上前去的结果肯定会和吴婶一样,遭到他的蛮横拒绝。
我站在门口,低着头向里走了几步,习惯性地向他赔礼道歉:“对不起,我刚才不应该对你说那些冒犯你的话,但不管怎样,请你先让我为你包扎伤口,可以吗?”
他轻蔑地冷笑一声,说:“你认为你刚才所说的都是错的了。”
“不——”我的语气很坚决,“我只是说那些话不应该对你说,并不代表我认为那些话说的都是错的。”
“在你心里我就是一个连最起码的人性道德都没有的混蛋,是吗?”他话说得异常平静,好象不以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