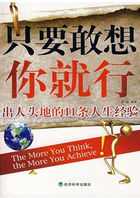“原文”
有弱态,有狂态,有疏懒态,有周旋态①。飞鸟依人,情致婉转,此弱态也;不衫不履,旁若无人,此狂态也;坐止自如②,问答随意,此疏懒态也。饰其中机③,不苟言笑,察言观色,趋吉避凶,则周旋态也。皆根其情,不由矫枉④。弱而不媚,狂而不哗,疏懒而真诚,周旋而健举,皆能成器;反之,败类也。大概亦得二三矣。
①周旋态:指智者工于交际和善于折中的情态。
②坐止自如:即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③中机:即心机。
④皆根其情,不由矫枉:根,根源于,来自于。情,这里指内心的真情。不由,不任人随意处置。枉,弯曲。矫枉,即故意做作。
常见的情态有以下四种:委婉柔弱的弱态,狂放不羁的狂态,怠慢懒散的疏懒态,交际圆滑周到的周旋态。如小鸟依依,情致婉转,娇柔亲切,这就是弱态;衣着不整,不修边幅,恃才傲物,目空一切,旁若无人,这就是狂态;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不分场合,不论忌宜,这就是疏懒态;把心机深深地掩藏起来,处处察言观色,事事趋吉避凶,与人接触圆滑周到,这就是周旋态。这些情态,都来自于内心的真情实性,不由人任意虚饰造作。委婉柔弱而不曲意谄媚,狂放不羁而不喧哗取闹,怠慢懒散却坦诚纯真,交际圆润却强干豪雄,日后都能成为有用之材;反之,既委婉柔弱又曲意谄媚,狂放不羁而又喧哗取闹,怠慢懒散却不坦诚纯真,交际圆滑却不强干豪雄,日后都会沦为无用的废物。情态变化不定,难于准确把握,不过只要看到其大致情形,日后谁会成为有用之材,谁会沦为无用的废物,也能看出个二三成。
“智慧解读”
“弱态”之人,性情温柔和善,平易近人,往往又爱多愁善感,“细数窗前雨滴”,缺乏刚阳果敢之气,有优柔寡断之嫌。即所谓的“多才惹得多愁,多情便有多忧,不重不轻正候,甘心消受,谁叫你会风流”之人。这类人的长处在于内心活动敏锐,感受深刻,若从事文学艺术事业或宗教慈善事业,往往有可能做出一定成就。这种人心事细密,做事周全,易中人放心,但不太适合做开创性的工作。
“狂态”之人,大多不满现实,爱愤世嫉俗,对社会弊病总喜欢痛斥其不足,个人品性往往是耿介高朴,自成一格,正因如此,难与其他人打成一片,团结合作精神不是很好。但这类人有钻劲,又聪明,肯发奋,持之以恒,终能有过人的成就。历史上如郑板桥等人,就属这一类。但过于狂傲,失却分寸,又可能给自己带来不少的麻烦。
具“疏懒态”者,大多有才可恃,对世俗公认的行为准则和伦理规范不以为然,满不在乎,由此引发而为怠慢懒散,倨傲不恭。这种人,倘若心性坦诚而纯真,则不仅可以呼朋引伴,广交天下名士,而且在学术研究或诗歌创作上也会有所成就。疏懒往往只是他们人格的一个侧面,如果某种事业或某项工作确实吸引了他们,他们会全身心地投入其中,进而孜孜不倦,勤勉无比。虽然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会疏懒不堪,但有一点则是无疑的,即断不能做官。上官一般不会选择他们作为下官,而他们既不善与一同僚相处,也不善于接人待物,更不会奉承巴结上官。
他们这么做多半是因为不愿在这些人际关系方面去浪费精力和时间,因此他们宁愿挂冠弃印而去。如陶渊明,做了40多天小官,毅然辞职而去,宁愿去种田,“带月荷锄归”,种种地,写写诗,过“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神仙日子。尽管生活很艰苦,他也自得其乐,绝不为五斗米折腰。
具“周旋态”者,智慧极高而心机机警,待人则能应付自如,接物则能游刃有余,是交际应酬的高手和行家。这种人是天生的外交家,做国家的外交官或大家豪门的外掌柜,任大公司或大企业的公关先生或公关小姐,都能愉快胜任。其办事能力也很强,往往能独当一面。假若周旋中别有一种强悍豪雄之气,那么在外交场合,必能折冲樽俎,建劝立业。古人所谓“会盟之际,一言兴邦;使于四方,不辱廷命”,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如历史上盛传的蔺相如完璧归赵、唐雎不辱使命等故事,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
然而,这中间仍需细细分辨,事物往往不会简单到四种类型就能概括一切,人之性态也如此:
“弱态”若带“媚”,则变为奉迎谄媚之流,摇尾乞怜之辈,这是一种贱相。
“狂态”若带“哗”,则为喧嚷跳叫、无理取闹之流,暴戾粗野、卑俗下流之辈,这是一种妄相。
“疏懒态”若无“真诚”,则会一味狂妄自大,此实为招祸致灾之阶,殊不足龋这是一种傲相。
“周旋态”若无“健举”,会由城府极深,迹近狡诈、阴险和歹毒,这是一种险相。对这种人,倒是应该时时警惕,处处提防,不能因一人之险进而乱了自己的阵脚,甚至败坏了自己的事业。
在是非之间,刘劭在《人物志》中明确提出一个“七似之流”的概念,就是说社会上有一类人,表面看来搏学多识,能力很强,但究竟属不属实,就需要仔细分辨了。刘劭把这类人分为七种,称为“七似”,他们都是模棱两可的人:
一似:有人口齿伶俐,滔滔不绝,很能制造气氛,哗众取宠,表面看来似乎能言善辩,但实际观察其知识,乃一肚子草包,根本就没有什么东西。目前社会有很多这一类的演说家,我们要小心上他们的当。
二似:肚里有些才华,但明明缺少高等教育,却对政治、外交、法律、军事等各种问题都讲得头头是道。表面上看来似乎博学多能,其实样样通就意味着样样都不精。这类人以御用学者居多,这是似若博学者。
三似:有人水平低,根本听不懂对方的言论,却故意用点头等动作迎合对方,装出听懂的样子。在有权有势的人身旁常有这一类拍马屁的人,这是似若赞解者。
四似:有人学问太差,遇到问题不敢表明自己的态度,于是等别人全都发表完之后,再跟随赞同附和,用他人的某些言语胡讲一通。许多不学无术的学者即属此类,这是似能只断者。
五似:有人无能力回答问题,遇到别人质问之时,故意假装得精妙高深的样子,避而不答,其实是一窍不通。有些官员遇到民众质问时,常认为不屑一答,加以回避,其实不懂,故意顾左右而言即属此类。这是似若有余实不知者。
六似:有人一听人的言论就感到非常佩服,其实似懂非懂,就是不懂。是似悦而不择者。
七似:有一种人物,道理上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可仍然牵强附会,不肯服输,一味地强词夺理。此种理不直气却壮的人,在讨论场上处处可见。这是似理不可屈者。
前面所讲的情态,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作为用人者,应迎其长,避其短。在察看之时,则应从细小处入手,方可明断其是非真假,正大者可成器材,偏狭者会成败类,应注意区分。
“智慧应用”
东郭垂观态识人
人一生要经历漫长的路程,大致说来有四个时期:幼年时期、青年时期、壮年时期、老年时期。在各个阶段,人的生理、心理发育和变化都有一定差异,有些方面甚至非常显著。表现在人的肤色上则有明暗不同的各种变化。这就如统一株树,初生之时,色薄气雅,以稚气为主;生长之时,色明气勃;到茂盛之时,色丰而艳;及其老时,色朴而实。人与草木俱为天地之物,而人更钟天地之灵气,少年之时,色纯而雅;青年之时,色光而洁;壮年之时,色丰而盛;老年之时,色朴而实,这就是人一生几个阶段气色变化的大致规律。人的一生不可能有恒定不变的气色,以此为准绳,就能辨证地看待人气色的不同变化,以“少淡、长明、壮艳、老素”为参照,可免于陷入机械论的错误中去。
一般来讲,仁善厚道之人,有温和柔顺之色;勇敢顽强之人,有激奋刚毅之色;睿智慧哲之人,有明朗豁达之色。
齐桓公上朝与管仲商讨伐卫的事,退朝后回后宫。卫姬一望见国君,立刻走下堂一再跪拜,替卫君请罪。桓公问她什么缘故,她说:“妾看见君王进来时,步伐高迈,神气豪强,有讨伐他国的心志。看见妾后,脸色改变,一定是要讨伐卫国。”
第二天,桓公上朝,谦让地引进管仲。管仲说:“君王取消伐卫的计划了吗?”桓公说:“仲公怎么知道的?”管仲说:“君王上朝时,态度谦让,语气缓慢,看见微臣时面露惭愧,微臣因此知道。”
齐桓公与管仲商讨伐莒,计划尚未发布却已举国皆知。桓公觉得奇怪,就问管仲。管仲说:“国内必定有圣人。”桓公叹息说:“白天来王宫的役夫中,有位拿着木杵而向上看的,想必就是此人。”于是命令役夫再回来做工,而且不可找人顶替。
不久,东郭垂到来。管仲说:“是你说我国要伐莒的吗?”他回答:“是的。”管仲说:“我不曾说要伐莒,你为什么说我国要伐莒呢?”他回答:“君子善于策谋。小人善于臆测,所以小民私自猜测。”管仲说,“我不曾说要伐莒,你从哪里猜测的?”
他回答:“小民听说君子有三种脸色:悠然喜乐,是享受音乐的脸色;忧愁清静,是有丧事的脸色;生气充沛,是将用兵的脸色。前些日子臣下望见君王站在台上,生气充沛,这就是将用兵的脸色。君王叹息时所说的都与莒有关。君王所指的也是莒国的方位。小民猜测,尚未归顺的小诸侯唯有莒国,所以说这种话。”
康熙:先观人心,再看才学
德才兼备是所有用人者倾心追求的人才,但能达到这一标准的人毕竟廖廖,只能两者相权取其重,康熙是“德重于才”论的代表。他强调“德胜于才,始为可贵。”立心制行,人之根本。作为一代封建帝王,康熙始终把德才兼备作为选人的唯一标准,并坚持如一。康熙七年(1668年),他对吏部说:“国家政务必委任贤能……今在京各部院满汉官员俱论资俸升转,虽系见行之例,但才能出众者常以较量资俸超擢无期,此后迂有昆要员缺,着不论资俸将才能之员选择补用。”意思就是说,国家政事必须委托给德才兼备的人。现在京城各部院满汉官员的升迁都是论资排辈,虽然这些都是多年的惯例,但才能出众的人常常因为资历太浅升迁无望,此后如果有重要的职位空缺应该不论资历,选拔有才能的人来担任。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四月,康熙帝对吏部说:“国家用人凡才优者固足任事,然秉资诚厚者亦于佐理有裨。比部院中亦有一两才优之人,所以未即升擢者,因其有才又能循分,故欠任之。朕听政有年,见人或自恃有才辄专恣行事者,思之可畏。朕意必才德兼优为佳,若止才忧于德终无补于治理耳。”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国家用人只要是有才能的就可以任用,但忠厚老实的人对治理国家也有帮助。每个部院中都有一两个有才能的人,他们之所以未能得到升迁,是因为他们有才能而不能安分守己,因此很长时间担任某个职务。有才能的人总是恃才傲物,一意孤行,想起来很可怕。我认为德才兼备是最好的,如果才优于德,对于治事国家是没有什么帮助的。在这里,康熙帝还是强调选拔人才要把德放在首要位置,才与德比较,德则更加重要。因此,必须坚持德才兼备的任人标准选用人才。早在亲政的最初几年,康熙多次与担任讲官的大学士讨论用人之道。十一年八月,十九岁的他曾让自己的侍讲官、大学士熊赐履谈论对用人方面的看法。熊赐履是这样说的:凡取人以品行为本,至于才气,各有不同,难以概律。随人才器使,但用其长,不求其备。天地无弃物,圣贤无弃人。
熊赐履的话大意也即是说,德行的标准是统一的,而才气则各有各的要求,难以一概而论。对人的使用要根据各自的特长,择其优势而用,不可求全。全人是没有的,天和地之间一切物体都能包容,圣贤看人也是各有各的用处。
康熙十分同意大学士熊赐履的这一观点。事过不久,他又对人谈起这个问题,又让熊赐履讲讲什么叫做“有治人无法治”。熊赐履说道:从来就没有无毛病的万能之法。得其人,变化其心,自足以治;不得其人,虽典章官礼,但亦难尽善。皇上唯留意用人,人材得,则政事理,是不易之道。
大意是说,什么法都不是尽善尽美的。找到了合适的人,让其按法而办,就可以达到目的;人找错了,法规策划得再好,也难以完成。皇上只要留心,得到了合适的人,政治上的事是无须发愁的。事实就是如此。熊赐履又说:人之能否,俱未可以外貌品定。意即看人能力的大小不可仅从其外貌上去判断。
康熙也开诚布公地谈了自己的看法,说自己衡量人才的标准是:先观人心术,其次再看其才学。一个人如果心术不正,便有才学又有何用。他认为虽然知人很难,用人也不易,但是致治之道,全在于此。如果不尽心,人才是不可得的。熊赐履见皇上的观点与他基本一致,抓住了用人之道的关键,十分高兴地夸赞说:才有大小,学有深浅。朝廷因才器使,难拘一格。至立心制行,人之根本。圣贤衡品,帝王论才,必首严其辨。圣谕及此,诚知人之要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