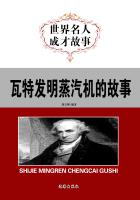魏源没有当过大官,不可能有影响国家大政的经世举措,来实现他的“君明臣贤、国强民富”的经世理想。他任州、县官时,保护河堤、保境安民、改善牢狱居住条件,“改建书院,储卷籍,置义冢,设义学,整饬育婴堂、恤嫠会,传种牛痘,兴水利,培地脉”等等,自然都是经世“善政”。这些“善政”,对于整个朝廷来说,对于一个时代来说,都是枝枝节节的,不能触动社会制度的本根,却可以促进办实事的社会风气的形成。
魏源经世,主要靠着书、写文章,来影响当代和后代的经世者。这是他的最大的经世贡献,本书在以后的各章里将详细论述。这里单谈他对水利的关心与努力。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在以农业生产为主的旧中国,有无水灾、旱灾,不但直接影响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农民的生命和生活,而且影响国家的税收、财政,甚至国家的兴衰。这是历代包括明君贤臣在内的许多人的共识。连康熙帝在他的《圣训》中也指出:“黄河溃决,关系运道民生。”“水利一兴,田苗不伤旱涝,岁必有秋,其利无穷!”作为有志经世的士人,魏源焉能不从史书中、从现实中敏感到治水的重要意义?正如他的朋友包世臣所说:“默深网罗近世有心世道之文至夥,而河事尤所注意。”嘉庆十九年(1814),魏源第一次上北京时,就注意到了黄河的变迁,成诗道:
客行梁宋道,言访梁宋迹。
欲寻史上踪,十九无一获。
浊河决千里,一淤辄寻尺。
屈指三千年,几决几淤积。
每有浚濠人,十仞逢甍脊。
沙覆中天台,尘掩兔园宅。
当年歌舞馆,下隔黄泉百。
当年龙战垒,上有河声湱。
陵谷复陵谷,太息重太息。
今日为陵,明日成谷,黄河如此大的自然变化,影响着社会的变化。这,引起了这位热血青年的无限喟叹。这,也引起了他对井田时代地尽其利、水旱无忧的向往:
缅怀画井世,畎浍兼沟涂。
经纬备潦旱,纵横资世储。
一经阡陌辟,屡值黄流潴。
谁言尽地利,地利弥有馀。
也许,这个时候便是他往后思考如何治理黄河的契机。
道光二十年(1840),作为幕僚的魏源,奉督抚之命去疏浚江苏的徒阳河,这更增加了他对水患水利的感性认识。
道光二十四年(1844)和第二年的春天,魏源两度上京赴试,两度从固安北渡永定河,顺便与这里熟悉河事的人了解永定河的水文情况,写成《畿辅河渠议》。他认为,畿辅的漳河,宜导之东北行,“东北行则安,东南行则病”,因为漳河的地势,南岸高,北岸低;永定河则宜导之南行,因为永定河的地势,北岸高,南岸低。他批评说:“近日治水者皆反之,逆水性,逆地势,何怪愈治愈决裂?”
他又认为,治漳河、永定河等应以“不治之治”为上策,即不筑堤束水,任其“迁徙无定”,因为“退淤之后,麦收必倍,报灾之岁,例免差徭”,“膏淤所及,以夏麦倍偿秋禾,民反为利”,大水退后,“土人谓之铺金地”。他进一步说,河水“以千里来源,而束之两堵之堤,适足激其怒而益其害,又况两岸有沙无泥,遇风则堤随沙去,遇水则堤与沙化,是筑堤不能束水”。
永定河本名浑河,因为河水非常浑浊而得名。上游称桑乾河,流至宛平,称卢沟河,下游则纵横荡漾,河道迁徙无定,故俗称无定河。康熙帝于三十六年(1697)亲至河边观察水情,第二年即派大臣于成龙进行修治,自良乡老君堂旧河口起,经固安、永清至东安狼城河,修筑南北河堤一百八十里,浚河一百四十里,引导浑河水出霸州柳岔口三角淀,至天津西沽入海。康熙帝赐名为“永定河”。这是康熙帝和于成龙的一项政绩,被载入史册。然而,魏源记载道:“康熙三十九年,抚臣于成龙发言改河东北,注之东淀,而淀受病。乃乾隆二十年,开北堤放水东行,于是河日淤,堤日高,视平地一二丈以外,动辄溃决。”他叙述的当然是事实,说明康熙乾隆年间对永定河的治理有功效,也有后患。
但是,魏源对漳河、永定河“无治而治”、任其患漫的思想,却很新鲜、很特别的。这大概是他看到堤高沙积的不良现实而产生的一种相反的思路,又过分地信任“旬日水退,土人谓之铺金地”的那种粗放式耕作的“理想”了。
当然,作为一个尚未踏入官场一步的士人,魏源能够写出这样的文章,也足见他对水利事业的关心。后来(道光二十九年)他在扬州府兴化县任代理县令,冒着淋漓大雨,不顾生命安全,又越级请命,以保护大堤不溃,保证下游田亩不淹,是他关心水利事业的思想的必然逻辑发展。这年,也是因为魏源关心水利事业,两江总督陆建瀛委托他查勘“下河水利救解之策”,同时“将上游、下游及中段情形逐一查访”。于是,他经六安至盱眙及安徽天长等县,巡查禹王河故道,并汇查了历年的案卷和河图图说,于道光三十年(1850)向总督写了一封“论下河水利”的信。
信中,他对长江北岸江苏地段的河渠情况作了相当专业的分析,否定了过去的三种治水方策:一是引淮河水入长江;二是在下游筑堤束水归海;三是移邮南四坝于宝应县,又在山阳(今淮安)县的泾河建闸,以求河水归海之路较近。他否定的理由都相当充分。他建议:“求其可以拯急而费省者,莫如先培运河西堤石工之一策。”因为运河西堤紧靠洪泽湖、白马湖、高邮湖。
邵伯湖,“两面皆水”,而各湖又接纳包括淮河在内的众多河流的来水,一到汛期,西堤即有溃决之虞,江苏腹地可成水泽。第二年(咸丰元年),魏源又上书陆建瀛,为下河七州县请命,要求西堤补砌条石,不用砂土。这样,“既有归江各路以畅之于下,有归海各闸以泄之于旁,又有西堤石工高厚坚固以横障于前,纵有全湖风浪,不能冒过西堤”。
虽然魏源声称,这样做,“实急则治标之计”,但亦为莫可如何的“拯急”之策。这反映着魏源在关注水利事业的过程中的求实态度。
魏源关注江苏腹地的水利,论及下河七州县的防汛避患,固有总督陆建瀛的委令在前,更因魏源关心民瘼。此时,魏源不过兴化县一位知县,不过高邮州一位知州,而他谋及的却是全局。这正如包世臣在信中所说,“阁下以邻境有司,不分畛域,出手券谕市人,出钱抢险,得以保全新埽三段,非恫在抱如吾弟者,安能及此?”魏源就是一个这样想干大事实事的无私者。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孕育着灿烂的中华文化。但由于它流经黄土高原,过潼关以下地势平坦,大量泥沙淤积,遂成水患。据史料,在东汉明帝永平十年(67)就有治理黄河的记载。当时,王景、王吴率“卒数十万”,“修渠筑堤,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馀里”,“直截沟涧,防遏冲要,疏决壅积,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无复溃漏之患”。
千乘,即今山东利津县,是当时黄河的入海口。是后千多年,历代都有河患,都有修筑。至清初,黄河下游淤塞不通,黄河水漫流南下,夺淮河河道入海,黄淮合流,以致苏皖北部泛滥成灾,成为心腹大患。康熙帝当政,“以三藩、河务、漕务为三大事”,书写在柱上,时时提醒自己,这说明治理黄河当时已成为国家大政之一。他起用靳辅、陈潢等治理黄河,筑堤御水,前后历时二十六年,才使黄河“水归故道,漕运无阻”,且“清水畅流敌黄,海口大通,河底日深,黄水不虞倒灌”。
但是,包括靳辅在内的历代治黄河者,大都在下游用工夫,没有根治中上游的水土流失,致河患依然如故。正如魏源所描述的,河臣多用“堵”的办法治河,“惟务泄涨,涨愈泄,溜愈缓,海口渐淤,河底亦渐高,则又惟事增堤”,“河高而堤与俱高”。“河堤内外滩地相平者,今淤高三、四、五丈,而堤外平地亦屡漫屡淤,如徐州、开封城外地,今皆与雉堞等,则河底较国初必淤至数丈以外。”黄河在徐州、开封等处,成为了“天上河”。因而,“每汛必涨,每涨必险,无岁不称异涨”。故自“国朝以来,无一岁不治河”。
在这种情况下,朝廷用于治河的开支,年年递增,成为清代财政的一大负担。魏源记述道:“乾隆四十七年(1782)以后之河费,既数倍于国初;而嘉庆十一年(1806)之河费,又大倍于乾隆;至今日而底高淤厚,日险一日,其费又浮于嘉庆,远在宗禄、名粮、民欠之上。”据魏源估计,“国家全盛财赋,四千万出入”,而治河“岁费五六百万”,占全年总收入的八分之一至七分之一,是故“河工者,国帑之大漏卮也”。
针对清朝以往一百多年治理黄河以“防、堵”为方针,筑堤束水无效、国库开支又很大的情况,魏源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改道,即改变黄河的河道。他断言说:“断非改道不为功!”并且说:“人力预改之者,上也。否则,待天意自改之。”
如何改道?魏源根据自己对黄河两岸的地形地势的分析,认为:黄河“一旦决上游北岸,夺溜入济,如兰阳、封丘之事,则大善;若更上游而决于武陟,则尤善之善者”。
办法是:“乘冬水归壑之月,筑堤束河,导之东北”,经河南的阳武[今原阳]、延津、长垣,到山东的东明,此“即汉唐旧河故道”,有“天然河漕”;然后流至山东张秋,与运河贯通,至于“张秋以东,下至利津,则就大清河两岸展宽”。
魏源认为,如此改道之后,“河既由地中行,无高仰,自无冲决;即使盛涨偶隘,而堤内堤外相平,一堵即闭”,自无水灾之忧;而且,“南岸有旧河淤身千馀里,高五六丈,宽数百丈,以[旧河]北岸为[新河]南岸,新河断不能再侵而南”,黄河水不会再泛滥于河南南部及皖北和苏北了。
魏源进一步说,这样改道有不少好处,主要是,每年可节省治河费五百万,“十数年可渐复乾隆库藏之旧”,节省的钱可以“全力饬边防、兴水利”;黄河以北自原武至考城一线土地硗瘠的居民,可迁至自开封至淮海一线土地膏腴之区;江苏的洪泽湖水通畅入海以后,淮西涸出的数万顷田土,可以开垦,且可“五坝不启,下河不灾,淮扬成为乐园”。
可是要实现黄河改道这样浩大的工程,谈何容易!主要的困难在于人们的思想问题。魏源预计,害怕裁缺裁费的河员,和不敢负责、坚持旧制的“畏事规避之臣”,必会“簧鼓箕张,恐喝挟制,使人口慑而不敢议”。魏源还预计,“自非一旦河自北决于开封以上,国家无力以挽回淤高之故道,浮议亦无术以阻挠建瓴之新道,岂能因败为功,邀此不幸中之大幸哉!”果然,十三年后的咸丰五年(1855),黄河在开封的铜瓦厢缺口,洪水夺大清河入海,与魏源设计的新河道大体相同。不过,这不是“人力预改之者”,而是“天意自改之”。
其实,作为一个无职权无名分的普通士人,魏源关于黄河改道的美好理想,能够上达到朝廷重臣和皇帝那里吗?阻力仅仅来自河员和一些“畏事规避之臣”吗?在魏源撰《筹河篇》的道光二十二年(1842),经过鸦片战争的大清王朝,已在走向没落,有心思、有财力去兴建这样的浩大工程吗?而此时清廷财政已捉襟见肘。况且,正如魏源自己所说,这个时候,“国家大利大害,当政者岂惟一河!当改而不改者,亦岂惟一河”!所以,魏源只好自我解嘲:黄河改道这样的工程,非自己这样的“下士所敢议”。不过,自己既有志经世,出乎良知,又说,“亦乌可不议”?
关于长江中游的水文和水患情况,魏源陈述说,“历代以来,有河患无江患”,但是,到了嘉、道年间,“数十年中,告灾不辍,大湖南北,漂田舍,浸城市,请赈缓征无虚岁,几与河防同患”。
为什么呢?魏源分析说:一是“承平二百载,土满人满,湖北、湖南、江南各省沿江沿汉沿湖,向日受水之地,无不筑圩扞水,成阡陌,治庐其中”,蓄水区“十去五六矣”,于是“水必与人争地”。二是上游移民“刀耕火种,虽蚕丛峻岭,老林邃谷,无土不垦,无门不避”,于是“箐谷之中,浮沙壅泥,败叶陈根,历年壅积者,至是皆铲掘疏浮,随大雨倾泻而下”,到达江湖,“水去沙不去,遂成洲渚。洲渚日高,湖底日浅”,而“近水居民,又从而圩之田之”,“洲渚日增日阔,江面日狭日高”。结果“向日受水之区,十去其七八矣”,“容水之地,尽化为阻水之区”。魏源对湖广产生水患的这两个根由的叙述,是很符合事实的,很科学的,说明魏源目光锐利,剖析至精。
魏源还具体地指出:长江、汉水“上游,旧有九穴、十三口,为泄水之地。今则南岸九穴淤,而自江[指长江]至澧[指澧水]数百里,公安、石首、华容诸县,尽占为湖田;北岸十三口淤,而夏首不复受江,监利、沔阳县亦长堤亘七百馀里,尽占为圩田”。古籍所记载的云梦泽,早已不复存在。魏源用诗句记述这种变迁说:
自昔楚薮夸云梦,几见洞庭登《禹贡》?
今日楚薮称洞庭,遗迹何处寻云梦?
水钟三湘失七泽,自古沧桑多变易。
遂以九江诬洞庭,那识长江旧横辟!
荆州九穴十三孔,今惟二穴馀皆壅。
地不让水水争地,仰盂受灌建瓴涌。
沿湖圩田岁增岁,曲防壑邻占地利。
何况老林秦蜀开,下游沙塞洲渚洄。
更加夏汛蛟水至,万马孰御风涛雷。
呜呼!八百里湖十去四,江面百里无十二,安能塞川川不流!
面对江湖的这种现状,魏源提出了一个治水的指导方针:
“两害相形,则取其轻;两利相形,则取其重。”围湖垦田,“人与水争土为利”,确实可以解决湖区人民的部分生计问题,国家亦可升科,增收财政收入,这都是利。但是,减少水患,则是更重更大的利。“两利相形”,只能采取减少水患这一方。故他建议说:“为今日计,不去水之碍而免水之溃,必不能也;欲导水性,必掘水障。”不管是官垸还是私垸,“但问其垸之碍水不碍水”,碍水者毁,以畅通水路。这样,可以“毁一垸以保众垸,治一县以保众县”。无疑,这一疏通水路的治水思路是很正确的。
不过,他说:“患在人者,上游之开垦,亦无如何。”上游的过度开垦,造成水土流失,这是魏源已认识到了的。但“亦无如何”,放任不管,是当时上游的水土流失,还没超过“度”,无需管呢?还是魏源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过度开垦的严重性,无用管呢?还是国家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羽檄纷驰,无心又无力管呢?魏源还注意到了长江下游的水文和水患情况。他分析江、浙的地形说:“一自湖州[今吴兴]趋杭州,一自镇江趋常州,南北皆高。”长江下游沿岸诸州县因而成为“南北皆高”的中间洼地,加上这地区河湖纵横如网,水患必然频仍。道光三年(1823)、道光九年(1829)、道光十四年(1834),江苏都大涝成灾。
他又分析江苏南部的水系情况说:境内“黄浦东江、吴淞中江、刘河、娄江,皆泄太湖之水入海,再北为白茆、七浦,为孟犊,则泄太湖之水入江”。然而,浏河、白茆河、孟犊河到道光年间早已淤塞,流量最大的吴淞江也屡浚屡淤。道光五年(1825),江苏巡抚陶澍主持疏浚了吴淞江。
道光十二年至十五年(1832-1835),总督陶澍与巡抚林则徐又主持疏浚了浏河、白茆河,会通了七浦、徐六泾等处出水口,修筑了昆山的至和塘,疏浚了太湖的茆淀和三江口的宝带桥。对于浏河、白茆湖的出海口,因为内外高下相等,潮水常常倒灌,使两岸田土逐渐碱化,林则徐又主持于两河的出海口修筑高坝,“使不通湖,而导蓄清水”。道光十四年(1834),浏河、白茆河“骤涨丈馀”,林则徐又下令“急决海口大坝”,“不三日水骤退,吴田大熟”。魏源歌颂道:两河河口的高坝,“急则泄水入海,常则蓄水隔潮,已岂非地势使然哉”!
此外,魏源又考虑到江水水平面的高低情况,认为“水平则低田筑堤,使大水不能入民田,可使堤外塘浦之水自高于江,而江水自高于海”。因而他提出了两点设想:一是沿太湖各州县“大修圩田,则足以束外水使之平”,以建瓴之势,东注于江于海;二是于上游的长桥、宝带桥一带,疏浚吴淞江,“大去壅塞,方可吸湖水,使之奔腾于江”,同时“于吴淞口对坝逼溜”,以“激江水奔腾入海”。这些举措虽未能付之实施,未知后果若何,然而魏源的“纸上谈兵”,却是谈得似乎有理有据。至于在湖的周边“大修圩田”,使湖面日益狭隘,肯定是不妥的。
魏源认为:“天下事皆先本后末,惟治水则以末为本。”
所谓“治末”,就是重在治下游、治尾闾,“其利害功效,下游居十之七八,而上仅十之二三”。在苏南,“治吴中之水,终须致全力于吴淞,而未可紊其节次,劳其工程,舍尾闾而先肠胃哉”!下游通、尾闾畅,自然水流可迅速入海。魏源的这一设想有一定道理。
但是,治水不重视治源头,不重视治中上游,而以治下游、治尾闾为“本”,其他为“末”,这种思想对根治水患,恐怕是无益有害的。这,与他论及两湖水利时不重视治理源头的过度开垦的思想,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