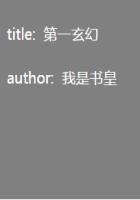火车跑出城市,如同牛仔骑马穿过向往的草原。五十个小时的硬座,一天仅一趟的青藏线,终于抵达藏族聚居区,身边揣着祖父收藏的旧版《植物图鉴》和《本草纲目》。
山路很长,从雨天一直通向夜色。很久不见暮色四合了,某人说。我正答应着,蓦地眼前一亮:路边竟有荆条花。一直走,身边一丛一枝,疏密相间,荆花开放。某人停下,在车票上轻轻写下花的名字。我告诉她,荆条花也叫牡荆,就是负荆请罪的荆,也是荆钗的荆。
背上有花开,想必负荆请罪在这里也演化成了美丽的罪。
某人“哦”了一声,说,这些不知名草木的故事,以后你得好好讲给我听。
山路依旧纵横,每一条都通向茂盛野草间。不禁令人遐想,夜里,山花烂漫处,定会有萤火虫明明灭灭,星星点点,漫撒夜空。
我们要拜访的人,就住在桑耶寺。桑耶寺在桑耶镇,桑耶,藏语意为“出乎意料”。这不起眼的地方会有什么出乎意料之处,我不清楚,只知道,布达拉宫如今成了游人如织的名胜,桑耶寺却依旧很安静。历经千年和无数劫难的莲花生法师静静地看着络绎到来的俗人,还有门口那只藏羚羊。
信步而行,一间偏僻的佛堂内,一个年迈的女子坐在佛前,数着轮回的念珠。桑耶寺,让人心里一动。
在这样一个缺氧的地方,人的思想精力极易过剩。
因了祖父的影响,每到一地,我也总想给当时的心境栽几株新生草木,于是有了记录之意,不写人事,只记录一些花花草草的情态,与草木谈谈心。
或许,藏地人事物的密码心结,也不过像那野草、野花。
绶草
在《诗经》中它是鬲鸟。二十多朵细密的小花,就如二十多只盘旋归落红唇白齿、一路洞开歌喉的小鸟。然而,它是植物。花开,纤细的身躯,被小小花儿包围得错落有致,盘旋缠绕的炫舞,和路过行人哼的会不会是同一首歌谣?事实上,我确实没想到,在高原还会见到绶草。我以为已经走了很远,远到存在的事物里只有陌生。以前,对西藏的想象,犹如对梦境的想象。梦里,天应该是雪山上的天,只有蓝色、阳光和白云。
我不再独语,只想倾听,某人指尖上最柔软的声音。高原不仅生育苦寒的骆驼刺,你看,绶草那么动人地开花,也旋转着舞蹈。
天竺葵
从南到北,到哪里都有天竺葵。拉萨的天竺葵长得最好,是高原有最好的阳光吧,好得竟让人不能直视,只能戴着墨镜仰头,看布达拉宫的窗口。每一个窗口,都有天竺葵盛开,那么斑斓的颜色。来浇水的喇嘛看见这样的颜色,合着花意,会想起怎样的故事呢?天竺,究竟只是一个虚构的传说,还是梦中的现实。
琉璃草
收获和预期之间的隔阂,是天与地的差距。而高原的天和地之间,除了矮小的雪山,已经没有距离。那么蓝的天,那么苦寒的地,那么多人到这里,寻找自己,迷失自己,忘记自己。只有琉璃草,兀自开花,不用美丽的故事,只用自己,就能讲述奇迹。那么大的天,那么大的地,那么小的草,那么蓝的琉璃,触手不可及。
毛蕊花
毛蕊花的蒴果是卵圆形的,种子多数细小、粗糙。疾驰的车上,疾驰的人,把镜头伸出窗外,本意是想带回山路边一株野草,回来给遇到的好友讲,一个人与一株草萍水相逢的故事。高原上,确实该有这么高大粗野的植物,和人一样高的草,同雪山一样,没被污染的草。随行不懂植物链的导游管它叫高原一枝蒿,却是比本名“毛蕊花”还好听的名字。会心一笑,一株野草里,也有别样的味道。
翠雀花
高原上的道路太悠久,悠久得像亘古的时间。蓝天白云是别处不曾有过的茂盛,而道路只在贫瘠单调的土地上延伸。幸好,路边还有那么蓝的花,比天空还蓝的翠雀花,长长的花萼像鸟。藏族的《晶珠本草》称它为德木萨。我不明白的语言里,神秘的蓝色鸟,在高原的风里静静纷飞。
骆驼刺
拉萨四周是山地裸岩,雅鲁藏布江边沙丘成阵,和我的藏地记忆一样,长满一丛丛的骆驼刺。骆驼刺是豆科,开红色蝶形花。没有丰美的水草,骆驼刺是高原羊群的食物。路遇的藏族女人叫它刺,说它是他们的柴。如果在漫长的公路上下车,可以去看看,贫瘠土地上坚韧生长的骆驼刺。如果有缘,你能遇见花开。
川西合耳菊
长久以来,因为对藏族聚居区的植物知之甚少,不少人甚至错误地认为,西藏地势高,气候酷寒,是不毛之地。其实藏族聚居区令你耳目一新的植物实在难以言尽。一路行来,我见到的第一种感觉新鲜的植物当数合耳菊了。拉萨离我的家乡很远,可是绿化树却和我出生的地方一样,主要是杨、柳和榆。出拉萨,去林芝,十个小时的漫漫长路,中途休息,跑去路边看植物,见到的就是野生的合耳菊,开着乳白色的花。不鲜艳,于我却新鲜。
石龙芮
像是专门等待一个人的到来一样,那棵开花的石龙芮。石龙芮不是坚硬的石,不是缥缈的龙,只是草丛里的一株草,花朵上明亮的阳光。旅人不在的日子里,结成花朵中一颗绿色的椹果。路边草丛的石龙芮,看着人们来来去去,留下匆忙的脚步。我等待一个停下的人,在被马赛克碎片化的世界里,听她讲,椹果里很长的故事。
金露梅
高原荒凉的路边,和骆驼刺一样多的灌木是金露梅。只是那名字里,多了一点水,多了一点生命的丰沛和柔美。生命的本质没有差别,在干旱的土地上兀自生长。没遇到骆驼刺的花期,疾驰的路上,看得见金露梅开黄色花。陪伴它开花的,是白色花的银露梅。有时我不禁想,人,为什么要选择在这空旷之地安家呢?某人说,答案不就在你眼前吗,江南有紫衣甘蓝,这儿有金露梅。
我把祖父托我带的书交给桑耶寺里的那位老人。先辈们的故事,我们这些晚辈不太清楚。或许,它们适合继续尘封在书本里,让静默的时间去解密。
走出寺庙,见到很大的柳树,刺眼的阳光下,柳树巨大的树荫像个阴凉的房子。房里只有两头牛:一黑一黄。向房子走来的,是一个穿红衣的喇嘛。黑牛看着喇嘛,喇嘛停下,看看黑牛。喇嘛走到黄牛身边,伸手去摸它。黄牛不看喇嘛,黑牛扭头看他。喇嘛转过身,离开黄牛,走过黑牛。黄牛不动,看着别处,“哞—”一声长吟,黑牛终于耐不住,视远山树影,如做人声语。
转身,一旁卖酥油茶的小姑娘看我照相,便微笑着凑过来,要我给她照一张。照好了给她看,她也只是笑,既不要钱,也不要我寄照片给她。不远处修建的建筑旁,意外地有正在打夯的青年男女。他们动作整齐划一,手持工具,男工起头,女工应和。一边唱一边击夯,像弹剑而歌的隐者一样向四面舞动。歌儿的旋律很简单,朗朗上口,清脆爽利。
七碗爱至味,一壶得真趣。空持百千偈,不如吃茶去。这样的场景里,我也自问城市的自己,除了键盘和屏幕,还能否找到一张干净的纸和一支能写的笔。文字消失、词语不在的夜里,我会弄不清体内的经络是否有血液流动,还是已变成无形的网络。机器世界会有怎样的秋天呢?铁片或者塑料做成的虫,一定不会是《变形记》的故事。
雨落在身上,没有诗意,只有肌肤锈迹斑斑。于是心中升起一种希冀:想召唤一只蝉,在落满尘埃的窗前,歌唱。
归途。月光正当好,不是狂人看见的那枚,是荷塘边的朱自清:这样的夜晚,什么都可以想,也什么可以都不想。怀中书本里,赫然是一首鲁迅的打油诗:爱人赠我百蝶巾,回她什么—猫头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