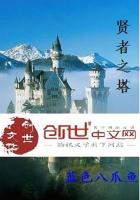“希腊”安东尼斯·萨马拉基斯
命令很明确。禁止下河洗澡,而且沿岸200米以内任何人不得擅入。因此丝毫没有可以误解之外。任何违令者将受到军法处置。
这命令是几天前由少校亲自向他们宣读了的。他下令全营集合向他们宣布了这一命令。这是司令部的命令,可不是开玩笑的。
大约3周前,他们来到河的这一岸,停止前进。对岸就是敌人,通常被称“敌方”。
3周来,毫无战事。当然,这种状态会持续很久,但眼下很平静。
河两岸的纵深处都是茂密的森林,双方的部队就各自驻扎在自己一边的森林中。
据情报,“对方”有两个营。但是他们并没有发起进攻。谁知道他们的意图是什么?同时,双方都派出哨兵隐蔽在本岸的森林中,戒备着可能出现的情况。
3个星期。真的已经过去3个星期了吗?自从两年半以前的这次战争开始以来,他们不记得曾有过类似的间歇。
他们刚来到河边时,天气还很冷,然而几天以前天气放晴了。现在春天来了。
第一个潜下河的是个中士。一天早晨他悄悄溜了出去,跳入水中。不久他肋下中有两颗枪弹爬了回来,他只活了几小时。
第二天两个二等兵去了,没人再见到他们。只听到几阵机枪扫射声,然后是一片,沉寂。于是司令部就下了这道命令。
但是,河仍十分诱人。他们听到哗哗的流水声,焦渴难忍。两年半来,他们一直过着邋遢的生活,忘掉了一切玩乐滋味。现在他们碰上了这条河。然而,来自司令部的命令……“滚他的司令部命令!”那天夜里他从牙齿缝里低语说。
他辗转反侧不能入睡。远处潺潺的河水依稀可闻,不让他休息。
明天他要去。是的,他一定要去。司令部的命令见鬼去吧!其他的士兵都在酣睡,最后他也睡着了。他做了一个梦,一个恶梦。起初他看见的是河,照它本来的那样。河就在他的面前,在等待着他。而他光着身子站在河岸,没有跳下去,似乎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拉住他。后来河变成一个女人,一个身体结实丰腴、肤色黝黑的女人。她赤裸着身体躺在草地上,正在等着他。而赤裸着站在她面前的自己并没有扑向她。一只无形的手似乎在阻拦着他。
他醒来时感到精疲力竭。天还没有亮……他来到岸边,站住了,开始凝视河水。河啊!这条河果然存在,他曾经一连几小时地怀疑冥想,这条河是否存在,或者只是他们大家的一种幻想。
他已找到机会,来到河边。天气多好啊!如果他运气、没有被人发现……。只要他能够跳进河中,泡进水里,无论发生什么他都不在乎。
他反衣服留在岸上的一棵树旁,枪立靠在树干旁。他转头扫了一眼身后是否有自己人,又朝对岸瞄了最后一眼,看是否有对方的人,然后纵身跳入了水中。
他那赤裸的、经过两年半折磨和已有两处伤痕的身体一进入水中,他就立刻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新人。好像有一只拿着海绵的手通过的身体擦去了那两年半的岁月。
他时而仰泳,时而匐泳。他顺流漂浮,接着又长时间的潜入水中。
作为战士的他在此时变成了一个孩子。他只有23岁,但过去的两年半已在他内心留下了深深的创痕。
左右两岸都有鸟群在来回飞翔,有时它们掠过他的头顶向他招呼。一条被水流卷裹的树枝漂到他的前方,他扎了一个深猛子想一次就到达那里。他停下来,想看得清楚些。那另一个游泳者也看见了他,同时也停了下来。他们彼此默默地注视着。
他立刻回过神来,恢复到原来的自我———一个经历过两年半战争、荣获十字勋章、把步枪留在了树旁的军人。他不知道对面的家伙是自己人还是对方的人。他怎么认得出来呢?他只一个脑袋。他可能是自己人,也可能是对方的人。
有几分钟时间两人都待在水里没动。一个喷嚏打破了静寂。是他自己打的喷嚏,而且像往常一样大声咒骂了一句。那个人开始很快地游向对岸。他自己也没浪费时间,拼命向岸边游回。他先出水,冲到放枪的地方,一把抓起了枪。对方的那人还刚从水里出来,这时,他也跑去拿自己的枪了。
他举起枪,瞄准。要击中对方那人的脑袋太简单了。只有20米外奔跑着的那一丝不挂的人体,是一个很容易击中的靶子。
不,他没有扣扳击。对方那人在彼岸,显条条的像刚从娘胎里出来时一般。而自己在岸这边,同样赤条条。
他开不了枪。两个人都赤裸着。两个裸体的人,脱掉了衣服,脱掉了国籍,脱掉了姓名,脱掉了军人的身份。
他开不了枪。现在河不是把他们隔开,相反把他们联结在一起。他开不了枪。
对方现在已成了一个普通的人,不再是专门名词“对方”,比他自己不多也不少。
他放下了枪,垂下了头。直到最后,他什么没见到,在眼角瞥见的群鸟,因听见对岸枪响而惊飞。他应声倒下了,先是膝盖跪下,随后平扑在地。
“品味”
作者在选材上颇下了一番功夫,他将光辉的人性放在了人间最具破坏性和最丑恶的战争之中来表现,益突出了人性的光辉,鞭笞了战争对人性的扭曲。两队处于敌对状态的士兵,夹河驻扎,对河流的向往促使两支队伍中都有一些士兵不顾禁令,偷偷下河游泳。他们在河中游泳的时候变成了一个个孩子,他们太年轻了。当小说中的主人公在河中遇到也正在游泳的敌队中的士兵时,他很快恢复了自我———“一个经历过两年半战争、荣获十字勋章、把步枪留在了树旁的军人。”于是,他上岸,拿枪,瞄准,一系列动作一气呵成,但是他开不了枪,那条河将他们联系到了一起,他们都是赤裸裸的人。对岸的枪响了,他倒下了。
但一个对于人和人性的思考却在此时不知不觉地深入到了读者的心中。这个倒下的士兵的自我到底是什么呢?是那个“一个经历过两年半战争、荣获十字勋章、把步枪留在了树旁的军人,”还是那个赤条条的一丝不挂的孩子?这个士兵倒下了,但是他身上所表现出的光辉人性却由此站立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