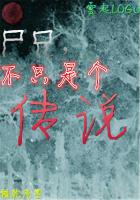田忌的好友孙膑说,我知道将军是在为赛马失利而苦恼。其实,在我看来,你的马和齐威王的马,实力上差不了多少。输在你的策略上。
田忌顿时来了精神,愿闻详情。
孙膑说,齐威王势力强大,在国内广招好马。每个等级的马都比将军马的快。
田忌说,是啊,所以我屡战屡败。
孙膑说,其实,只要将军将赛马的秩序调整一下就可以马到成功。
田忌急不可耐,你说说如何调整法?
孙膑说,你可以用你的下等马对齐威王的上等马,用你的上等马对齐威王的中等马,用你的中等马对齐威王的下等马。这样保你两胜一负,稳操胜券。
田忌闻后大喜,立即找齐威王赛马,果然如孙膑所料的那样,田忌二比一获获胜。田忌大摆酒席款待孙膑。
齐威王连续赛马失利,十分沮丧。为赢回本钱,几乎每天都要和田忌塞上一回,可是每赛必输。齐威王心中窝火,竟然病倒了,茶饭不思。
齐威王手下的一个驭手,见大王病倒,便来求见,称有办法战胜田忌,只需纹银千两。
齐威王大喜,叫人拿来纹银交与驭手,说,如果此次获胜,还有重赏。
驭手说,大王尽管约田忌前来赛马,只是赌注一定要大,让田将军从此不敢再与大王赛马。
齐威王便差人越田忌前来赛马。
田忌因为齐威王生病,好多天不赛马了,心里着急上火。听说齐威王又邀请他赛马,自然高兴之至。便带着马匹和驭手前来参赛。
第一局,齐威王的上等马出战,田忌用下等马应付。齐威王下的赌注是半个家产。田忌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赛马开始,齐威王的马自然是一马当先,最先冲到终点。
齐威王笑逐颜开,田忌也是面不改色。
第二局,齐威王的中等马出战,田忌用上等马应战。田忌下的赌注也是半个家产。齐威王说,如果你再输了,你可就真的是倾家荡产了。
田忌心有成竹,嘴上却说,我只是想捞回刚刚输掉的半个家业,齐威王手下留情啊,哈哈哈。
赛马开始,锣声响过,田忌的赛马箭一般蹿出,齐威王的赛马却还在原地不动,齐威王的脸当时就白了,摔了手中的酒杯,刚想斥责。就听到一阵急促的锣声。裁判判定田忌将军的赛马违规抢跑了,重新开始比赛。跑出半程的赛马又被牵回原处。
重新开始,情况依旧,田忌的赛马又是抢跑在先,跑出半程的马又被牵回,赛马已经开始喘着粗气了。
田忌急了,你们的锣是怎么敲的?
齐威王说,田将军莫要紧张嘛。也是你的马求胜心切啊,欲速则不达。你看我的马就是训练有素,原地不动啊。来来来,喝酒,喝酒。
锣声再起,赛马腾空而出,双方几乎并驾齐驱。田忌的上等马优势不再,最后时刻体力明显不支,齐威王的赛马领先一个身位率先到达终点。
好!齐威王一饮而尽,说田将军的马也相当不错啊,只是险胜,险胜。
田忌脸色发白,坐在椅子上,如同刚刚跑完赛程的马匹一般直喘粗气。
齐威王拍着田忌的肩膀,说田将军,最后一句也就不用再赛了吧?
田忌说,不,要赛,赛到底!
齐威王说,还赛啊,将军已经输光了所有的家当,你押什么啊?
田忌说,就押我这双手。
第三局,齐威王下等马出战,田忌用中等马上阵。
赛前,裁判认为田忌的赛马尾巴太长,还来回的摆布,都甩到了其他马的眼睛里。要求把赛马的尾巴剪短,驭手认为这是无理取闹,拒绝。拒绝就取消比赛资格。驭手赌气,把漂亮马的尾巴剪得像个秃尾巴鸡,别说观看的人取笑,连赛马都觉得自卑,低着头,蹄子刨地。齐威王的驭手还牵来一匹发情的小母马在没有了尾巴的马前走来走去,搞得那匹赛马心不在焉。锣响了,还都没有反应过来是怎么一回事,输了个稀里哗啦。
齐威王哈哈大笑,田将军,你的那双手还是留着打仗立功再赚家业吧。失陪了。
田忌稀里糊涂输了比赛。垂头丧气地往家走,路过一家酒馆,忽然看见赛马的裁判和齐威王的驭手在推杯换盏,喝的正欢。
田忌当时就吐血倒地。
秋祭
我和红酒是朋友,红酒写小小说。
红酒笔下的故事,都是以相思镇为背景的。“小贱妃”是红酒一篇小小说里的人物。
当年,相思古镇有个唱青衣的女演员,饰演皇姑爱由着自己的性子来,她忘了自己是身穿日月龙凤衫的金枝玉叶,只要一出场,手端玉带侧身站定,就冲观众频频地丢媚眼儿,师姐给她起了个绰号“小贱妃”。“小贱妃”的戏格外出彩,观众喜爱,也惹得县里的一个头头儿春心荡漾。想对“小贱妃”非礼,岂料“小贱妃”戏里戏外两样人,义正词严地拒绝,全没了往日的妖媚惑人。
我赞叹红酒笔下的人物形象,也很想见识一下“小贱妃”的原型。
红酒认为我的想法可笑,那小贱妃是把舅舅讲的故事加工后虚拟出的人物,怎么能让你去现实中对号入座。
难道不可以吗?我还去拜访过你小说里的人物二功子呢。
红酒不再作声。
前年冬天,海外一个朋友看了红酒的小说《二功子》,专程从美国赶来要见见这个说书人。那天忽地飘起鹅毛大雪,去乡下的路很难走,车轱辘打滑,我们惊出一身冷汗。二功子听说是外国客人来访,高兴坏了,叫了几个朋友,就在土坯屋里拉开了场子,连说带唱了两个多小时,恨不得把自己的绝活都使出来,引得海外的朋友直翘大拇指。回到城里,我们全感冒了。红酒说只当是为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做了点贡献,这个贡献的代价是她咳嗽了俩月,挂了十多天吊瓶。
周末,我和朋友相约去相思古镇寻访一座明末清初的古戏楼。时至晚秋,天已渐凉,道旁的白杨树在秋风中抖索着,枯黄的落叶在瑟风中飘零。垂暮泛黄的野草却显得精神饱满,摇曳着坚韧婀娜的身姿,不卑不亢地凄凉着。
古戏楼孤零零出现在村口,看上去比我想象的还要沧桑。戏楼是两层土木结构硬山式建筑,下面的一层据说是演员起居和放置道具的场所,二层就是演出用的戏台了。台子上的楼板已经破裂,围栏也腐朽不堪,两根柱子上有楹联一副,字迹依旧遒劲飘逸:是虚是实当须着眼好排场,非幻非真只要留心大结局。
村里人见有陌生的面孔来访,便三三两两地聚过来,好像也是第一次看到古戏楼子,与我们一起转悠看。
这里唱过大戏吗?我觉得这不过是民间艺人的杂耍地方。
唱过!全本的《穆桂英挂帅》,《西厢记》,《铡美案》都唱过,你们不知道,听老人说起先这戏楼子对面是东大庙和昭帝寺,再往前两里地就是清代商铺一条街,繁华的很。每逢大集这儿都唱大戏,一唱就是七八天,热闹着哩。
噢,那你们听没听说过,当年剧团里有个绰号叫小贱妃的在这里唱过戏?
村人摇摇头,这是明清的戏楼,几十年前被当作学校,后来成了危房,学校早搬走了。
我走到二层的戏台前,凭栏眺望,想象着当年的繁茂风华,禁不住唱了几句现代京剧。
我的朋友经不住我的怂恿,也来到台前,唱了一段《梅妃》:
下亭来只觉得清香阵阵,整衣襟我这厢按节徐行。
初则是戏秋千花间弄影,继而似捉迷藏月下寻声……
朋友喜欢戏曲,大学里曾修过此类课程,程派的韵味还是有的。我叫了声好。
村民都是在豫剧曲剧窝子里泡大的,对京剧没有多少概念。唯独一个背着柴草的老婆婆似乎听的很专注,还轻轻地点着头合着节拍。
婆婆,一看就知道您懂戏啊。我这位朋友唱得怎么样?
婆婆说,程派,唱得还中,就是神态不像。
哈,真遇到行家了。婆婆,您给指点指点。
婆婆环顾四周,犹豫着。
婆婆,我们从城里来,专们来访古戏楼。看这戏楼子多年没有琴鼓声了,它寂寞着哪。我看您老懂戏,也来一段吧,也不枉这戏楼子在咱村口矗立了几百年。
婆婆让我说动了心,放下柴草,掸掸褂子上的浮尘,伸手捋了捋头发,蹒跚着走上戏楼。就在她往台中央一站的那个瞬间,我们都惊呆了,只见她全无了不安和拘谨,一个亮相,开口唱的是《西厢记》里的红娘:
怨只怨你一念差,乱猜诗谜学偷花。
果然是色胆比天大,夤夜深入闺阁家。
若打官司当贼拿,板子打、夹棍夹、游街示众还带枷。
姑念无知初犯法,看奴的薄面就饶恕了他。
一曲唱罢,竟然往台下丢了个飞眼。我们大声叫好。
村民说,还不知道怡萍她娘会唱戏哩。她闺女怡萍在剧团唱戏,多少年也没唱出个啥样法。听说傍了个大款,立马就出名了。在城里买了房子买了车,要接她娘进城享福,她娘死活不去还把闺女给骂走了。
婆婆走下台,朝我笑笑,又佝偻着身子,背起柴草郁郁而去。
品咖啡时,我把经过告诉了红酒,我说她肯定就是当年的小贱妃,假如她当初能灵活些,别得罪了权贵,现在也不至于落到这种地步,没准还在舞台上风光哪。
人,总要活个气节吧。红酒不再搭话,凝神望着窗外,轻轻地唱了两句。什么词没听清,只是觉得那曲调除了低回婉转外还有些许惆怅忧伤……
秋荒
我和非鱼是朋友,非鱼写小小说。
非鱼说,写字写累了,找个地方采采风,轻松轻松。
好啊。我们开始合计着去哪,我这座城她来过多次,该玩该转的也都去了,她那儿也游了几次,没啥新鲜感了。
要不,就去你的荒岛吧。
非鱼笑了。非鱼有篇小小说《荒》,一个叫民的人,为了躲避现代城市的喧嚣,去了一个荒岛。又耐不住一个人的寂寞,只好又叫来一个女人。结婚生子,不断的引入各类人物,在自己千辛万苦营造出来的现代化岛国里,重新陷入人类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不得已只得再次逃遁。
人是耐不住寂寞的,能耐住寂寞的不是人,是神。没人会喜欢荒岛。非鱼说。
我说,不见得,我的朋友何乃儿就特别的怀念荒岛。
何乃儿是个女孩,是个不漂亮的女孩。何乃儿知道自己长得不招人待见,因为连女孩子也不愿意同自己玩。何乃儿更多的时候都是自己在屋里看书。
女友来找何乃儿了,说准备去死海泥湖玩,涂一身黑泥巴,还护肤美容。何乃儿被说动了心。准备行程的前一天,萌萌忽然来电话,吞吞吐吐地说,同去的几个男同学说人多了,玩着不方便。何乃儿晓得是男同学不愿意自己加入,她豁达地对萌萌说,你去玩吧。我也有了另外想去的地方了。
何乃儿看着自己准备好的行装,心里有些沮丧。她看到晚报广告栏里介绍了一个新开发的海滨景区,闲着也是闲着。自己就去玩一趟。
随团行进的路上,大家又说又笑,却没有人与何乃儿搭腔。何乃儿还听到几个男孩不怀好意的说笑。那个白胖子还夸张地说,可以降下波音747了。他们是嘲笑自己的胸脯平展,缺少女人特征。她装作什么也没有听见,看着窗外海滨的秀丽风景。
在海边戏水满惬意的,四个男孩忽然租来一只橡皮艇,招呼着还有谁愿意上来。何乃儿就跳了上去。白胖子说,迫降啦。他们哈哈笑着,发动皮艇驶向太阳滑落的地方。皮艇离海岸也越来越远。他们这才发现,刚才还明媚的天空不知何时已经变得乌云密布,黑压压的云仿佛伸手就可以触摸到。他们慌了,赶忙找浆划水。雷雨风暴顷刻间就光临,小艇在风浪中任意颠簸,如一枚飘零的树叶。他们喊着叫着哭着,都无济于事,皮划艇将他们翻入大海。
他们清醒过来的时候已经在一片沙滩上,这儿是个孤岛。谁也说不清楚是怎样在海浪中逃生的,大浪几乎扒光了他们身上的衣服,只有白胖子绷在身上的T恤还在。
何乃儿双手紧紧抱着胸,坐在一块岩石上,干瘦的身躯瑟瑟发抖。白胖子忽然脱掉了自己的T恤,走到何乃儿身旁说,穿上吧。何乃儿套上T恤,宽大的衣服穿在何乃儿的身上就像披了一件道袍。
雨停了,风还在刮。瘦子找了个避风的地方,大家挤了过去。瘦子说,反正也睡不着,我们讲故事吧,什么都行。大家就轮着讲自己的事情。何乃儿说了自己的故事,因为我长得不着人喜欢,所以没一个朋友。瘦子说,其实,你的皮肤挺好,又白又细。胖子说,你的头长发又浓又密,我可以摸摸吗?何乃儿说,可以啊。瘦子说,我们四个围成一圈,把何乃儿围在中间,会暖和一些的。何乃儿连忙摆手,不行不行。胖子说,怎么不行,你就是我们的公主。还搂住了何乃儿的肩膀。何乃儿小鸟依人般倚在胖子身边,几个男的竟然有些嫉妒了。
第二天,风和日丽。孤岛上的风光绮丽无比。何乃儿说,我们现在只有等待救援了。与其坐等,还不如我们游游这个小岛哪,好歹我们跟它也是有缘的。大家同意,就沿着岛屿游玩,一边还采集着能填肚子的野菜,鲜嫩的野菜都先给了何乃儿。何乃儿很高兴,告诉大家,今天是自己二十岁的生日。真的?几个男的开始分头采集野花,瘦子的手很巧,编织了一只绚丽多姿的花环,戴在了何乃儿的头上,几个人把何乃儿抬起来,一边走一边唱着祝你生日快乐。何乃儿感动得眼泪都跑出来了。
忽然,远处有了船的影子。大家欢呼着又跑又跳,奔向海边。上了船,何乃儿发现自己头上的花环掉在了沙滩上。何乃儿撒娇地说,我的花环,谁去把人家的花环拿过来。船上的男孩就跟没有听见一样,看也不看何乃儿。何乃儿自己跳下船,把丢在地上的花环抱上了船。一路上,没有人再和何乃儿说话,直到上岸分手,也没有人和何乃儿道别,仿佛形同陌路。
何乃儿时常坐在靠近窗边的竹椅上,出神地望着挂在窗棂上的一只花冠。花冠是用野草野花扎成的。野草早已枯黄,野花也枯萎得如干瘪的姜皮。何乃儿望着花环发呆,她总念叨着还想去那个带给她快乐的荒岛。
非鱼听完故事,没有说话。
我说,想好了没有,到底去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