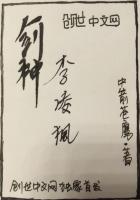队长第一个带头跳进了废墟,拼命地挖起来,边挖边喊,“下面还有人。”第二个人也跳进去,也跟着喊,“下面还有人”这句话,从第三个人的嘴里传出来的时候,已经变了,“下面还有活着的人。”这句话让所有人再次站起来走向废墟。雨水伴着汗水,在战士们的脸上交汇在一起,残碎的混凝土从人们的手中,一块块地被清理出来,在人们心里只有一个信念,只要有一分的希望,就要做百分的努力。当人们再次把一块楼板抬起来的时候,下面果然有一个年轻的女老师,队长轻轻地搬开她,把手指放在她鼻子上试了试,无奈地摇了摇头。于秋华把目光移向她的身体下面,惊呼道,“这下面还有一个学生,一小男生!还活着!”毫无疑问,这是在那场地震来临时,这位老师,用身体护住了他,可老师因此却受重伤,她没能生存下来,而她身下的那个学生却活下来。于秋华过去把那个小男生抱起来,“小同学,你醒醒啊。”小男生慢慢地睁开眼睛,声音微弱地说:“王老师,王老师,你们一定要救我的王老师。”人们相互看了看,没有人言声,队长走过来说:“你们王老师还好,她是一个了不起的好老师。”小男生缓了一口气说:“王老师,没事吧?”人们几乎同时点点头,“她没事。”小男生这才闭上眼睛,“王老师说了,我们要坚持,坚持,叔叔们会来救我们的,可她说着说着就没声了,你们一定要救……”小男孩由于太虚弱了,没等说完就晕了过去。队长回过头来,大喊:“赶快抬到救护所!”
小男孩被人们抬走了,队长走到那位年轻的女老师身旁,轻轻地一点点地擦掉她脸上的泥水,缓缓地站起来,对周围的战士们喊道:“全体队友,立正——”战士们不约而同放下手里的东西,站直了身子,队长带着哽咽声说:“敬礼!”
当记者的经历
那一年,于秋华大学中文系毕业,在省城一家晚报社当实习记者,试用期三个月。他从小崇拜记者的职业,觉得当记者有一种人间卫道士的神圣感,因此对这份工作十分珍惜,工作也很积极,起早贪黑四处奔波。
一天,于秋华在报社值班,电话骤然响起,他拿起电话,对方迫不及待地说:“天都娱乐城失火了,烧得野鸡乱飞,你们快来报道!”说完挂了电话。那段时间,于秋华正准备采写一组消防类的稿子,真是天赐良机,他背上采访包直奔现场。
火是从三楼烧起的,浓烟滚滚中,他看见几个几乎光着身子的小姐从三楼窗口顺着几条用床单接成的绳子滑下来,还有一些男子也抢着往下溜。于秋华此时才明白,电话中所谓“野鸡乱飞”是怎么回事,原来“野鸡”就是这些三陪小姐呢!
于秋华问身旁的人:“怎么还不快打119?”
旁人说:“打了,都过去半个小时了,消防车还没到。”于秋华随手拍下几个镜头,拽住一个逃出来的男子问:“上面还有多少人?”那个人把捂在脸上的手拿开后,于秋华仔细一看,吃了一惊,原来这个人是他曾经采访过的消防队长!看他光着膀子,露着被熏得黑乎乎的肌肉,于秋华赶紧脱下自己的外套给了他,他胡乱地穿上后便迅速地消失在人群里。
过了好一会,消防队终于赶到了,火也随即被扑灭了,这时才见市领导的小车悠悠到来。
回到报社,于秋华如实地写了一篇报道,满怀信心地交给主编。主编看着便皱起眉头,沉着脸把稿子往边上一放,说:“难用。”
于秋华问:“为什么?”
主编说:“关系没有理顺,主题思想没有突出,今晚有电视新闻,你看了就明白。”
那晚的电视新闻确实与他写的不一样,先是领导赶到现场指导,然后是消防员灭火,最后才是逃生者,其中还有那位被熏黑的消防队长救火的镜头。逃生者的形象好像是有次序的安排,至于那些有失大雅的镜头一个也没有,与于秋华所见所写的正好相反。第二天,主编对于秋华说:“看起来你还得好好历练一番。有一篇市里提名的表扬稿子,你去写写吧。”
表扬稿要写的是一位厂长,他的主要事迹是带领全体工人经过几年拼搏,使厂子起死回生,解决了很多人的就业问题。于秋华找到厂长,厂长介绍完自己的奋斗经历后说:“前任厂长也是功不可没的,没有他,就没有我的今天。”采访之前,于秋华向老记者讨教过,说在写表扬稿时,有三种人是不能忽视的:现任、前任、上级,特别是有后台的。于秋华来了个折中法,给他们平分秋色、各个都赞扬一段。
稿子登出来后,坏了,报社的大门被一些工人堵死了。他们吵着闹着要把那位没德性的记者叫出来,要揍他,让他不要写假报道。原来前任厂长是贪污犯,是他把厂子搞垮的,工人们恨透了他。于秋华的这篇文章捅出了大娄子!
主编见状叹口气对于秋华说:“你还是去搞点花边新闻吧,就是人们茶余饭后爱看的那些。比如说,狗咬人,不算稀奇,要是人咬狗,一定会有看头。”
眼看实习试用期就要结束了,于秋华还没写出几篇像样的东西来,心急如焚。那天,他在公园里看到有个秃顶老头搂着一个小姐啃得起劲,猛然来了灵感,很快写出一篇《老狗爱上小花猫,形影不离活到老》的稿子,第二天在报上登了,读者反映还不错,主编也露出了笑脸。于是于秋华如法炮制了《小母狗为了贞操,拒绝做爱》、《想妈的画眉,撞死在笼里》等一些凭空臆造的东西相继见于报端。主编肯定了他的成绩,他也明白该写什么,怎么写了。
实习结束的前三天,主编又把于秋华叫了去,说:“你采写的动物稿件充满人情味,颇受欢迎。昨天,市二医院为动物园的大猩猩成功地做了摘除肿瘤手术,你去了解一下,弄一篇有分量的稿子来,争取能让国家级报纸转载,这对报社和对你本人都很重要。”于秋华当然明白言下之意是这篇稿件关系到自己的去留。
到了医院,那个面色苍白的院长慷慨陈词地讲述他们医院为攻克这一难关,如何精心准备,如何选配精干医生,如何认真诊疗。于秋华听着听着,一个题为《珍惜每一个生灵,让世界充满爱》的稿子就在他脑海中形成了。
采访结束后,院长非得要在京华酒店请于秋华吃一顿,并说:“刚刚到任的卫生局长一会儿也会来,他要亲自对你表示感谢。”盛情难却,在院长的陪同下,于秋华去了。
在经过门诊部走廊时,于秋华发现一个乡下老人蜷缩着躺在长椅上,呻吟不止;走到门口,又见一位衣衫破旧的小女孩,跪在地上磕头:“大爷大娘叔叔们,我爹得了急性阑尾炎,住院费还差500元,帮帮我吧,救救我爹吧!”她身前还扔着些票子,于秋华的心为之一颤,转过头对院长说:“可不可以让他爹先入院,不能因为500元耽误了病人治病。”院长面无表情地说:“这样的事我们见多了。不交足住院费不能住院,这是院里的规定,我也无权改变。”
这时,一辆小轿车嘎地停在于秋华面前,院长说卫生局长来了。于秋华一看,疑惑了,来的不正是那位消防队长吗?他怎么当起卫生局长了?卫生局长见到于秋华,便笑呵呵地对院长说:“这位小兄弟为人仗义,与我有患难之交,你们可不要怠慢他呀!”院长屁颠地说:“一定好好招待!一定好好招待!”于秋华惊奇地问:“你怎么由救火变成救人了?”局长哈哈一笑:“还不是多亏你的那件衣服,我救火有功。”接着他又说,“救人比救火更重要。火灾不能天天有,可病人天天不断。工作忙哟,兄弟,你若是需要看病治疗,就来找我,一路绿灯!”他的话让于秋华哭笑不得。
于秋华猛然想起走廊上那位可怜的老人,就转身对院长说:“那个在长椅上呻吟的老人,是我一个远房叔叔,请你网开一面,让他先入院好吗?”院长望了局长一眼赶忙说:“于大记者,你怎么不早说啊!”他对跟他出来的人说:“快,快把那个老大爷安排到病房去。”望着那位陌生老人远去的身影,于秋华的心一阵发酸。局长在一旁催促:“走,小兄弟,咱们到京华酒店去尝尝大甲龟,那可是从深海里打捞上来的,大补呀。”于秋华趁他们上车之时,悄悄地溜走了。
回到报社后,于秋华什么也不想写了,不久,他便离开了那家报社。
每人一支铅笔
我们这里很穷,周围大山环抱,交通不便。
山村里的孩子们依旧穿着带补丁的衣服,村里的小学就更寒酸了,简直像个破庙。
教师节对我们这些村小的教师来说,只是意味着一天的假期。今年,情况照样如此。老校长慷慨陈辞地宣布完放假一天后,人们都开始为回家做准备了。
“老师,你们等一下。”一个怯生生的声音从外面传进来。接着钻进一个不太干净的脑袋。
“什么事?”老校长认出这是本校的一个学生。
在教师会上,有学生敢闯进来,在这个很闭塞的小学里,还是开天辟地的头一次。一个、两个、三个、一连十几个土里土气的孩子,正正经经地走进来,走上讲台。
老校长莫名其妙地站起来,不置可否地退下来,“你们!”
“老师们,我们听说,大地方的学校,在今天都要发给老师很多东西。你们年年什么都没有。”一个领头的学生用很庄重的声音说。
“我们也想给你们买点东西,可我们凑在一起才3块多钱。3块钱,不够分的。我们还是想给呀。就托二妞他爹,从大地方买来一张纸,几支铅笔。”
说着,他们用长满茧的小手,把纸展开,一个个举过头顶。在那洁白的纸上,歪歪斜斜地写着:“老师,节日好”。那些并不工整并不美观的字体,在一个个又黑又脏的小手上飘动着。
整个会场沉默了,静静地一点声音也没有,就连我们自己都要忘记的节日,在他们心中还活着。一个教师、一个人民小学教师,在那一片片洁白的土地上种下的绿色种子永远地活着,就像这周围的群山一样,永远不会忘记。
那个领头的学生说,“现在,奖给你们每人一支铅笔。”
“哗”,我们这些大人们再也坐不住了,全都站了起来,走向这些比我们矮了多半截的小人们,双手颤抖着领回铅笔,并深深地行了一个鞠躬礼。
一份亲情的承诺
列位,你见过百岁的老人吗?有人说了,见过。那你见过面色红润,神智清醒,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平常连个头疼脑热都少有的105岁的老人吗?有人摇头了,可那位要问了,她一定是位有钱的主,享受着高级医疗护理吧?不,你错了,她是江苏省徐州市沛县大屯镇一位农村老太太,医疗条件一般般。可那位又问了,这位老人是不是吃了什么仙丹妙药?仙丹倒是没有,妙药却是有一副,她的妙药就是,摊上一位心地善良、躬行孝义的儿媳妇张公兰,一个八十岁的老人!与婆婆相守六十四年,照顾高度瘫痪卧床的婆婆,二十八年如一日,无怨无悔!
话说三十三年前的一个初春,天灰蒙蒙的,还下着毛毛细雨。面容清瘦的张公兰缓缓地走出医院,一屁股坐在雨地里,强忍着悲痛,仰望苍天,低声呐喊道:“老天,你怎么这么不公啊!”泪水伴着雨水,从她脸上无声地流下来。那位问了,她怎么了?说起来让人心酸呐。
张公兰十六岁那年,嫁到一贫如洗的唐家,母亲在她出门前,拉住她的手说:“公兰,娘跟你说,你一定要孝敬公婆,人不孝其亲,不如禽与畜。慈乌尚反哺,羔羊犹跪足。人不孝其亲,不如草与木。”那时,涉世不深的张公兰,轻松地说出三个字:“我会的。”这简简单单的“我会的”,在日后的岁月里,岂能是用沉甸甸形容得了。
婆婆唐伊氏年轻守寡,含辛茹苦地把两个孩子拉扯大,那艰辛就别说了,张公兰打心眼里佩服婆婆。婚后,作为大儿媳的张公兰,主动帮婆婆承担起持家的责任。那些年,为了养家糊口,白天,她和男人一样,卷起裤腿,到微山湖破冰捕鱼、捞虾挖藕,常被蚂蟥咬得鲜血直流,手被芦苇刺得伤痕累累。夜里,她还要纺棉、织布到深夜。渐渐地,家境一天天地好起来。可天有不测风云,张公兰二十二岁那年,小叔子突然染病身亡,婆婆第一次白发人送黑发人,哭得死去活来。这还不算,更重要的是,小叔子一家,再加上自己一家,十口人哪,十张嘴,那可不是现在,那是闹饥荒的年月,其艰难状况可想而知啊。丈夫唐金成看看粮囤里那点为数不多的存粮,低声问张公兰:“怎么办?”这点粮食想养活十口人,显然是不可能的。张公兰咬了咬牙说:“走,带上我们的孩子,去逃荒。”那个年代,到处都是逃荒的人,路边常有饿死者。这个决定就等于,把更多的生的机会,留给了老人和小叔子的孩子,把死的危险让自己家人去扛。丈夫含着泪,点点头,于是他们带着大女儿和二儿子踏上一年多的讨饭征程。
过些年,家境好转了,可是现在丈夫又被查出胃癌,还是晚期。在七十年代末的农村,这就是等于判了一个人的死刑。张公兰在雨地里坐了很久很久,才慢慢地站起来,一步一步地向家里走去。到了门前,她又不得不一遍一遍地擦干了泪水,她想哭,但是不能在家人面前哭。家里还有年迈的婆婆和嗷嗷待哺的孩子。婆婆已经失去了一个儿子,如今又要白发人送黑发人,她怎么能撑得住。在孩子们面前,她不能倒下,她倒下了,这个家就垮了。
年幼的小儿子见她回来了,跑过来说:“妈妈,我饿了。”张公兰强忍着泪说:“我这就给你做饭。”婆婆觉得不对劲,担心地问:“金成的病是怎么回事?”张公兰强装出一副轻松的样子说:“没什么大事。”那顿饭她做得时间很长很长,饭还是做糊了,菜也忘记了放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