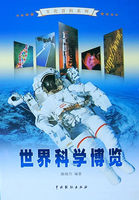第二天,晴雯真的死了。到了傍晚,宝玉祭完晴雯,正想返身回去,只听花影中有个人声,倒吓了一跳。细看不是别人,却是黛玉,满面含笑,口内说道:“好新奇的祭文!可与曹蛾碑并传了。”宝玉听了,不觉红了脸,笑着说:“我想着世上这些祭文都过于熟滥了!所以改个新样。原不过是我一时的玩意儿,谁知被你听见了。有什么大不了的,何不修改修改?”黛玉说:“原稿在哪里?倒要细细一读。长篇大论,不知说的是些什么,只听见中间两句:什么‘红绡帐里,公子情深;黄土陇中,女儿命薄’。这一联意思却好,只‘红绡帐里’未免俗些。放着现成的真事,为什么不用?”宝玉忙问:“什么现成的真事?”黛玉笑着说:“咱们如今多是霞影纱糊的窗格,何不就说‘茜纱窗下,公子多情’呢?”宝玉听了,不觉羞愧地说:“好极!到底是你,想的出说的出。可知天下古今现成的好景好事太多,只是我们愚人想不出来罢了。但只一件:虽然这一改新妙之极,却是你在这里住着还可以,我实不敢当。”说着,又连说:“不敢。”黛玉笑着说:“为什么?我的窗即可为你的窗,何必如此分析,也太疏了。古人异姓陌路,尚能互相救助而无憾,何况咱们?”宝玉笑着说:“论交,不在肥马轻裘,即黄金白璧亦不能与锱铢相比。倒是这唐突闺阁,万万使不得的。如今我索性将‘公子’、‘女儿’改去,竟算是你诔她的倒妙。况且素日你又待她甚厚,今宁可弃了这篇文,万不可弃此‘茜窗’新句,莫若改作‘茜纱窗下,小姐多情;黄土陇中,丫鬟薄命。’如今一改,虽对我没什么,我也惬怀。”黛玉笑着说:“她又不是我的丫鬟,怎么能这么说?况且小姐丫鬟亦不典雅,等我的紫鹃死了,我再如此说,还不算迟呢。”宝玉听了,忙笑着说:“这是何苦又咒她。”黛玉笑着说:“是你要咒的,不是我说的。”宝玉说:“我又有了,这一改就恰当了。不如说:茜纱窗下,我本无缘;黄土陇中,卿何薄命!”
黛玉听了,斗然变色,心中虽有无限的狐疑,外面却不肯露出,反连忙含笑点头称妙,说:“果然改得好。再不必乱改了,快去干正经事吧。刚才太太打发人叫你,明儿一早到大舅母那边去呢。你二姊姊已有人家定准了,说是明日那人来叩头,所以叫你们过去呢。”宝玉说:“何必如此忙?我身体也不大好,明儿还未必能去呢。”黛玉说:“又来了,我劝你把脾气改了罢。一年大得一年了……”一面说话,一面咳嗽起来。宝玉忙说:“这里风冷,咱们只顾呆站着,凉着可不是玩的,快回去吧。”黛玉说:“我回家去歇息了,明儿再见吧。”说着,便径自走了。宝玉只得闷闷地转步,又忽想起黛玉无人随伴,忙令小丫头子跟送回去。自己到了怡红院中,果然王夫人打发老妈妈来,吩咐他明日一早到贾赦那边去,和刚才黛玉说得一样。
原来贾赦已将迎春许与孙家了。这孙家乃是大同府人氏,祖上军官出身,乃当日宁荣府中的门生,算来也是世交。如今孙家只有一人在京,现袭指挥之职,此人名叫孙绍祖,生得相貌魁梧,体格健壮,弓马娴熟,应酬权变,年纪未满三十,且又家资富足,现在兵部候缺提升。因未曾娶妻,贾赦见是世交子侄,且人品家当多相称合,遂择为东床娇婿。亦曾回告贾母,贾母心中却不大称意,但想儿女之事自有天意,况且他是父亲做主,何必出头多事,因此只说“知道了”三字,并不多说。贾政又很讨厌孙家,虽是世交,不过是他祖父曾仰慕宁荣之势,有不能了结之事,才拜在门下的,并非诗礼名族之裔,因此倒劝过两次。无奈贾赦不听,也只得罢了。
宝玉却从未见过这孙绍祖一面的,次日只得过去聊以塞责。只听见那娶亲的日子甚急,不过今年就要过门的,又见邢夫人回了贾母,将迎春接出大观园去,越发扫兴。每日痴痴呆呆的,不知作何消遣。又听说要陪四个丫头过去,更不高兴地说:“从今后这世上又少了五个清洁人了。”因此天天到紫菱洲一带,徘徊瞻顾,见其轩窗寂寞,屏帐倏然,不过只有几个该上夜班的老婆子。再看那岸上的蓼花带叶,池内的翠荷香菱,也大部分摇摇落落,好像有怀念故人的样子,但不能与那些美妙女子可比,所以情不自禁,于是出口吟唱:
池塘一夜秋风冷,吹散菱荷红玉影。蓼花菱叶不胜悲,重露繁霜压纤梗。不闻永昼敲棋声,燕泥点点语棋枰,古人惜别怜朋友,况我今当手足情!
宝玉刚才吟罢,忽然听到背后有人笑着说:“你又发什么呆呢?”宝玉忙回头,见是香菱,便转身笑问:“我的姊姊,你这会子跑到这里来做什么?许多日子也不进来逛逛。”香菱拍手,笑嘻嘻地说:“我何曾不要来,如今你哥哥回来了,哪里比原来自由自在的了。刚才我们奶奶让人找你凤姐去,竟没有找着,说往园子里来了。我听见了这话,就讨了这个差进来找她。遇见了她的丫头说在稻香村呢,如今我找她去,谁知又遇见了你,袭人姊姊这几日可好?怎么忽然晴雯姐姐死了,到底是什么病?二姑娘搬出来的好快,你瞧瞧这地方一时间就空落落的了。”宝玉只有一味答应,又让她同到怡红院喝茶。香菱说:“此刻可不能,等我找到琏二奶奶,说完了正经事再来。”宝玉说:“什么正经事这么忙?”香菱说:“为你哥哥娶嫂子的事,所以要紧。”宝玉说:“正是。说的到底是哪一家的?只听吵嚷了这半年,今儿说张家的好,明儿又说李家的好,后日又议论王家的好。这些人家的女儿,他也不知犯了什么罪,叫人好端端地议论。”香菱说:“如今定了,已不用乱扯别家了。”宝玉问:“定了谁家的?”香菱说:“因你哥哥上次出门时,顺路到了个亲戚家去。这门亲原是老亲,且又和我们同在户部挂名行商,也是数一数二的大门户。前日说起来时,你们两府都也知道的。全京城里,上至王侯,下至买卖人,都称他家是桂花夏家。”宝玉忙笑着说:“如何又称为‘桂花夏家’?”香菱说:“他家本姓夏,非常的宝贵。其余田地不用说,单有几十顷地独种桂花。凡这长安城里城外的桂花局都是他家的,连宫里一应陈设盆景也是他家供奉,因此才有这个称号。如今太爷也没了,只有老奶奶带着一个亲生的姑娘生活,也并没有哥儿兄弟,可惜他们竟一门尽绝了后。”宝玉忙问:“咱们也别管他绝后不绝后,只是这姑娘可好?你们大爷怎么就中意了?”香菱笑着说:“一则是有缘,二来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当年时又是通常来信,从小都在一处玩过。叙亲又是姑舅兄妹,又没嫌疑。虽离了这几年,前天一到她家,他们夏奶奶又是没儿子的,一见了你哥哥出落得这么样,又是哭又是笑,竟比见了儿子还亲热。又令她兄妹相见,谁知这姑娘出落得花朵儿似的了,在家里也读书写字,所以你哥哥当时就一心看准了。连当铺里伙计们一群人也遭扰了人家三四日,他们还留多住几日,好容易推辞才放回家。你哥哥一进门,就咕咕唧唧求我们太太去求亲。我们太太原是见过的,又见门当户对,也依了。和姨太太、凤姐姐商议了,打发人去一说就成了。只是娶的日子太急,所以我们忙乱得很,我也巴不得早些娶过来,又添一个做诗的人了。”宝玉冷笑着说:“虽然这么说,但我倒替你担心虑后呢。”香菱说:“这是什么话!我倒不懂了!”宝玉笑着说:“这有什么不懂的,只怕再有个人来,薛大哥就不肯疼你了。”香菱听了,不觉红了脸,正色说:“这是怎么说?素日咱们都是斯文相敬的,今日忽然提起这些事,怪不得人人都说你是个亲近不得的人。”一面说,一面转身走了。宝玉见她这样,便怅然若有所失,呆呆地站了半天,只得没精打采,还入怡红院来。
一夜也没安睡,种种头绪困扰。次日便懒进饮食,身体发热。也由于近日抄检大观园,逐司棋、别迎春、悲晴雯等羞辱惊恐悲凄事所致,兼以风寒外感,所以竟然病了,卧床不起。贾母听得如此,天天亲来看视。王夫人心里后悔,不该因晴雯过于逼责了他。心中虽如此,脸上却不露出。只吩咐众奶奶等,小心服侍看守,一日两次带进医生来诊脉下药。一月之后,方渐渐的痊愈。贾母命好生保养,过一百日方许动荤脂油面等物,方许出门行走。这一百日内,连院门都不许到,只在屋里玩笑。四五十天之后,就把他拘得火星乱迸,哪里忍耐得住?虽百般请求,无奈贾母、王夫人等执意不从,也只得罢了,因此和那些丫头们无所不至,恣意耍笑。又听得薛蟠那里摆酒唱戏,热闹非常,已娶新人入门,听说这夏家小姐长得十分俊俏,也略通文墨,宝玉恨不得就过去见一见才好。再过些日子,又听说迎春出了阁。宝玉思及当时姊妹情深,从今一别,纵然相逢,也不似从前那等亲密了。眼前又不能去一望,真令人凄惨伤心。少不得潜心忍耐,暂同这些丫鬟们厮闹解闷,幸免了贾政责备,逼迫读书之难。这百日,只不曾拆毁了怡红院,和这些丫头们无法无天,凡世上所有之事全玩耍出来。
香菱自那日回敬了宝玉之后,心中认为宝玉有心讽刺,从此倒要远避他才好,因此以后连大观园也不轻易进来了。日日忙乱着,薛蟠娶过亲自以为得了护身符,自己身上分去责任,到底比这样安静些;二则又知道新娘是个有才有貌的佳人,自然是典雅和平的,因此他心里盼过门的日子,比薛蟠还急十倍,好容易盼得一日娶过来,她便十分殷勤,小心服侍。
原来这夏家小姐今年方一十七岁,长得挺漂亮,也认得几个字。若问心里的计划胆量,与王熙凤很像。只吃亏一件,从小父亲去世得早,又无同胞弟兄,寡母独守此妇,娇养溺爱,不啻珍宝。凡女儿一举一动,她母亲皆百依百顺,因此未免变得目空一切盛气凌人。自己尊若菩萨,窥他人秽如粪土;面如桃花心似青蝎。在家里和丫鬟们使性赌气,轻骂重打的。今日出了闺,自认为要做当家的奶奶,比不得做女儿时腼腆温柔,要拿出些威风来才压得住人。况且见薛蟠气质刚硬,举止骄奢,若不趁热打铁,一气呵成,将来必不能降得住他;又见有香菱这等才貌双全的爱妾在室,越发添了宋太宗灭南唐之意。因她家多桂花,她小名就唤作金桂。她在家时,不许人嘴里说出“金”、“桂”二字来,凡有不留心误嘴里一字者,她便定要苦打重罚才罢。她因想“桂花”二字是禁止不住的,须得另换一名,想桂花曾有广寒嫦娥之说,便将桂花改为“嫦娥花”,又寓自己身份。
如今薛蟠本是个喜新厌旧的人,且是有酒胆无饭力的,如今得了这样一个妻子,正在新鲜兴头上,凡事未免谦让她些。那夏金桂见了这种情况,更加得寸进尺。一月之中,二人气概还差不多。至两月之后,便觉薛蟠的气概渐渐地低矮了下去。
一日薛蟠醉后不知要办什么事,先与金桂商议。金桂执意不从,薛蟠便忍不住骂了几句话,赌气自行办了。金桂便哭得如醉人一般,茶汤不进,装起病来,请医调治。医生又说:“气血相逆,当进宽胸顺气之剂。”薛姨妈恨得骂了薛蟠一顿,说:“如今娶了亲,眼前就抱儿子了,还是这样胡闹。人家凤凰似的,好容易养了一个女儿,比花朵还轻巧,原来当你是个人物,才给你做老婆。你不说收敛些,安分守己,一心一意和和气气地过日子,还是这样胡闹,灌了黄汤,折磨人家。这会子花钱吃药,白操心。”一席话说得薛蟠后悔不及,反来安慰金桂。金桂见婆婆如此说,更加猖狂,更装出些花样来,总不理他。薛蟠没了主意,惟有自叹而已,好容易十天半月之后,才渐渐地哄转过金桂的心来。自然更加小心,不免气概又矮了半截。那金桂见丈夫旗橐渐倒,婆婆良善,也就渐露锋芒。开始不过挟制薛蟠,后来倚娇作媚,将及薛姨妈,后来又欺侮宝钗。宝钗早已发觉她的不轨之心,每随机应变,暗以言语压制她。金桂知其不好对付,多次想寻找应对的语言,但都没有找到,只得顺其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