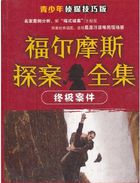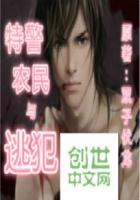宝玉说:“我不是要咒她,今年春天已有兆头的。”袭人忙问何如,宝玉说:“这阶下好好的一棵海棠花竟无故死了半边,我就知道有坏事,果然应在她身上。”袭人听了又笑起来,于是说:“我如果不说,又憋不住。你也太婆婆妈妈的了,这样的话,岂是你读书人说的?草木怎么又与人联系起来了呢?”宝玉叹着说:“你们哪里知道,不但草木,凡天下有情有理的东西,也和人一样,得了仙气便极有灵验的。若用大题目比,就是孔子庙前的松、坟前的蓍草,诸葛祠前的柏,岳武穆坟前的松,这都是堂堂正大之气,千古不朽之物,世乱则枯萎,世治则繁荣,几千百年之枯而复生者几次,这难道不是兆应?若是小题目比,也有杨太真沉香亭的木芍药,端正楼的相思树,王昭君坟上的长青草,难道不也有灵验?所以这海棠亦是应着人生的。”
袭人听了这篇痴话,又可笑又可叹,于是笑着说:“这话真正更让我生气了。那晴雯是个什么东西,就费这样心思比出这些正经人来!还有一说,她总不按次序。便是这海棠也该先来比我,也还轮不到她。想是我要死的了。”宝玉听说,忙捂她的嘴,劝道:“这是何苦!一个未弄清;你又这样。罢了,再别提这事,别弄得去了三个又饶上一个。”袭人听说,心里暗喜着想:“若不如此,也没个结果。”宝玉又说:“我还有一句话要和你商量,不知你肯不肯?现有的她的东西是瞒上不瞒下,悄悄的打发人送给她去。再或有咱们常日积下的钱,拿几吊出来给她养病,也是你姊妹好了一场。”袭人听了,笑着说:“你太把我们看得小器又没人心了。这话还等你说,我早就把她的衣裳各物打点下了,都放在那里。如今白日里人多眼杂,又恐生事,且等到晚上,悄悄地叫柳妈给她拿去。我还有穿下的几吊钱也给她去。”宝玉听了,点点头儿。袭人笑着说:“我原是久已出名的贤人,连这一点子好名儿还不会买去不成!”宝玉听了她刚才说的,又赔笑抚慰她,怕她伤心。一时趁空,宝玉将一切人稳住,独自抽空到园子后角门,央求一个老婆子带他到晴雯家去瞧瞧。开始这婆子百般不肯,只说怕人知道“回了太太,我还吃饭不吃!”无奈宝玉死活央告,又许她些钱,那个婆子才带了他去。
这晴雯当年是赖大买的,还有个姑舅哥哥叫做吴贵人,都叫他贵儿。那时晴雯才十岁,时常赖妈妈带她进来。贾母见了喜欢,故此赖妈妈就孝敬了贾母。过了几年,赖大又把贵儿也收买进来,给他娶了一房媳妇。谁知贵儿生性胆小老实,那媳妇却倒伶俐,又兼有几分姿色,看着贵儿无能力,便每日打扮的妖妖艳艳,两只眼水汪汪的,招惹的赖大家人如蝇逐臭,渐渐做出些风流事来。
那时晴雯已在宝玉屋里,他便央告晴雯转求凤姐和赖大老婆要求过来住,目前两口儿就在园子后角门外居住,伺候园中买办杂差。这晴雯一时被撵出来,住在他家,那媳妇哪里有心肠照管,吃了饭便自己去串门子,只剩下晴雯一人,在外面屋内趴着。宝玉命那婆子在外了望,他独自掀起布帘进来,一眼就瞧见晴雯睡在一领芦席上。幸而被褥还是旧日铺盖的,心内不知自己怎么说才好,于是上来含泪伸手轻轻地拉她,悄悄地叫两声。这时晴雯又因着了风寒,受了她哥嫂的讥讽,病上加病,嗽了一日才朦胧睡着。忽然有人唤她,强睁双眼,一见是宝玉,又惊又喜,又悲又痛,一把死攥住他的手,哽咽了半天,才说:“我只当今生不能见你了。”一句话未了,便嗽个不住,宝玉也只有哽咽无语。晴雯说:“阿弥陀佛,你来得很好,快把那茶倒半碗我喝。渴了半日,叫个人也叫不着。”宝玉听说,忙擦着眼泪问:“茶在哪里?”晴雯说:“在炉台上。”宝玉看到,虽有个黑沙吊子,却不像茶壶。只得桌上去拿一个碗,未到手内,先闻油膻之气。宝玉只得拿了来,先拿些水洗了两次,又用自己的绢子擦干了。闻了闻,还有些气味,没奈何,提起沙壶斟了半碗。看时,绛红的颜色,也不大像茶。晴雯扶着枕头说:“快递给我喝一口罢!这就是茶了,哪里比得上咱们的茶呢!”
宝玉听到这里,自己先尝了一口,并无茶味,咸涩不堪,只得递给晴雯。只见晴雯如得了甘露一般,一口都灌下去了。宝玉看着眼泪直流下来,连自己都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了。一面说:“你有什么说的,趁着没人告诉我。”晴雯呜咽着说:“有什么可说的!不过挨一刻是一刻,挨一日是一日,我也知道,最多再过个三五天,我就不行了。只是一件,我死也不甘心,我虽生的比人略好些,并没有私情勾引你。怎么一口死咬定了我是狐狸精!我今日既已担了虚名,况且没多长时间了,不是我说句后悔的话,早知如此,我当日……”说到这里气往上涌便说不出来,两手已经冰凉。宝玉又痛又急又害怕,便歪在席上,一只手攥着她的一只手,轻轻地给她捶打着,又不敢大声叫,真如万箭攒心。两三句话时,晴雯才哭出来。
宝玉拉着她的手,只觉瘦如枯柴,腕上还带着四个镯子,于是说:“拿下来,等好了再带上罢。”又说:“可惜这两个指甲,好容易长了二寸长,等这病好了,又损了好些。”晴雯擦了擦泪,把好手用力缩回,搁在口边,狠命一咬。只听“咯吱”一声,把两根葱管一样的指甲齐根咬下,拉了宝玉的手,将指甲搁在他的手里;又回手挣扎着,连揪带脱在被窝里把贴身穿的一件旧红绫袄子脱下,递给宝玉,不想虚弱透了的人哪里禁得这么抖拨,早喘成一处了。宝玉见她这般已经会意,连忙解开外衣,将自己的袄褪下来盖在她身上,却把这件穿上。来不及系扣钮子,只用外头衣裳掩了。刚系腰时,只见晴雯睁眼说:“你扶我起来坐坐。”宝玉只得扶她,哪里扶得起?好容易欠起半身,晴雯伸手把宝玉的袄儿往自己身上穿。宝玉连忙给她披上,拖着胳膊伸上袖子,轻轻放倒,然后将她指甲装在荷包里。晴雯哭着说:“你去吧,这里你怎么受得?你的身子要紧。今日这一来,我就死了,也不枉担了虚名!”
正说话间,只见她嫂嫂笑嘻嘻地掀帘进来,说:“好呀,你两个的话,我都听见了。”又问宝玉说:“你一个做主子的,跑到下人房里来做什么?看我年轻又俊,是来调戏我么?”宝玉听说,吓得忙赔着笑说:“好姊姊,快别大声的,她服侍我一场,我私自来看看她。”那媳妇点着头笑着说:“怨不得人家都说你有情有义的。”便一手拉了宝玉进里间来,笑着说:“你要不叫我嚷,这也容易,你只是依我一件事。”说着,便自己坐在炕沿上,把宝玉搂在怀中,紧紧地将两腿夹住。宝玉哪里见过这个,心内早突突地跳起来了,急得满脸涨红,身上乱战,又羞又愧,又怕又恼,只说:“好姊姊,别闹!”那媳妇斜了醉眼儿,笑着说:“呸!整天听见你在女孩儿们身上做工夫,怎么今日就假装起来了?”宝玉红了脸,笑着说:“姊姊撒开手,有话咱们慢慢地说。外头有老妈妈,听见什么意思呢!”那媳妇哪里肯放,笑着说:“我早进来了,已经叫那婆子在园门口儿等着呢。我等得这么辛苦,今日才等着了,你要不依我,我就嚷起来,叫里头太太听见了,我看你怎么样。你这么个人,只这么大胆子儿!我刚才进来了好一会子,在窗外细听,屋里只你两个人,我原以为有些羞耻话儿。这么看起来,你们俩个竟还是两不相扰儿呢,我可不能像她那样傻。”说着,就要动手。宝玉急得死往外拽。
正闹着,只听窗外有人问:“晴雯姐姐是在这里住吗?”那媳妇也吓了一跳,连忙放了宝玉。这宝玉已经吓呆了,听不出声音。外边晴雯听见她嫂子缠磨宝玉,又急又臊又气,一阵虚火上攻,早昏厥过去。那媳妇连忙答应着,出来看不是别人,却是柳五儿和他母亲抱着一个包袱。柳妈拿着几吊钱,悄悄地问那媳妇说:“这是里头花姑娘叫拿出来给你们姑娘的。她在哪间屋里呢。”那媳妇笑着说:“就是这屋子,哪里还有屋子?”那柳妈领着五儿便匆匆往外走。谁知五儿眼光早已见是宝玉,便问他母亲说:“刚才袭人姐姐不是悄悄地找宝二爷吗?”柳妈说:“嗳哟,可是忘了,方才老宋妈说见宝二爷出角门来了,门上还有人等着要关园门呢。”因回头问那媳妇儿。那媳妇儿自己心虚,便说:“宝二爷哪里肯到我们这屋里来了?”柳妈听说便要走。这宝玉一则怕关了门,二则怕那媳妇进来又缠,也顾不得什么了,连忙掀了帘子出来,道:“柳嫂子,你等等我,一块走。”柳妈倒吓了一大跳,说:“我的爷,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那宝玉也不答言,一直快步走。那五儿说:“妈妈,你快叫住二爷不用忙,留神冒冒失失叫人碰见,倒不好。况且才出来时,袭人姐姐已经打发人留了门了。”说着,连忙同他妈来赶宝玉。这里睛雯的嫂子干瞅着没办法。
宝玉跑进角门,才把心放下来,还是突突地乱跳。又怕五儿关在外头,眼巴巴瞅着他母女也进来了。远远听见里边妈妈们正查人,若再迟一步就关了。宝玉进入园中,且喜无人知道。到了自己房里告诉袭人,只说到薛姨妈家去就罢了。一时铺床,袭人不得不问:“今日怎么睡?”宝玉说:“不管怎么睡都行。”原来这一二年间袭人因王夫人重视她,越发自要尊重。凡背人之处或夜晚之间,总不与宝玉接近,较先前幼时反倒疏远了。虽无大事办理,然一应针线并宝玉及诸小丫头出入银钱衣履杂物等事,也甚烦琐;且有失血之症,故近来夜间总不与宝玉同房。宝玉夜间胆小,每醒肯定要喊人。因晴雯睡卧警醒,故夜晚一应茶水起坐呼唤之任都交给了她一人,所以宝玉外床只是晴雯睡。她今去了,袭人只得将自己铺盖搬来设于床边。
宝玉发了一晚上呆。等他睡下,袭人等也睡下,听着宝玉在炕上长吁短叹,翻来覆去,直至三更以后,方渐渐地安顿了。袭人才放心,也就朦胧睡去。没半杯茶功夫,只听宝玉叫“晴雯”。袭人忙连声答应,问做什么。宝玉因要喝水。袭人忙下去倒了半盏茶来,宝玉笑着说:“我近来叫惯了她,却忘了是你。”袭人笑着说:“她乍来时,你也曾睡梦中叫我,以后才改了。”说着,大家又睡下。
宝玉又翻转了一个更次,至五更方睡去时,只见晴雯从外头进来,仍是往日形景,向宝玉说:“你们好生过罢,我从此就永别了。”说完,返身便走。宝玉忙叫时,又将袭人叫醒。袭人还只当他习惯了乱叫,却见宝玉哭了,说:“晴雯死了。”袭人说:“这是哪里的话!叫人听着什么意思?”宝玉哪里肯听,巴不得一时亮了就遣人去问信。
天刚亮,就有房里小丫头叫开前角门传王夫人的话:“‘即时叫起宝玉,快洗脸换了衣裳来。因今日有人请老爷赏菊花,老爷因喜欢他前日做的诗好,故此要带了他们去。’这多是太太的话,你们快告诉去,让他快来。老爷在上房里等着他们喝茶呢。环哥儿早来了,快快儿的走罢,我去叫兰哥儿去。”里面的婆子听一句应一句,一面系扣子,一面开门。袭人听得叩院门,便知有事,忙命人问时,自己就起来了。听得这话,忙催人来舀洗脸水,催宝玉起来梳洗,她赶忙去取衣服。因思跟贾政出门,便不拿出十分出色的新鲜衣履来,只拣那三等成色的来。
宝玉此时也没办法,只得忙上前面来。果然,贾政在那里喝茶,十分喜悦。宝玉请了早安。贾环、贾兰二人也都见过宝玉。贾政命坐下喝茶,向环兰二人说:“宝玉读书不如你两个。论题联和作诗这种聪明,你们皆不及他。今日此去,未免叫你们做诗,宝玉须找机会帮助他们两个。”
王夫人从来不曾听见贾政说这等话语,真是喜出望外。一时,等他父子去了,正想到贾母这边来时,就有芳官等三个人的干娘走来,回答说:“芳官自前日,蒙太太恩典赏了出去,她就疯了似的,茶饭都不吃,勾引上藕官、蕊官,三人寻死觅活,只要铰了头发做尼姑去。我只当是小孩子家,一时出去不惯,也是有的,不过隔两天就好了。谁知越闹越凶,打骂她们也不怕,实在没法。所以来求太太,或是就依她们做尼姑去,或教导她们一顿,赏给别人做女儿去罢,我们没这福。”王夫人听了,说:“胡说!那里由得她们?佛门也是轻易进去的?她们每人打一顿,看还闹不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