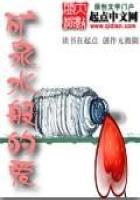2008年的大事太多,我这里只说小事。
“小事”之“小”,总是相对于“大事”之“大”而言的;我们习惯了认为“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的思维习惯,所以常常把“小事”与“个人的事”联系在一起。比如,这一年的元月我就开始写我的《三十年间有与无》,这当然是很小的事,之所以到现在还没有刊登完,就是因为这一年的“大事”太多:自然灾害、人为破坏、两会召开、十七大、奥运会,每遇大事,小曹都不得不满怀歉疚地说:
对不起,一切都得让路,你的连载不得不暂停……我自然是个通晓事理的人,不但欣然应允,而且也不得不满怀歉疚地说:知道,我懂,让你受累了……既然是小事,就要把它当成很小的事来看。在今年2月上半期的《社会科学论坛》上有张宝明的一篇文章:《“思想”能决定“尊严”
吗?》,说潘光旦先生曾用四个英语中的“S”来总结自己的后半生,这就是surrender(投降)、submit(顺从)、survive(幸存)、succumb(死掉)。这四个“S”让我沉思良久,久久不能释怀,尽管它真是一件仅属于潘光旦个人的小事。后来,我读《布罗茨基谈话录》,知道他早年《布罗茨基谈话录》,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
因“不劳而获罪”被判刑、流放,1972年被驱逐出境,198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今天的圣彼得堡,在他的故居前有巨大的大理石纪念牌。他也说,回想起来,当初在苏联流放时,竟是他生命中最好的时期之一;而到了美国后,生命中的一切对他来说“不是为了生活,而是为了过完余生”,因为“我们这些年纪上的人,自主或不自主地就已经是定型的生物了。基础、起跑——都发生在祖国。我们在俄国的存在是原因。今天所获得的是结果。”我同意他们的话,不管是四个“S”也好,还是“过完余生”也好,个人的事不过如此。
也还有些并不完全属于个人的事,但也一定会被划归“小事”之列,比如《“华南虎”为什么跑不过“范跑跑”》(6月24日《新华每日电讯》的一则标题),比如《摄像头时代,我们如何生存》(6月25日《东方早报》的一则标题)的问题,还有贵州一位名叫杨贤祥的农村代课教师,办学二十二年,年薪三百六十五斤包谷(7月31日《新华每日电讯》)等等。进入今年“流行语榜单”的还有“飞机集体返航”、“京剧进校园”、“限塑令”、“周老虎”、“许霆案”、“中华文化标志城”等等,与今年的诸多大事比较起来,自然也是小事,恐怕能记得的人已经不多了。至于挪用公款四亿六千万元的双钱股份董事长范宪,受贿一千多万、挪用一千多万的吉粮集团董事长兼党委书记刘宪鲁被人遗忘更在情理之中,因为这样的事毕竟太多了。
但我特别关注的是两件“国家小事”:一是原美国援军第十四航空队(飞虎队)成员唐纳德·克尔的座机在被日军击落后,他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被一位年仅十四岁的中国少年李石救起,藏在深山密林中,躲过了日军的搜索。克尔1977年逝世,2005年,克尔的儿子戴维找到了李石老人,还有另一名当年参与营救的邓斌;两个月后,戴维再次带着他的妻子、女儿前来拜访这两位老人,当面向两位老人的救命之恩表示感谢,说克尔最后的遗言就是“我们爱和平”。但此时的李石已经失忆,对当年的事全然不记得了;邓斌也已八十七岁,垂垂老矣,并不知道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当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一幕时,禁不住热泪盈眶,忽然间对“感恩”和“失忆”这两个似乎全然无关的词语有了全新的理解。因为在大讲“感恩”的日子里,我真的想到了生理功能上的“失忆”或广义的“失忆”:在以后的岁月里,不知还会有多少人在失忆后,才会被人想到感恩;而这些事与人,是今天的我们所不可能知道的。
再一件事更小,但也是国家大事,这就是中国驻大阪的领事代表8月7日首次出席了广岛原子弹爆炸纪念仪式。这件事很小,小到在报纸上只有一行字,而且我们也不知道驻大阪的领事代表是谁、去了几个人、有些什么活动。但这件事却与上面那件事连在一起,让我们超越了战争的对错、正义与非正义而想到了对生命的珍重。差不多同一天的报纸上还有一条小消息,这就是罗马教皇本笃十六祝愿北京奥运成功,说他一直“满怀情意地关注着北京”,希望奥运能展现人间的友爱与和平。
我希望在这样的祈祷声中揭过2008让人永世难忘的一页。
奥运会前的5月19日下午2时28分,汽笛长鸣,行人肃立,全国下半旗向汶川地震死难者致哀,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小事”;我之所以也想把它列为“小事”,是为了让大家在都记得那些大轰大嗡、惊天动地、举国欢庆的“大事”的同时,也不要忘记在这短短的三分钟里,我们都曾低下了自己高傲的头颅。
6月4日,无事之中,看到舒芜过去的一首诗,就擅自改动,变成自己的抒怀:
不信唯物不参禅;
也尽人为也信天;
无泪可挥无话说,
有鬓已白有喟然。
5日,《书城》有一茶座,在咖啡室聊天,吴亮、王安忆、蔡翔、陈子善、郜元宝、张生、贺圣遂、邓正来、邓安庆以及《书城》的几位主要人物都来了,这种形式在上世纪80年代曾出现过,想不到差不多二十年后“死灰复燃”,同仁学者们又开始在一起“清谈”;不过80年代时大家的精神意向大体一致,而现在则分歧很大,那时都很认真,现在则多了些调侃与幽默。大家都在适应新的相处方式。约定了让我主讲一次《普世价值与当代中国》,我自然也很高兴,觉得某种小型的公共活动空间正在形成。
还有一件小事也应该记下:6月30日,上海大学举办第三届“文学周”活动,纪念汶川地震,捐书捐款,还举办了晚会,让我听到了赵长江、阎连科、孙甘露、王安忆、李锐、蒋韵等人的诗朗诵和即席演讲,特别是梁波罗和狄菲菲两位专业演员的朗诵更是把晚会推向了高潮。
就这样,在我的心目中,2008就算过去了。
1978到2008是三十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七届三中全会也是三十年,有许多的机构和个人在记录着这三十年的大事,我,恐怕就只能说这些了。
青年时代的诗人奥登在生命即将结束时说,我所写下的反希特勒的东西没有挽救一个犹太人,我的诗句也没有令战争提前一分钟结束,我有什么用?布罗茨基有些忧郁地回答说,让我们把眼光放远,延伸到世界的极限,在那里,你就会发现诗人的语言,他的发言吐字,他的思维方式,就可能间接地改变世界。因为当时的人还不可能意识到,总有人在用自己的语言取代官方的、政府的语言,就如现在的意大利人使用的是但丁的语言而不是教皇或皇帝党的政论语言一样。他说:“国家所使用的语言在很多方面都不是俄语。这种语言被强烈地德意志化了,被世纪初马克思论文的行话、被列宁与考茨基的争论所污染,等等。这种社会民主纲领论争的行话,突然成为接近政权的人们的用语。……掌管中央机关的人开始带着成见和怀疑观察运用另一种词汇的人,需要证明他不是一头骆驼。……但今天的俄罗斯人不用社论的语言说话。我认为他们不那样讲话。苏维埃政权可以为所有方面而得意洋洋,除了一点——语言。”
下来,就该看奥运开幕式了,让我们看看那该是一种什么样的语言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