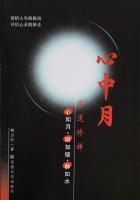入世关怀主要是相对于出世解脱而言的,是对现实人生价值的肯定和对现世生活、现世事业的关注和参与。中国佛学面向社会人生和关注、参与现实社会人生的入世关怀是与其肯定人和人生价值的人本观念密切相联的,同时它也是中国佛学人文精神的现实体现。正是在肯定人和人生价值的基础上,中国佛教进一步强调了“出世不离入世”,反对离开现实的社会人生去追求出世的解脱。就中国佛学入世关怀形成的总体发展过程而言,中国佛学继承了老庄玄学的体用论主题,在大乘佛教般若中观学说和佛性如来藏思想的基础上阐发了“即体即用”、“体用一如”、“理事无碍”、“事事无碍”等观念,为中国佛教面向现实社会人生、关注现实社会人生提供了理论依据。而禅宗突出心性的觉悟,将修行融于运水搬柴、穿衣吃饭的平常日用中,则体现了中国佛教对世俗生活价值的肯定,同时也确立了中国佛教将修行实践融入世俗生活的特征。在禅宗“即世间求解脱”的修行观基础上,近代佛教发展起来的人间佛教思潮,则进一步将关注现实社会人生的入世关怀推到一个新的高度,改良社会、利益人群、建设人间净土的入世的事业成了人间佛教关注的重要方面。这样,中国佛教在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下通过哲学上由无主体向有主体的过渡而日益获得了一种面向社会人生、肯定人和人生价值的人本观念,并在此基础上,一步步走向了现实的社会人生。立足于“众生”(指人及一切有情识的生物)永超苦海的印度佛教在中国则转向了对“人”的随缘任运、当下解脱的强调,转向了改良社会、利益人群的入世关怀。
一、“体用一如”入世关怀的理论依据
印度佛学自传入中国之始,即面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入世观念的挑战,也从一开始就走上了面向现实社会人生的旅程。无论是最初的佛经翻译对儒家伦理观的迎合,还是僧肇对魏晋玄学体用论主题的承续,无论是《大乘起信论》“一心开二门”的理论构建,还是华严宗“理事无碍”、“事事无碍”的法界观,其中对世俗伦常的肯定,对现世之用的认可,对现象世界、现实事物之间联系的关注,都体现了中国佛学面向现实社会人生的趋向,并为禅宗“不离世间求解脱”的修行观,为近代佛教倡导的救国救世的入世主张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思想基础。
佛学从其在印度产生之日起就具有“出世”的特征。释迦牟尼为了寻求人生痛苦的解脱而放弃王位,抛妻别子,他组织的僧团也过着与世俗完全不同的生活。解脱人生痛苦,体证涅盘寂静,这是佛教的根本追求。大乘佛教出于自利利他、度化众生的理想,主张顺应众生的不同根性,对现实人生有一定程度的关注,主张将出世与入世统一起来。大乘佛教“世间出世间不二”的观念,为中国佛学面向现实社会人生提供了理论前提。中国佛学理论中的“即体即用”、“体用一如”、“理事无碍”、“事事无碍”等观念,从根本上说,是从中国传统哲学体用论的角度对印度大乘佛学“世间出世间不二”、“生死涅盘不二”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佛教对解脱的根本追求及其独特的修行和生活方式,在传入中土之初,曾遭到具有鲜明人文精神的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抵制。为了能够在中土社会文化环境生存发展,佛教非常注重吸收融合传统思想文化的入世观念,这主要体现在它对儒家思想观念的妥协和吸收融合上。例如在佛经翻译方面十分注意对以儒家名教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传统社会伦理的迎合;面对儒家的种种攻击,佛教徒或者通过把佛教的“五戒”与儒家的“五常”相比配等来说明儒佛一致,或者在佛教的思想体系中加入忠孝仁义等儒家的内容以调和儒佛的分歧,而更多的则是以社会教化作用的相同来强调儒佛的互为补充,可以并行不悖。“出世”的佛教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逐渐融入了重视现实人生的品格。魏晋南北朝时期,慧远、僧肇、竺道生等的佛学思想都带有鲜明的融合印度佛教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特征。在这里,我们试以僧肇“即体即用”的体用论为例来说明魏晋南北朝佛学面向现实社会人生的理论取向。
僧肇佛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是从印度大乘般若中观学说出发来阐释魏晋玄学的主题。僧肇的佛学不仅阐述了魏晋玄学的有无论、动静观、认识论,而且还从“世间出世间不二”的思想出发阐发了魏晋玄学的体用论。体用论是魏晋玄学的重要理论,它不同于西方哲学意义上的本体论,而兼有世界观、境界论、工夫论、人生观等方面的内涵。从境界论、人生观的角度而言,所谓“体”主要是指内在的精神境界,或者说对世界本真存在状态的体认;所谓“用”则主要是指通过内在的精神超越确立的应对现实社会人生的生存智慧。在体用关系上,魏晋玄学一方面试图将体与用统一起来,另一方面又存在以体为本,以用为末,以体统用的思想倾向。魏晋玄学体用论体现了传统思想文化关注世间之用的入世特征。
汤用彤先生曾经指出:“肇公之学说,一言以蔽之曰:即体即用。”僧肇的体用论在《肇论》中有充分的体现。例如《般若无知论》以“虚不失照,照不失虚”来表达虚照不二的般若境界,又说“圣人空洞其怀,无识无知,然居动用之域,而止无为之境;处有名之内,而宅绝言之乡”。《涅盘无名论》则从“用即寂,寂即用”来表达“用寂体一”的涅盘境界。在对理想境界的表述上,僧肇在强调“虚”、“寂”的同时,突出了“照”、“用”的一面。应该说,僧肇关于“体用不二”的观念,主要是从般若中观思想出发的,是对大乘佛教“世间出世间不二”、“生死涅盘不二”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但就其试图将内在的精神超越与世间之用统一起来,试图在现实生活中体证超越的精神境界的思想意向来看,则与老庄玄学的人生追求相契合,体现了僧肇佛学对传统文化入世取向的肯定和认同,其从“照”、“用”角度对般若智慧和涅盘境界的阐释,具有明显的面向现实社会人生的理论趋向。
僧肇之后,体用论观念及思维模式对中国佛学有持续的影响,这充分体现在南朝梁代出现的《大乘起信论》及其对中国佛学的重要影响。《大乘起信论》究竟是译着还是中国学者的撰述,这在学术界仍有争议,但此论出现以后,对隋唐宗派佛学乃至整个中国佛学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却是不争的事实。《大乘起信论》从体相用三方面来阐释一心的内涵,认为众生心含摄一切世间出世间诸法,依于此心能够揭示大乘佛法的体相用。《大乘起信论》对“相用”及“觉”性的强调,是与传统文化关注现实人生之用的精神特性相契合的。《大乘起信论》的思想观念、思想结构和思维模式等对隋唐宗派佛学如天台、华严、禅等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例如天台宗“一念无明法性心”即是对《大乘起信论》“一心二门”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在它看来,十二因缘十法界为一念无明生起,世间与无明相即不二。同时,从本性上讲,十二因缘十法界因一念心起,又是即于空、假、中的,无明心也就是法性心。世间与法性的统一,为中国佛学肯定世间、肯定现实人生进一步铺平了道路。华严宗在体用不二、性相融通方面发展了《大乘起信论》的思想,它将《起信论》的体相用简化为理事、体用,而以法界为体,以缘起为用,将《起信论》的真如缘起论进一步发展为法界缘起论,在《大乘起信论》体用不二、理事无碍的思想基础上,进一步阐发了现象与现象之间的不一不异、相互贯通的关系,从而更突出了中国佛学关注现实世界、关注世间之用的入世特征。华严宗法界缘起论由理事无碍向事事无碍的递进,表明中国佛学经由体用论的过渡,进一步趋向对现象世界和现实人生价值的肯定。至此,中国佛学人文精神的理论构建也逐渐趋于完善。
二、“即世间求解脱”入世关怀之融入平常日用
前文提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具有很强烈的关注现实社会人生的人文精神。就入世关怀而言,则突出地表现在关注治天下的政治实践,重视维护社会等级秩序的道德伦常,以及肯定世俗生活的价值。佛教在适应中土社会文化环境的过程中,一方面论证佛教与传统思想文化并不矛盾,另一方面又注意依附政治力量,吸收融合传统思想文化的入世精神,肯定世俗伦常,注重发挥自身在劝世化俗、辅助王化中的作用。就佛教与政治的关系而言,中国佛教中出现了“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认识,将这种认识落实于具体践行,便表现为一些僧人直接参与现实的社会政治活动,利用佛教来为政治服务,同时也依赖统治者的支持来求得佛教的发展。例如释慧琳不仅参与政事,深得宋文帝的赏识,甚至还获得了“黑衣宰相”的称号。惠能的弟子神会在安史之乱以后积极设坛度僧收香水钱以助军需,为朝廷恢复两京立下汗马功劳,如此等等。从佛教与社会伦理的关系而言,则表现为对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的吸收融合,而这又突出地体现在对儒家孝亲观的吸收、融合与发挥。总体而言,禅宗六祖惠能之前,中国佛学的入世关怀还主要表现在理论论证和对社会政治、伦理的妥协调和上,还没有将修行实践拓展到现实的日常生活领域。真正将修行实践融入世俗生活的平常日用中,并形成广泛的社会影响,应该说是始自惠能南宗。惠能有句名言:“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外兔角。”强调了理想人生的实现不能脱离现实的人生,因此,他劝人“勿离世间上,外求出世间”,认为离开了世间,也就没有出世间。在把佛法和出世间拉向世间的同时,惠能还把遵奉世间法视为求得“出世间”的重要途径,甚至比“持戒”、“修禅”等更重要。他说:“心平何劳持戒,行直何用修禅;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让则尊卑和睦,忍则众恶无喧。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听说依此修行,天堂只在目前。”后世禅宗继承发展了六祖惠能奠定的入世修行、即世间求解脱的修行原则。例如神会就不止一次地指出:“若在世间即有佛,若无世间即无佛。”“不动意念而超彼岸,不舍生死而证泥洹。”大珠慧海也一再强调“非离世间而求解脱”。大照禅师更是把不坏纲常名教等世间法说成是求得涅盘解脱的必要前提,他说:“世间所有森罗万象,君臣父母,仁义礼信,此即是世间法不坏。是故经文:不坏世法而入涅盘,若坏世法,即是凡夫。”黄蘖希运禅师则视世间与出世间、众生与诸佛“元同一体”,进一步把世间与出世间打成一片。中国佛教的这种“即世间求解脱”在宋明以后得到了更充分的体现,“世间法则佛法,佛法则世间法”成为佛教界的普遍共识,憨山德清甚至提出了“舍人道无以立佛法……是则佛法以人道为镃基”的说法,这里“所言人道者,乃君臣、父子、夫妇之间,民生日用之常也”。
主张“出世”的佛教在中国最终完全面向人生,依“人道”而立“佛法”了。
禅宗即世间求解脱的修行实践更突出地体现在了其农禅并作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农禅生活最早可以追溯到四祖道信。在道信之前,禅僧大体上都过着游方的生活,居无定所。到道信入住双峰山,号召门人垦荒耕田,劈柴烧火,从事生产劳动,开始过上自给自足的定居生活。四祖之后,这一农禅并作的生产生活方式为后世所继承。到百丈怀海,更身体力行,带领徒众共同劳动,乃至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美谈。百丈怀海还在以上思想和行事的基础上,不循旧律,因地制宜地制定了禅门规式——《百丈清规》,将“行普请法”、“上下均力”、共同劳作作为制度确立下来,从而为农禅并作的生产生活方式提供了制度保障。百丈之后,躬行“农禅”的祖师代不乏人,北宋宗杲禅师、明代慧经禅师、元贤禅师等均大力倡导“农禅”事业,特别是宗杲禅师不仅以“农禅”传道,而且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满怀忠义之心,力主抗金,抵御外侮。他曾说:“予虽学佛者,然爱君忧国之心,与忠义士大夫等。
但力所不能,而年运往矣。”宗杲以方外之士关注时事,将修禅之“菩提心”同世间之“忠义心”结合,表现了他习禅不忘爱国救世的入世关怀。农禅并作的生产生活实践,不仅适应了我国小农经济为主的社会环境,有利于禅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同时也促使中国佛学朝现实社会人生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惠能开创的“即世间求解脱”的修行观念及修行实践,特别是后期禅宗倡导的“农禅”事业,将佛教修行实践融入平常的日用之中,融入农业生产劳动之中,将出世与入世融为一体,以方外之身、出世之心从事世间事业,反对离事空谈禅法,体现了中国佛教对世俗生活价值及生活方式的肯定,是中国佛教入世关怀的现实体现。
三、“救世救国”入世关怀之参与世间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