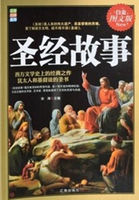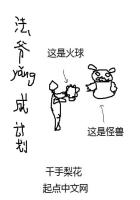日本的林进指出:“各种非语言的象征符号体系如仪式和习惯、徽章和旗帜、服装和饮食、音乐和舞蹈、美术和建筑、手艺和技能、住宅和庭园、城市和消费方式等等,都包括其中。这些象征符号体系在人类生活中各个领域都可以找到。”这些象征性非语言符号也是一种无声的语言,它们主要以形象的方式传达了许多语言符号不能或不完全能传播的信息。生活中其实处处是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相结合才能保证传播活动的顺利进行。老子率先提出“不言”的语言传播理念。在他看来,就无限的道意而言,语言是苍白的。“不言”或少言比多言更能达到传播效果。老子是基于“多言数穷”的认识提出“不言”的。老子的“不言”思想历来引起不少争议。聪明的白居易对此也颇感困惑,他在《读老子》诗中说:“言者不知知者默,此语吾闻于老君。若道老君是知者,缘何自着五千文?”他自鸣得意以为抓住了老子的致命弱点;其实,自己不过是老学的门外汉而已。老子所说的“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老子》第五十六章)的名言,首先是他一贯讲究慎言慎行的必然结果。
他认为无论是说话做事,都应当奉行“唯施是畏”(《老子》第五十三章),言多必失,谨防祸从口出。不过,“老子没有否定语言传播的价值,而是从批判的角度,说明了语言传播的局限性,揭示了现实社会中语言传播的异化现象,提出了语言传播的最佳境界是不言,不言才是最好的言。”“从语言传播看,只要一切符合言的自然性(即言的规律),不在言的自然性之外去刻意追求,就能达到最佳的传播效果,这便是老子所谓不言的真正内涵。”其实,最好的语言是没让人感觉语言的存在,正如天地的美不需要言说而自美一样,庄子就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庄子·知北游》)物以其内在规定(理)呈现为现象界的形象,这是自然而然的。语言传播的最好感觉那就是让受者好像成为对象本身,对象的一切了然于心,而没觉得语言符号在告诉他什么。“老子用否定的方法建立的对语言传播的认识,使我们对语言媒介可以有更清楚的了解,它促使人们对语言传播中言与意的关系、语言的美与真及美与善、语言传播的最佳效果等等这些问题作进一步的思考。”其实,老子提倡“不言”,还有一个意图,那就是实现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相互配合以实现最佳的传播效果。
老子曰:“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老子》第二章)称“不言”的传播效果是:“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老子》第四十三章)“不言之教”的重要内容包括形象传播、体态符号传播等。老子形象地刻画了得道圣人的日常行为表现,而圣人的以身作则,便是对百姓的不言之教:古之善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夫唯不可识,故强为之容。豫焉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俨兮其若容;涣兮若冰之将释;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浊。(《老子》第十五章)这种不言之言的效果是“不言而善应”(《老子》第七十三章),意思是说百姓争先效仿。《管子·心术上》:“不言之言,应也。”《管子·心术下》:“不言之言,闻于雷鼓。”可以说,不用言语的语言,有着潜移默化的效应。在道家看来仁义礼智信的教化效果是有限的,很容易适得其反。老子就说:“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老子》第三十八章)圣人“为而不争”(《老子》第八十一章)的行为形象,反而深深地感动百姓,进而自觉地配合圣人施政。正如施拉姆(WilburSchramm)所言:“尽管非语言的符号不容易系统地编成准确的语言,但是大量不同的信息正是通过它们传给我们的。”也就是说,信息的传播并不完全依靠语言符号,只有充分地运用非语言符号的传播艺术,语言传播才能得以更顺畅地进行。
此外,不言也指面对不可言、不能言的东西当保持沉默。在道家看来,道正是这样的存在。《庄子·知北游》说:“道不可言,言而非也!”道是无限的,语言是有限的,以有限的语言来表现无穷的大道,必然会显得窘迫。《吕氏春秋·审应览·精谕》曰:“目击而道存矣,不可以容声矣。”意思是说,两个见面即相知,无须语言。眼睛所见的形象也是一种承载意义的符号,是谓“目视于无形”(《吕氏春秋·审应览·精谕》)。见到形象,则对方的心志自明。这正是不言的原因之一。
(二)无言:无不言的语言传播效果
道家崇尚“无为”,无为不是不为,其实是为无为,无为而无所不为,无言其实就是言无言,无言方可无所不言。道家追求“无言”之境,试图以“无言”的方式去体悟道意。这其实是“道”的存在方式决定的。道虽然不是具体事物,但也是物的存在,是无物之物,这就决定语言在表达道的时候当是“无言之言”。
《庄子·则阳》曰:“万物殊理,道不私,故无名。”无名自然是无言了。无名为众名之源,无言为众言之主,正所谓“此时无声胜有声”。在语言传播过程中,常常也有“此时无言胜有言”的情景。无言并不是不说,只是此时此地此人不该说则不说。无言又何尝不在“言”。“无言”可以通俗理解为“无不当之言”。言必及道,言必合道。庄子学派说:“其口虽言,其心未尝言。”(《庄子·则阳》)他们认为口之所言,乃应事而言,事过则舍,其内心未尝动,没有情感渗入,故“无言”。《庄子·寓言》所说的“终身言,未尝言;终身不言,未尝不言”也是这个意思。此外,《列子·仲尼》曰:“得意者无言,进知者亦无言。用无言为言亦言,无知为知亦知。无言与不言,无知与不知,亦言亦知。亦无所不言,亦无所不知;亦无所言,亦无所知。”得意者沉醉于意境中,故无言;进知者在品味智能的佳酿时,亦无言。然而,他们此时此刻又何尝无言,何尝无知,又何尝言,何尝知?知与无知,言与无言没有绝对的界限,如果有界限了,那就是小言、小知了。道家倡导“去小知而大知明”(《庄子·外物》),认为“小知不及大知”(《庄子·逍遥游》)。大知是没有局限的,而小知则囿于己见。道家倡导“大言”,摒弃“小言”,这是因为“大知闲闲,小知间间。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庄子·齐物论》)闲闲乃宽裕之意;炎炎乃燎原烈火;间间者,分别之意;詹詹者,费词之意,含竞辩之意。道家提倡“大道不称,大辩不言”(《庄子·齐物论》)。大言乃是言满天下,无所不言,却又无所言,因为其言无瑕谪;小言则私心自用,费神焦心。
道家注重无言,并不是什么时候都可以无言,无言是得“意”的结果。
黄老道家作品《吕氏春秋·审应览·精谕》曰:“知谓则不以言矣。言者谓之属也。”谓是所指,即意义。语言是从属于意义的,意义既然获得了,就无需“言”。
(三)忘言:语言传播效果的极致
忘言是对语言工具的升华,其实质便是意义的获得。“语有所贵者,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庄子·天道》)。在道家看来,单纯的贵言是舍本逐末。“着于竹帛,镂于金石,可传于人者,皆其粗也”(《文子·精诚》)。“粗”意谓“末”。因为本在“意”,末为“书”(含语言文字符号)。语言有形式上笔画的形象存在,还有发音上的声音存在,然而离开了意义,语言本身的形式存在便没有任何价值。其实正如解释学所说的,语言一旦以文本的形式呈现,其意义便非立言者所能限定,文本所载这“言”总是包含着不断延伸的意义空间。庄子学派将圣人之言视为“糟粕”,其旨在告诉世人不要死于文字之上,而应于圣人的心地上驰骋。《庄子·秋水》曰:“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物之外在形象和内在功用常常是可以言论的,也可以用思维来把握。在道家看来,终极的意义是言语道断,即语言成为进道的障碍,必须“忘言”。只有忘言了,才能实现对意义的完全占有。而此时,意会内涵之意义是不能言传的。轮扁说:他“斫轮……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
此种斫轮之技乃基于悟性,非语言的理性所能表达。《庄子·外物》曰:“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言好比捕鱼之荃,逮兔之蹄,行动的目在于鱼兔,而非荃与蹄。语言运用的最终目的在于传意,得到意,就不需要去在乎“言”。究其实质,作者是想表达一种思想即语言不能代替生活本身。一切包括语言在内的活动都应以维护人的存在为前提。“得意”的含义在于对语言的超越,是人对自己存在价值的获得。此种佳境是“无言而心说(悦)”(《庄子·天运》)。可见,道家除了关注言与意的关系问题,还以“心”的方式体现人的主体性,并关注着自由与幸福。此所谓“言不尽意”。其意义在于“尽心”、“洗心”,即心的冰释。《易传·系辞上》也肯定指出“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但这不等于说不要言,言表达不了意。而是说“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这里的“尽神”便是“尽心”之意。卦象、卦爻辞都是在尽言、尽意、尽利,最终还在于悦心,是谓“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忘言的精髓在于忘心。《庄子·大宗师》曰:“悗乎忘其言也。”悗,无心也。言必有心,无心则无言。语言常带有个人的目的性,而这在道家看来是人生之累的根源,应当舍弃。无言,无心,逍遥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