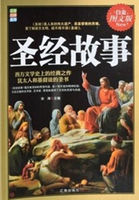甚至我们考虑到口头传说经过长久的代代相传,以及从一地传到另一地的流传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各色各样的大量掺杂和改变,即使在这时候,我们仍会发现很难从关于一场大洪水的多种多样的、往往是离奇、幼稚或者荒诞不经的故事中辨认出这是对一个单独的神圣原本的人为复制。而且自从现代研究证明了人们所推测的《创世记》里的神圣原本也不是什么原始文本,而是古老得多的巴比伦版本或准确地说是苏美尔版本的一个相对较晚的复制品以后,这种困难就大大增加了。为基督教辩护的人中间没有一个愿意把带有强烈多神教色彩的巴比伦故事,当作是神对人的原始启示。如果说神灵启示论对原始文本不适用,那也就不可能靠它来说明其复制品。
因此,我们在摒弃与已知事实不可调和的神启论的同时,还必须探寻巴比伦传说或苏美尔传说——它肯定是所有洪水传说中最古老的——是否可能不是其他所有传说的鼻祖。对这个问题很难给出正面回答,因为在此类情况下是不可能给出证明的,同时我们的结论必须来自对各种可能性的考虑,而不同的人对它们会有不同的评价。无疑可以分析每一个故事直到它们的各种组成元素,把这些元素进行分类,计算出各种不同故事中共有元素的总数,并根据某个故事中发现的共有元素的总和判断出它可能是派生的还是原生的。我的一位前辈实际上已经在这个研究领域里做过这项工作了,可是我不打算重复他的计算。具有统计学或数学才能的读者可以到他的著作中查询,或者可以根据我前面的内容所提供的数据自己进行计算。我在这里将仅仅满足于陈述一般结论,而让读者利用我提供给他的材料去验证、纠正或反驳这个证据。
因此,与无疑来自巴比伦的希伯来人的传说不同,以及与明显带有后来传教士或者无论如何是基督教影响痕迹的现代故事不同,我认为我们没有明确的理由去把任何一个洪水传说追溯到巴比伦,并将其作为原始范本。确实,有几位学者坚持认为古希腊传说和古印度传说都起源于巴比伦;他们也许是正确的,但是我并不觉得这三个传说之间的相似之处足以向我们证实所谓的同一来源。毋庸置疑,在古代的最后年头,希腊人既熟悉巴比伦人的洪水传说,又熟悉希伯来人的洪水传说,但是他们自己的大洪水传说却要比马其顿王亚历山大的征服活动早得多,这种征服第一次向西方学者揭示出东方的知识宝藏。在希腊人传说的最早形式中并没有显示出向亚洲源泉借用的明显印记。比如,在最接近巴比伦的丢卡里翁的传说里,只有丢卡利翁和他的妻子在洪水中存活下来,等到洪水平息后,他们被迫必须用抛石头的神奇方法重新创造人类,根本没有提到重新造出可能已经在水灾中死亡的动物。这与巴比伦传说和希伯来传说非常不同,后两种传说通过让足够数量的人和动物搭乘上船或方舟的方法,为洪水过后人类和动物的定期繁殖埋下了伏笔。
类似地,将古印度的洪水传说与巴比伦的洪水传说作比较,也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某些重要的差异。在古印度所有各种说法中起着重要作用的怪鱼,在巴比伦故事中找不到明显的对应物。虽然有些学者机敏地争辩说,印度传说中化身为怪鱼警告摩奴洪水将至的神,是埃阿神的复制品,埃阿神在巴比伦传说中也这样警告过乌特纳皮什替姆,因为看来埃阿毫无疑问是个水神,故而构想和表现为半人半鱼的形象。假如所猜测的两个传说之间的这种对应联系能够得到证实,那当然可以说在两种传说之间锻造了坚固的纽带。另一方面,在《百道梵书》里最古老的印度洪水故事形式中,摩奴是大洪水中的唯一幸存者,而在灾难过后,必须用他的供品牛油、酸牛奶、乳浆和乳渣,神奇地创造出一个女人,以便让他能够繁衍后代。只有到了这个故事后来的版本里,摩奴才把各种动物和植物大量带到船上;甚至在这些版本中,当这个贤人出现在船舷边时,虽然有一帮他从水中救起免死的兄弟们在旁边,却仍然只字未提他救出自己的妻子和孩子。
这个疏漏不仅透露出摩奴缺乏家庭温情,而且揭示了他作为思想家缺乏一般的深谋远虑,并与巴比伦传说中与他相应的那个人富有实际经验的远见卓识形成强烈的对比。巴比伦传说中的“摩奴”身处同样艰难的境地,他至少因为被漂流在狂暴的水中的家人们围在当中而感到安慰,他感到安慰还因为知道洪水不久就会停息,他能够在他们的帮助下,通过正常的自然方式,准备人种的繁衍。两个故事之间的这种有趣差异,对于研究闪米特人精通世事的深谋远虑和印度人理想的禁欲主义之间的对照,不是很富有想象力的吗?
总的来说,没有多少能证明古印度和古希腊的洪水传说都来源于相应的巴比伦传说的证据。我们想起,据我们所知,巴比伦人从来没有成功地将他们的洪水故事传播给埃及人,尽管他们与之有着几个世纪的直接交往。那么,如果他们没能把该故事传递给距离更远、直到亚历山大大帝时期才与之发生一点点联系的希腊人和印度人,我们也就不会感到奇怪了。后来,通过基督教文献所起的媒介作用,这个巴比伦传说才真正走遍了全世界,并在珊瑚岛的棕榈树下,在印第安人的小屋里,在北极圈的冰雪之中所讲的故事里得到了反响。但如果撇开基督教或伊斯兰教的媒介作用不谈,那么这个传说实际上看来几乎没有越出过自己的本土以及毗邻的苏美尔地区。
如果我们想在已经审查过的其他许多洪水传说中,找出从一个共同源头派生出来的证据,并因而找到从一个单独的中心向外传播的证据,我们必定会因北美阿尔冈昆人的故事系列中那种派生和传播的明显标记而遭受挫折。在分布如此广泛的同一语族的不同部落中记录下来的许多洪水传说,彼此之间如此相像,以至于我们只能认为它们不过是同一个传说的各种变体。在最初的那个故事中,各种动物潜入水中去找泥土的情节,究竟是本土的还是基于对白人传给印第安人的挪亚故事中鸟儿的回忆,这也许仍然是个问题。
此外,我们注意到,据洪堡说,在奥里诺科河附近居住的印第安人中的各种洪水故事之间,可以探寻出总体上的相似点。而据威廉·埃利斯说,在波利尼西亚人的各种传说中也盛行同样的相似之处。也许在这两个地区,传说是从地区的一些中心传播开来的,换句话说,它们是同一个原本的不同异文。
然而,我们在允许存在从地区中心向外传播的所有这种情况的同时,必须承认,看来也可能存在一些独立起源的洪水传说。
17.大洪水故事的起源
化石证据支持的普遍性洪水的旧理论 世界性大洪水理论在19世纪的留存 大洪水故事被解释成太阳、月亮或星星神话 地理证据不支持世界性洪水 关于远古世界性海洋的哲学理论 许多洪水故事可能是对真实事件的回忆 值得注意的荷兰洪水 太平洋地震海啸引发的洪水 太平洋地区有些洪水故事可能是对地震海啸的回忆 暴雨引发的水灾 巴比伦故事用幼发拉底河谷每年的河水泛滥来解释 大洪水传说半是传说,半是神话 基于地质构造和化石的观察神话 所以大洪水故事可能都不是太古老的我们还要发问,产生洪水传说的原因是什么?
人们怎么会普遍认为在某个时候,整个世界或者至少是人居住的所有地区,曾淹没在几乎毁灭整个人类的一次强大的洪水之下?对这个问题,从前的回答是,这样的大灾难确实发生过,《创世记》里有一个详细和权威的记载。而在居住得非常远的人类中间发现的许多大洪水传说,则包含着对那场可怕大灾难的或多或少不完整的、混乱的、歪曲的追忆。在支持这种观点时,一个最常提到的根据据说是挪亚时代的洪水退去以后,留在高处以及在沙漠中或山顶上晒干的海中贝壳动物和化石。德尔图良引用了山上发现的贝壳类海洋动物,以此证明大水一度曾淹没世界,不过他没有明确地将它们与《创世记》中的洪水相联系。为了修缮维罗纳城,1517年在当地进行了发掘,出土了大批希奇古怪的化石,这项发现引发了各种各样的猜测,挪亚及其方舟当然在这些猜测中格外引人注目。但它们并非没有遇到挑战,因为意大利自然哲学家弗拉卡斯托罗相当大胆地指出了这个普遍流行的假设中的困难之处。
他注意到:“那次水灾,持续的时间太短;它主要是由河水泛滥引起的;假如它能把贝壳类水生动物长距离搬运,那一定会把它们散播在地表,而不会把它们埋在群山里的最深处。”假如人们的激情没有被这场争论煽动起来的话,他对证据的清晰表述也许已经使争论永远结束了。到17世纪末,一支由意大利人、德国人、法国人和英格兰人组成的神学家队伍侵入了地质学领域,他们使问题变得模糊,使本来已有的混乱变得更加混乱。“从此,那些不同意说所有的海洋生物遗骸是摩西五经中那场洪水的证据的人,都被扣上怀疑整部《圣经》的污名。自从弗拉卡斯托罗时期以来,几乎没有向正确理论迈出一步:一百多年的时间都花费在把有机体化石纯粹是大自然的游戏这一原理明确地写下来。
此后又过了一百五十年,这段时间注定要花费在驳倒有机体化石都是因挪亚洪水而埋藏在坚固的地层里的假设。在任何科学分支里,还没有一个理论谬误是如此与准确的观察和对事实的系统分类发生严重的抵触的。在近代,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快速进步主要归功于通过研究矿物体内各种有机物遗骸,以及它们有规律重叠的方法,仔细地确定它们的演替次序。但是,旧的洪水研究专家囿于自己的体系,弄混了所有聚积在一起的地层组,同时把所有的现象都归结为一个起因和发生在一段短时间里,而不是归结为各种原因在各个时代的长期替换中发挥作用的结果。他们只看见现象,因为他们希望看到这些现象,他们有时歪曲事实,有时则从正确的数据里推演出错误的结论。简而言之,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末的地质学发展简略过程,是新观点同各种教条进行不断激烈斗争的历史,这些教条一直以来受到许多代人毫无保留的信仰,并认为建筑在《圣经》权威的基础之上。”
这样打上查理·赖尔爵士印记的谬误很难消亡。不到一个世纪前,威廉·巴克兰受任牛津大学地质学高级讲师,他在自己的就职演说中仍然向听众保证说,“如此明确而无可辩驳的证据表明,距今并非很远的时期所发生的世界性洪水这一重大事件,即使我们从来没有在《圣经》或其他任何权威著作里听说过类似事情的话,那么地质学为了解释洪水活动行为,本身就得求助于类似的大灾难。”在我们生活的时代,还有另一位着名的地质学家写下了如此看法:“我一直认为,为了弄懂《创世记》第七章和第八章的故事,只能设想这是当时的某位目击者的日记或书札,被《创世记》的作者收录在他的书里。大水涨落的数据,水位最高时测量漫过山顶的水深记录和其他一些细节,以及故事的总体基调,看来都需要这样的推测,这种推测同时也消除了通常总会感觉到的解释上的所有困难之处。”但是,如果《创世记》中的洪水故事是当时一个目击者的记录,那么如何解释其中包含的关于洪水持续时间和带上方舟的动物数量等明显的不一致之处呢?这样的理论不仅没有解决困扰着故事的各种困难,而且相反,使这些矛盾变成只能推测,否则便完全无法解释,而这种推测无论对于讲故事人的诚信度或严肃性都是有害和不公正的。
我们也无需过多地停留在德国近几年广受欢迎的对洪水故事的另一种解释上面。根据这个观点,洪水故事其实与水或方舟没有任何关系,而是讲述太阳、或者月亮、或者星星、或者三者皆在其中的一个神话。至于做出这个惊人发现的学者们,他们因反对一般流行的“尘世”解释而走到一起,但是相互之间在自己神圣的“天体”理论的所有细节处并不一致。
有些人说方舟就是太阳;另一些人认为方舟是月亮,方舟上涂抹的松香则是月蚀的象征性表示;而我们应该根据方舟建有三层来理解月亮的相位。
最近有一个月亮理论的信徒,让人类乘上月亮之船,却让动物住到星星上去,各自为生,从而试图将所有的矛盾都调和成一个更高层次的整体。严肃地谈论这些争论也许是过分尊敬了如此博学的荒诞无稽。我提到这些理论仅仅是为了娱乐,用它们来减轻一点严肃冗长争论的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