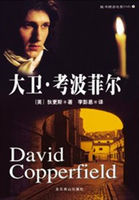纪事
这一年上半年在香港,犹豫一年之后,终于在9月初开始到中国人民大学上课,又在半年之内两度赴德一度赴法,至少参加了四次较大的学术会议……所以回顾之下,觉得以自己如此惰性,竟还写了在我看来是相当多的论文,有些惊奇。也许,两个“9·11”事件(参见附录一)的刺激是一个原因?
当然,代价是要付的,妻子说我的头发变白,明显衰老,就是在此之后!
立足道德自强,争取社会正义
——《我有一个梦想》序
年纪稍大的中国人应还记得,1968年春,“文革”还正如火如荼之际,毛泽东发表了一篇“五·二零声明”,全国各地为此举行了由上级组织的大规模游行。很多人应还记得,事情同马丁·路德·金被刺杀有关,而这位马丁·路德·金,乃是着名的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事过多年之后,我却发现,不少人居然把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同四百多年前那位德国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相混淆,而对他的主要主张“非暴力抵抗”,更是懵然无知!
1956年,二十六岁的马丁·路德·金在第一次领导黑人市民抵制蒙哥马利市公共汽车公司的种族隔离制度时,就举起了“非暴力抵抗”的旗帜。他号召久被歧视的黑人群众说:“我们要抵抗,因为自由从来不靠恩赐获得。有权有势的欺压者从不会自动把自由奉献给受压者。权利和机会,必须通过一些人的牺牲和受难才能得到。”但是,“仇恨产生仇恨,暴力产生暴力……我们要用爱的力量,去对付恨的势力。我们的目标,绝不是击败或羞辱白人,正相反,我们要赢得他们的友谊和理解。”
然而,当他回到家里,却接到了白人种族主义者的恐吓电话!再过一段时间,恐吓变成了事实——他的家被炸了!
就在那被炸得七零八落的家门口,他对闻讯赶来、手持武器、群情激动的支持者发表演说:“冤冤相报的暴力不能解决问题,我们要以和平对待暴力,记住基督耶稣说过: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无论那些白人对我们怎样,我们要爱他们,如同兄弟。耶稣不是说过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逼迫你们的祷告吗?我们要以恩报怨,以爱报恨。”
十二年后,这位“非暴力抵抗”的倡导者,死在枪弹的暴力之下。这当然令人想起马丁·路德·金所钦佩的印度国父圣雄甘地——他作为“非暴力抵抗”的首创者,也死在枪弹的暴力之下!
于是,有不少人得出结论说:非暴力主义是软弱的、无效的、注定要失败的!
它的两位最着名的鼓吹者甘地和马丁·路德·金,就是最好的例子!
甘地和马丁·路德·金失败了吗?他们用生命去实践的主张是失败的吗?
是无效的吗?是软弱的吗?
首先,我们要承认,中国的古话“勿以成败论英雄”,是出于良知的智慧,而“历史由胜者来书写”,是人类社会的耻辱。
即便我们只采用世俗的“成败观”来评判这两个人物和他们的主张,我们也无法抹杀这些基本的事实:
就甘地而言,他比任何别的印度领袖都动员了更多的民众,他用最少的牺牲赢得了当时世界上最多的人口的民族独立运动的成功!他以最低的代价(或伤亡率),以和平的方式,最有效地摧垮了一个统治方式最有效的殖民帝国的长期统治!他那副瘦骨嶙峋的身躯包含着的精神力量之强大,使得那个作为世界霸主的敌人也肃然起敬,不但多次把他从阶下囚尊为座上宾,而且至今把他的形象同诸多英国伟人一同安放在伦敦的蜡像馆中!他不但成了印度的伟人,也成了世界的伟人,他的思想和典范不但属于印度,也属于全人类!
就这本书的主角——马丁·路德·金而言,他领导的非暴力抵抗运动,不但赢得了蒙哥马利城公共汽车种族隔离制度的废除,而且赢得了全国、全世界对伯明翰市黑人运动的关注和同情;不但胜利地组织了向首都华盛顿的大进军,而且深深地打动了包括总统肯尼迪在内的各阶层白人的心;不但促成了美国国会通过民权法案,从法律上正式结束美国黑人的被歧视地位,而且影响了英国国会通过反种族歧视法和反性别歧视法,从长远来说还促成了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崩溃——顺便说说,南非黑人运动的领袖曼德拉,可视为甘地和马丁·路德·金之后最伟大的非暴力抵抗倡导者。
至于这些胜利之伟大,以及马丁·路德·金的努力成效之惊人,可以从以下事实略见一斑:美国白人对黑人的歧视,曾在长达三百多年之中被视为当然,被视为有理,所以问题远远不止是法律的禁止与否,而是人们的心理和观念的改变与否,后一件事情人人都明白是最难做到的。然而人们看到,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一些大学的白人学生暴乱,会仅仅是因为学校收了几个黑人学生,而在20世纪结束之前,白人却早已习惯了大量的黑人官员、黑人警察,甚至黑人部长、黑人军队首脑,更不用说社会生活各领域的黑人白人的共同活动,甚至已有了不少白人与黑人的通婚;而在21世纪开始之际,甚至已有黑人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国务卿!
就马丁·路德·金个人而言,他不但在生前获颁诺贝尔和平奖,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获奖者,而且他的生日早被确立为法定全国假日,这在从国父到各界名人的行列中也极其罕见。最主要的是,他也同甘地一样,不但成了他本国良知的代表,还成了人类良知的代表。而这一切所证明的,恰恰是同样个子矮小、其貌不扬的马丁·路德·金的精神力量之强大,恰恰是他和甘地、曼德拉等等所代表的非暴力抵抗的精神力量之强大。而这种精神,往近处可以追溯到托尔斯泰和雨果,往远处可以追溯到人文主义的许多伟大思想家,究其本源,还可以追溯到各大文明的创始性人物耶稣、苏格拉底、佛陀和孔子。
当然,我们已经看到,就马丁·路德·金来说,他的这种精神之强大,是来源于他的基督教信仰。但他认为基督福音不是个人精神的福利奖券,而是社会公义的实践要求。但在争取社会正义的斗争中,他认为“爱心是我们唯一的武器”。他说:“爱你的敌人……是指圣经希腊文的agape(圣爱),是无视敌友亲疏、仿效上帝的无私博爱。”这种爱有一种最根本的神学肯定作为存在基础,即“上帝就是爱”。
正因为如此,他可以强大到不在乎胜利与否的地步——他领导的运动参加者要遵守的“非暴力十诫”中有一条是“要争取正义与和解,而不是争取胜利”。这令人想起林肯的名言:“我关心的不是事情能否成功,而是事情是否正当。”
也正因为如此,他可以强大到视“受苦”为“救赎”,甘愿自己流血牺牲的地步——他说:“要争取自由,必须付出流血的代价,而流的血必须是我们的鲜血……无辜受苦是有救赎力量的,它可以取代欺压者与受压者双方苦毒怨恨的悲剧结局。”这更令人想起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难。
这种来自信仰的精神之强大,在马丁·路德·金争取社会正义的斗争中,就表现为一种道义上的强大或道德上的自强。为他在复杂的处境、艰难的斗争和内心的矛盾中提供了坚如磐石的基础的,正是这种道德自强的力量。这种力量对于任何争取社会正义的斗争来说,是经费的或经济的、武器的或武力的力量都不可比拟的。
马丁·路德·金已经去世三十三年了。但是,这本书所提供的他的言行,对于当今的世界来说,不是仍值得思索吗?这些言行所树立的崇高榜样,对于当今的人类来说,不是仍值得效法吗?
2001年6月9-10日
爱、理性与正义
——“9·11”事件引起的思考
“9·11”惨剧发生之后,一位反恐怖专家回答大家最关心的问题说:对于今后的安全,只可能有更好一些的保障,不可能有绝对可靠的保障。
这道理十分清楚:正如大炮无法对付吸血的蚊子,再强大的保安设施也无法对付少数扭曲的心灵在阴暗中滋生的恶念。这类丧心病狂的行动(不久前在我国石家庄也发生过一次),恰恰是来自这类暗中滋生的思想。而对于思想,任何军警的配置,任何武器的装备,任何保安的设施,都是无法防止其产生的。
难怪还有一些专家在谈到反击或惩罚行动时,十分担心由此激起的仇恨思想,会制造更多的无辜者受害者。因为,偏执而狂热的仇恨所导致的恐怖主义,正是以无法进行防范的广大民众为目标的。
当然,我们不能排除一些恐怖分子的内心,也许还有过分膨胀的自大狂、自以为是的“英雄”热、自我中心的出名欲、宗教狂热的“天堂”梦等等,但是,毫无疑问的一点是,促成这类丧尽天良的恶行的,主要是偏执狂热的仇恨。正是这种仇恨,扭曲了罪犯的心灵,催生了犯罪的思想。
一
思想的形成,是广义教育的结果。所谓广义教育,即不仅仅是家庭和学校的教育,而是包含媒体宣传和环境影响在内的诸因素对人心的综合性作用,也即是“性相近,习相远”一语中的所说的“习染”。这些东西对人发生的作用,既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可以培育爱,也可以培育恨。正因为如此,所以《三字经》接着要说起“昔孟母,择邻处”的教育故事。
显然,针对偏执狂热的仇恨思想的产生,我们所需要的是爱的教育。因为在“9·11”事件中,有劫持飞机者的恨,也有排队献血者的爱,而前者在制造死亡,后者却带来生命。
尽管如此,我们也很难断言,被仇恨扭曲的恐怖主义者心中,从未有过任何一种的“爱”。例如,其中的张三也许爱他原来的工作,李四也许爱他的情人,王二麻子也许爱他的民族或国家。而且,这类爱的情感,也许还同这种恐怖行动有某种关联(例如由于其所爱的对象被剥夺),至少这种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事实上,人类生活的经验告诉我们,爱与恨常常相连甚至常常相辅相成。更有甚者,我们还常常发现,人类生活中的诸多罪恶,都同爱有某种关联。例如,不少个人在杀害情人或情敌时,以“爱得太深”为理由(如某些通奸杀人案);不少集体在迫害异己时,以“爱党”为理由(如文革中的无数冤案);不少民族在侵略别族别国时,以“爱国”为理由(如二战时的许多日本人)。以至于我们可以发问说:爱,有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当然,我们可以发现,人类生活中的罪恶现象与“爱”的关联,有些是虚假的(例如一些情杀借用爱的名义,其实是出于自利心或妒忌心或报复心,而不是爱心),有些是真实的(例如一些残酷的战争行为,有些乃出自真实的爱国心,尽管这“国”已成为脱离了“人”的大受歪曲的抽象概念)。但是往深处看,这些联系却反映出爱这一现象的高度复杂性,以及由之产生的认知混乱和思维混乱。
实际上,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的日常生活中,都有许许多多对“爱”这一概念的误用或滥用。而这些误用或滥用,有很多来自对爱的一种简单化解释,即将其仅仅解释为一种情感。当然,爱首先是一种情感状态,是一种自然或自发的感情。它正如蒂里希所言,“不是意图或要求的事情,而是偶发或天赐的事情。”这是对爱的情感论解释。但是蒂里希也指出对爱还有另一种解释,即伦理学的解释。因为,既然爱作为情感是不能要求的,而在西方文明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的“爱上帝、爱邻人”这两大诫命即要求又有着巨大的意义,那么,就只能把对爱的理解扩大,才能够把握这一复杂现象的本质。为了理解爱的伦理性质,蒂里希还提出了爱的本体论或存在论定义,即“爱是对分离者重新结合的推动”。按照这种本体论或存在论,由于存在本身是一,一切存在者本来也在本质上是一体,但是存在者一旦进入实存或时空之中,也就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体而同其他的个体分离。分离者总是在力争重新结合。而爱,就是使一个存在物趋向另一个存在物的力量,即使之重新结合的力量。
在西方语言中,至少有四个词被用来表达爱本身的复杂多样或多层次性。第一个是libido,狭义指性欲或性爱(弗洛伊德),广义则指趋向生命自我实现的正常动力(蒂里希);第二个是eros,一般指情爱或欲爱,在较高层的意义上则可指“对真善美的爱”;第三个是philia,可译为友爱,主要指“人与人之间的亲近和信赖的友谊之爱”;第四个是agape,可译为“圣爱”或“仁爱”,指的是爱的最后和最高的形式,是与生命基础相关联、可防止其他形式的爱被扭曲为自私自利、体现了终极实在的爱。
在现代汉语中,至少也可以用三个词来表达爱的不同类型,一是“喜爱”,二是“情爱”,三是“仁爱”。这三种类型的爱,在起因、趋向和爱的关系这三大方面都是不同的。
喜爱在某些方面接近希腊文之eros,或拉丁文之libido,或古汉语之“欲”。它的起因,是认知到对象的可喜性质;而其趋向,是欲求占有该可喜的对象或享受该可喜的性质;与之相关,这种爱的关系,是以自我为中心,以爱的对象为客体,在爱者与被爱者之间建立的“我-它”关系。人与一些动物共有的“性爱”、一时的“欲爱”和一贯的“嗜爱”,均可归于此类。这种爱的特点,一是与动物共有的“自然”性质,二是人所具有的“自我中心”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