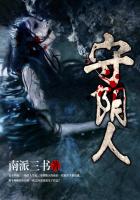命运是注定的吗?如果是,你的任何行动(包括求神拜佛)都是多余的了。如果不是,也就是说,可以通过人力改变,那么这个“账本”又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
有这样一个笑话:一个人到算命先生那里卜问命运,算命先生仔细端详他的掌纹,然后严肃地下结论说:“你很容易上当。”
不可否认,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对于科学——即关于我们赖以生存的物质世界及其法则的知识——是极其缺乏常识的。这并不完全是我们的错。对我们来说,科学从来不是有趣的,我们也几乎没有什么机会对它感兴趣。科学就像巫术——我们既不知道它能做什么,也不知道它为什么能做。科普?简直就是小儿科的游戏。
于是我们心安理得地浅薄和愚昧着,满足于在声光电气中做个野蛮人。这有啥不好吗?
尽管科学昌明,但还是有很多人相信神秘的“命运”是存在的,半信半疑的人就更多。要指出逻辑矛盾是容易的,命运是注定的吗?如果是,你的任何行动(包括求神拜佛)都是多余的了。如果不是,也就是说,可以通过人力改变,那么这个“账本”又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一种防御性辩解是:命不可变,运可以变。这好比说:量变质不变,怎么可能有坏命好运或好命坏运这种奇怪的东西?
上帝有好恶吗?标准是什么?这个标准和人类的道德标准是否一致?很多人说是,如好人一生平安,善有善报,义人的天国,大多数宗教都是这样一套教义,可它们又都宣称除了自己以外,其他宗教都是错的。那么该信谁的?还有一种不便明言的标准:多磕头,多上供,上帝就保佑你。照这个逻辑思考,我们不免疑惑:上帝是个贪官吗?反之,上帝惩罚那些冒犯者,上帝又是个暴君?
毛姆曾回忆他早年遇到的一个老人,这是一个虔诚的教徒,但是却涂抹掉了《赞美诗》中所有对上帝的赞颂之语。他解释说:他是个绅士,从不喜欢阿谀奉承;同时,他相信上帝也是个绅士,也不会喜欢有人对他阿谀奉承。这种逻辑在迷信者看来是危险的,但的确是理智的。
在科学的边缘
有些聪明人会说:好吧,迷信不足取,可是你必须承认,世界是神秘莫测的,我们的知识不过是以管窥天,以锥测地,比如很多超自然现象,科学根本无法解释,既然理解不了,你就得承认,天外有天,某种超出我们理解能力之外的存在是可能的。再说,科学本身不就是在不断前进吗?你怎么知道,你对灵魂、天外来客、宇宙能量的否定不会像过去人们对日心说的否定一样,成为历史的笑柄?
生物学家道金斯曾在一本书里谈到他的一位朋友的见解:既然人类对世界的解释,都是建立在不可靠的有限知识上,那么凭什么认为我们今天对月球的认识要比古人的神话真实?道金斯的回答是:我们可以凭借已掌握的知识登上月球,而神话的“知识”却没有这个能力。
科学的边缘潜伏着一系列诱人的或至少是有些令人震惊的想法,但是对这些思想还没有进行过有意识的检验:一种观念认为地球的表面应是在一个球体的内表面而不是外表面;或宣称你可以通过冥想飘在空中;或说有一种称为灵魂的东西,既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而是一种没有任何实体痕迹的东西。
“心灵感应”这个词意味着是交流感觉、情绪,而不是思想。很多人相信他们经历过类似心灵感应的事情。两个互相了解、住在一起、互相熟悉对方的感觉、交往和思维方法的人经常可以预先知道同伴要说什么。这仅仅通过人的五个感官和心意相通、敏感及理解力就可完成。也许感觉起来像超感知,但这些根本不是“心灵感应”这个词所定义的。
如果像这样的事情最终被确定无疑地证明存在,那么,它还是有可以辨别出的物理原因——也许是脑电流。伪科学,无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称呼,都决不是指超自然的东西,超自然的定义是自然之外的东西。
也许这些超感知主张中的一小部分有一天会被确凿的科学数据所证实是有那么很小一点可能性的,但没有充分的证据就接受它们中任何一个说法都将是愚蠢的。
对于那些还没有被证伪或充分解释的主张,我们最好还是以怀疑的态度,保持耐心,培养对模糊性的宽容,去等待——最好是寻找——支持或否定的证据。
蔚为大观的“神秘事物”
在没有掌握资料之前就建立理论是一种严重的错误。这时人会不知不觉地扭曲事实以符合理论,而不是让理论符合事实。——夏洛克·福尔摩斯
我们都听到过或看到过许多叫人晕头转向的奇谈。比如,据说人们在金字塔里挖出过一个金字塔形状的电视机,四个面都是屏幕;“法老的诅咒”(只是许多传播者弄错了地点,这个故事并不是发生在金字塔里);“神灵附体”的预言家们;灵魂出壳;诺查丹玛斯的预言;“大脚”野人和尼斯湖怪(世界各地似乎都有它们的表兄弟);“世界末日”(由于某种原因,这个日子一拖再拖);印地安人的古老水晶人头;百慕大神秘的“三角洲”等。
你怎么区别真假?面对这些信息,感到真假难辨并不丢人。在大多数领域,我们都很无知——也许,首先承认这一点,是最重要的。一些简单的常识性问题可以帮助你。
首先,这些消息本身可靠吗?来源可靠吗?这些消息的内容可信吗?你是否曾听过类似的?什么人在传播这些消息?
例如,据一个法国人类学家讲,非洲马里的多贡人有一个传说:天狼星有一颗极为致密的伴星。实际上天狼星确实有这样一颗伴星,尽管只有相当精密的天文学技术才能探测到它。那么,多贡人是源于一个曾拥有巨大的望远镜和理论天体物理学的被遗忘的文明吗?或者,他们曾经得到外星人的指点?或者,多贡人是从来访的欧洲人那里听说天狼星的白矮星伴星的?或者,法国人类学家搞错了而多贡人从来没有类似的传说?
即使你判断不出,也没有关系,记住不要轻易下结论。要勇于说“我不知道”。但是你要记住:知识、科学可能犯错,但是我们人类能走到今天,全是和知识一同进步的结果。
车库里的龙
科学家萨根曾讲过一个“车库里的龙”的故事:
某人对你说:“在我的车库里有一条喷火的龙。”这时,你一定想亲眼看一下。几个世纪以来流传着无数关于龙的故事,但从没有真凭实据。这可是个好机会!
可你只看到一堆杂物,没有龙的影子。“龙在哪里?”你问道。
“噢,它就在这儿。”这个人胡乱地挥了挥手,“我忘了说明,它是一条看不见的龙。”
你建议在车库地板上撒上面粉以获取龙的爪印,但他告诉你龙是浮在空中的;你想用一个红外线探测仪检测龙喷出的看不见的火,但他说看不见的火也不会发热;你想对龙喷漆使它现身,但又被告知它是非物质的龙,油漆无处可粘。
如此如此……你每提出一种物理检测方法,他就找个特殊理由来说明你的办法不会有效。
那么,一条虚无缥缈的龙与根本没有龙之间有什么区别?如果没有办法反驳他的争辩,没有可以让人信服的试验来反对它,是否就等于龙确实存在呢?你不能证明关于龙的假设不成立,这与能证实它成立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不能检验的观点和无法证伪的断言实际上毫无价值,不论它们在给我们以启示或是在激起我们的好奇心方面有些什么用处。
想像一下,尽管所有的检测方法都无效,你仍希望自己谨慎地不抱有偏见,因而你并不完全否定车库里有条会喷火的龙。你只能表示怀疑。当然,如果因此指责你太乏味、太缺乏想像,那么显然是不公正的。
现在想像一下另一个场景,假如不只一个人,而是好几个你熟识的人,包括你非常肯定他们互不认识的一些人,都告诉你他们的车库中有龙——但每个人的证据都难以琢磨得让人发疯。我们每个人都承认我们对于被如此奇怪的一个没有事实根据的信念所吸引感到心烦意乱。我们所有的人无一精神异常。我们思索全世界的车库中如果真的都藏着看不见的龙,而我们人类却不知所措,这意味着什么。也许所有古代关于龙的“神话”根本就不是神话……
魔术需要观众与魔术师的默契配合——放弃怀疑,或者如同有时我们所说,心甘情愿地放弃不相信的怀疑。我们立即可以看出,如果要使魔术被拆穿,使戏法被揭露,我们就必须中止合作。
可证伪性是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重要因素之一。一个科学理论或假说,必须经过实践检验,只要你找到反例,你就可以证明它错了。宗教不是这样,迷信更不是。
有一些观点很难检验——例如,一次寻找鬼怪或者雷龙的探险失败了,但这并不能说明它们就不存在。缺乏证据不能证明它不存在。少量的——如永动机——可以用基础物理学排除其可能性。除它们之外,有一些在我们掌握确定其错误的证据之前还不能作判断,奇怪的事情经常是与科学相联系的。
经常出现的问题是,证据的可靠性到了什么程度?证明的重任当然是落在那些提出主张的人的肩头。历史上的佛道之争,道家失败,因为上了佛家的当。佛家抓住道家“真经不怕火炼”的理论,要求当场证明,道家只好同意。结果可知。
动物神话种种
神话的动物——龙、凤凰、独角兽和麒麟的生命早已走到了尽头,然而,动物的神话却还在绵绵不绝且愈演愈烈。
每个人都多多少少听过一些关于动物的难以置信的故事,如海豚拯救落水者,旅鼠的死亡大行军,蚂蚁军团所到之处白骨累累,等等。这其中有些是真实的,有些是夸大的,有些则是彻头彻尾的胡扯。
被陷于狼群的故事总是让人毛骨悚然,每个人都听到过几个版本的这类故事,某个人(或某些人)在荒野被几百条狼包围在一间屋子(或一辆汽车、一个岗楼)里。可以想像,谁要是落到这一步恐怕是在劫难逃了。
幸好——实际上恐怕没人会落到这步田地——上百只以上的狼群在自然情况下几乎是不可能出现的。不要忘了,任何动物行为都有其合理性,而成军队建制的狼群显然没有这种合理性。狼群在春夏季规模很小,往往只是一个家庭,因为此时捕食比较容易;冬天,狼群的规模就大一些,因为环境恶劣,小动物不易捕到,必须捕猎大动物,如麋鹿、驼鹿、野牛等等,这种硬仗需要团队力量。然而,上百只甚至几百只狼组成的大军,无疑是一场灾难,它既不经济、效率又低,难以找到充足的食物供应这只大军——须知:狼集群是为了更好地生存下去,而不是为了称王称霸或有意和谁过不去,研究狼群生活的动物专家告诉我们,实际上,即使大小全算上,狼群的规模也很少超过20只。
如果说,这类夸大还有情可原(毕竟一个受到惊吓的目击者很容易草木皆兵),那么有些有意的胡扯就不可原谅了。一直有人靠大肆编造耸人听闻的动物神话来哗众取宠,遗憾的是这往往很奏效。比如下面这个故事,它曾被很多报刊转载过。
一群麋鹿(或盘羊、岩羊、野山羊)被狼群追上了绝壁,而对面的山崖又相距太远,跳不过去,麋鹿们自动结成了对子,“一老带一新”,两个同时跳,一个踩着另一个的脑袋瓜子跳过去,于是乎,一半儿的自我牺牲拯救了另一半儿的生命,于是乎,“我的眼睛湿润了……”
如果你的眼睛也湿润了,别急着自我陶醉,你不过是个愚人节的傻瓜而已。这位“目击者”的运气很好(居然目睹了如此奇观),可脑袋很差(或者说品行很差,至少该说,很不诚实),不但缺乏最起码的动物学知识,而且缺乏最起码的物理学知识——或者说,除了武侠小说里乱七八糟的胡扯外,几乎什么知识也不具备。
这类乱七八糟的谎言还有的是:有人曾在神农架发现了一种大头驴,专吃老虎,这消息如果有一点真实,就足以令动物学家们惊喜。事实上,神农架早就没有老虎了(显然,缺少了这种可口食品,奇异的大头驴也在劫难逃)。
经常让人提到的另一则神话是马达加斯加岛上的食人树(这回的主角换成了植物)。奇怪的是无论什么时候去调查,这种树总是长在岛的另一头。1920年,美国一家周刊发表了一篇“目击者”的报道,大致内容是一个少女被食人树活活吃掉,这悲惨的故事令好多软心肠的家庭主妇们唏嘘不已。唯一可以告慰她们的是这不过又是一个现代“山海经”。任何生物都不是无缘无故存在的,如果真的有这种食人树,它要生存下来,就必须不断以人或大小差不多的动物为食,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一只到处乱跑的狮子还免不了挨饿,更不用说寸步难行的树了。实际上,食人树现在根本就不存在,也许从来就没有存在过。
只要想想,就会明白这些动物神话大行其道并不奇怪,因为我们实际上是些城市囚徒,对于“文明”之外的东西知之甚少;因为我们总是判断先于理解,猎奇甚于探究;因为所谓“自然”已经越来越成了一种“不自然”的稀罕之物。这种情况下,出几个泡制赚人热泪故事的牛皮匠有什么奇怪的呢?
不,最让人难过的不是这些,而是很容易预见的一幅灰暗的前景:真正的野生动物都已消失,我们只剩下这些荒诞不经的动物神话,并一代一代地传诵下去,越来越离题万里,越来越匪夷所思。
“信仰疗法”为什么起作用?
当我们遇到问题时,自然希望找到答案,当我们现有的知识无法提供答案时,我们就会求助于未知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