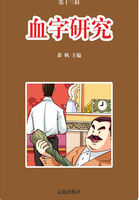“太子妃,太子殿下还在书房处理公事,恕小人冒昧一声,您这……不合适啊……”小厮巴巴地跟在谢子清身后,好说歹说,却还是阻止不了她前进的脚步。
“有什么不合适的?”榕青接过话头,“新婚之夜不见个人影也就算了,这会还不准我们郡主去看他,你们太子殿下身份还真是贵重啊。”句句皆是嘲讽之意。
“榕青,不得无礼。”谢子清轻蹙柳眉。
“奴……奴婢知错。”闻言,榕青想要争辩,但转念一想昨日谢子清同她说的那些,只好垂了垂头,双肩也往下垮了垮。
谈话间,已是到了书房。
“去跟太子殿下说,太子妃娘娘来了。”那小厮看已无力回天,只好向守在门旁的侍从说,那侍从看了谢子清与榕青一眼,推门进去了,不过一会,他出来说,太子让谢子清进去。
“郡主……”榕青想跟着她进去。
“不用了,你守在这里便是,我等下出来。”谢子清言罢,推开了书房的门。
专属于竹简和墨迹的两种香味扑面而来,她站定,最前方,一张竹桌子放在窗下,那男子坐于椅上,玄发束于脑后,却有些许散于肩上,着一身玄色长袍,他的手修长而指节分明,轻衔着一枚白棋,两者相互衬映,竟让见者不知是他的手更白,还是那枚棋子更白。
听到声响他并没有转过头来,只是道,“听闻南堂郡主谢子清棋艺过人,不知今日可否让齐某领教一二?”
“子清只是略知深浅,不敢当这头衔。”谢子清道,“且子清三月前头部受过重创,所谓棋艺,已模糊一片,记不得了。”
“你的意思是,如若没有你身旁那榕青,你恐怕连自己是郡主都未曾想起?”他终于转头望她,分明是带着某种情绪的语句,他却平平淡淡地道来。
“大约如此。”面对他的试探,谢子清不置可否。
他便轻挑了眉,道,“难得你失了记忆还如此平静,不愧为南堂郡主。”
“臣妾不敢。”她仍是面无波澜,却还是站着——从到书房开始,她就没行过礼。
“你还有什么不敢的。”许是听她自称臣妾,他终于站了起来,将那棋子轻扣在棋盘上,转身朝她走来。
“无论何事,臣妾如今都不敢。”她镇定自若地与他打着哑谜,“这些,殿下不是清清楚楚么?”
“青夙。”他在她面前站定,叫着她身为郡主时的封号,伸手便挑起了她的下颚,迫使她抬头与他对视,然后,他端详着这张绝美的脸庞,她的眼里只有一闪即逝的错愕,便立马被平静掩饰。
他的力道大到几乎要将她的下颚捏碎,谢子清轻蹙黛眉,却仍是固执地盯着他的眼睛,毫无畏惧。
她的心里其实很慌,不似她云淡风轻的神色,她居然不敢看齐玦的眼睛,那是一双什么样的眼睛啊,仿佛要将她拉进深不可测的深渊里,她觉得自己在这双眼睛面前仿佛褪去了所有的伪装,所有的一切都显露无遗。
“你今天来找我,所为何事?”半晌,他终于放了手,谢子清的下颚已经有了一道深深的红印,她的腿只是软了一刹,便又重新支撑着自己的身子,脸上的神色却依旧平静如水。
“臣妾既然已经出嫁,便已经是太子的人。”谢子清道,“太子如今正是用人之际,臣妾又岂会坐视不管?”
“当今朔泽,正处在变革之期,这一点,不用臣妾明说,您也心中有数。”她望着齐玦,“您的羽翼若不丰满,被挤兑的,迟早有一日会轮到自己。”
齐玦挑眉看她,等她的后话。
“四王爷与七王爷已在暗中发展势力,论人才,朔泽不会少于南堂,您要在这场斗争中取胜,便还缺了一个契机。”
谢子清定定地望着他的眼睛。
“这个契机,就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