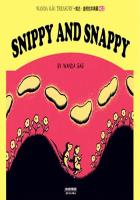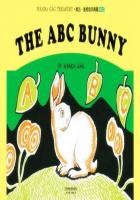“可惜的是,林清还没有把话说完便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他的双眼悲愤地望着天空。”
李夫人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她取出手帕擦拭汹涌而出的泪水,哽咽着往下说。
“我的祖父说,多数华工在死去后仍然睁着眼睛,因为他们备受屈辱与摧残,他们死不瞑目。我的祖父伏在林清身上放声大哭,其他的华工也都泪如雨下,这样一位有着菩萨心肠,对大家嘘寒问暖的手足兄弟;这样一位仁心济世、技艺高超的中医就如此被眼睁睁地害死。我的祖父拼命地拍着坚硬的岩石,边哭边说,‘林兄弟,你安心上路吧,你早日回到中国去。我一定将古钱带回中国,即使再苦再难也万死不辞!’
“对于林清的死,华莱士是毫不以为然,他没有表现出一丁点儿愧疚和不安,相反,他嘻嘻哈哈地同打手们去旁边的工棚里饮酒赌钱,他们恬不知耻的嬉笑声和吵闹声像一把把尖刀在割着华工们的心,要不是惦记林清的嘱托的话,我的祖父一定会冲过去同他们拼命。
“我的祖父和华工们将林清埋在了合恩角附近的山巅上,这样他每天能够没有阻挡地看到日出,那轮温暖耀眼的太阳正是升起于东方。
“林清的坟很简陋,小小的石块垒起的圆堆上只插着一块用旧枕木做成的墓碑,华工们都不识字,西马克太太请人在上边刻了四个英文字,‘圣人林清’。西马克先生在墓碑下边摆放了一瓶上好的威士忌酒。
“我的祖父牢记林清的嘱托,将那枚古钱妥善带在身上,日夜都不离身,他认真地端详过这枚古钱,这只是一枚普通的铜钱,但我祖父猜测这一定是林清受之于父母,从小就佩戴的长命锁,或者是陪伴他多年的信物。相隔滔滔重洋,这是林清身上唯一能带回去的东西,也是他在世间唯一的见证,因此我的祖父格外诊视它,每天临睡前都要用手摸一摸或者拿出来看一下,生怕有什么闪失。
“最让我的祖父和工友们为难的是他们不知道林清的家乡到底在什么地方,听林清的口音他好像是山东人,他也曾经提起过自己是山东人,但山东地广物博,究竟将铜钱送到哪里仍是个难题。
“尽管如此,我的祖父仍然下决心要完成林清的遗愿,将铜钱带回中国。也许是我祖父的忠诚感动了上天,也许是林清的魂魄在暗中保佑,总之,我的祖父竟然平安无事地活了下来,开凿长达1600英尺的唐纳隧道时他没有被塌方活埋;修筑漫长的犹他大盐湖铁路时他没有被沼泽吞掉;铺设内华达地区的路基时他也没有被雪崩压死。他虽然伤痕累累,形容枯槁,但是奇迹般地活了下来,直到最后一根道钉在太平洋铁路的路基上时,他仍然活着。而像他这样活到太平洋铁路竣工的华人不足三分之一。”
我深深地低下脑袋,我感觉自己的身上背负着全美国的债,我们欠中国人的太多太多。
故事还没有结束,李夫人接着说,“修筑完铁路后,我的祖父和工友们原以为能够带着用性命和血汗换来的为数不多的工资踏上归家之旅,他们没想到的是,此时的中国内忧外患,雨雪交加。国内经济凋敝,战祸不断,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只顾着维护自己摇摇欲坠的统治,根本无暇考虑流落在海外的中国劳工。而唯利是图的美国船运商人趁火打劫,大幅度地提高船票价格,轮船公司并没有向华工提供舒适的座位,他们在原本就狭窄的船舱中再加夹层,留给每名华工的空间只有一尺多,在这样的船里,华工们只能‘日则并肩叠膝而坐,夜则交股架足而眠’,即便是如此恶劣的条件,轮船公司的白人们制定的船票价格也高得吓人,华工们用两到三年不吃不喝挣来的钱才能勉强买一张这样的船票。
“火上浇油的是,当太平洋铁路修筑完毕后,白人们觉得华工再没有什么用处,他们害怕华工会挤占自己的就业机会,于是想方设法地要将华工全部赶走。忘恩负义的白人们出台了一项针对华工的政策,要求他们每人交纳一笔人头税,这些钱对任何一名华工来说都是一笔难以想象的天文数字。华工们陷入了回国无门、留美无路的尴尬境地。然而,噩梦其实才刚刚开始,卸磨杀驴的美国政府接下来又出台了极其不公平的《排华法案》,法案规定10年内暂不接受华工移民,并且对非美国出生的所有华人后裔的国籍不予承认。
“法案实施后,原太平洋铁路工地上的华工被无条件全部解雇,而挑三拣四、拈轻怕重的白人们又担心吃苦耐劳的华人会抢他们的饭碗,提出了‘不给华人一个工作机会’的口号,处处煽动对华工的仇视和排挤。
“身无分文的华工们找不到新的工作机会,只能成群结队地沿着自己修筑的铁路流浪。他们当中的相当一部分孤苦无助地沿街乞讨,没有机会再看一眼年迈体衰的父母和阔别多年的妻儿就抱恨而终。
“即便是如此,白人们也不肯善罢甘休,恩将仇报的白人居民不断制造暴行,他们嘲笑华工愚昧丑陋,侮辱华工是不讲卫生的、没有进化好的劣等人种,将他们背后的长辫子称为猪尾巴。有些穷凶极恶的白人暴徒干脆暴力攻击华工。当年,在怀俄明州的石泉镇,150多名全副武装的白人围攻华人,向他们开枪射击,28名华人被射杀和活活烧死,而围观的白人们却拍手喝彩,甚至参与抢劫。在丹佛市,姑力煤矿以及阿拉斯加等地,这样的暴力事件层出不穷。
“我的祖父也成了投国无门、无家可归的流浪者。”说到这,黯然神伤的李夫人情不自禁地往一旁的书架中望去,我才发现那里摆着一个精致的相架,相架中镶嵌着一张陈旧的一寸相片,相片上是一位气宇轩昂的留着长辫子的中国人,我猜他一定就是李夫人的祖父。
“我的祖父直至最后一刻都在构想着如何回到中国,因为那里有他朝思暮想的父母,有他魂牵梦萦的家乡,还有林清临死前留下的重托。我的祖父千方百计地积攒船票钱,为此他不惜再次忍辱负重,为白人搬运沙石,充当廉价的苦力。
“祖父饱尝冷暖辛酸,在艰难的岁月里,他同一位华工的遗孀,也就是我的祖母结下了感情,并最终成为患难与共的夫妻。他们含辛茹苦,期盼着早日结伴回国。
“祖父和祖母万万没有想到一天深夜里发生的事情永远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并且永远使他们分开了。
“那天夜里,一伙手持刀枪棍棒的白人闯进华人居住区,这一次他们没有纵火焚烧房屋,而是绑架和劫持青壮劳力,他们在加州就发现了一处金矿,需要大量的人手去凿矿淘金,好逸恶劳的白人当然不愿意亲自动手去干这些苦活,他们再次将眼光投向了憨厚朴实的华工,而且这一次,他们根本就没打算支付工钱,也没有计划让这些华工们都回来。”
李夫人闭上双眼又睁开,虽然她没有亲历当时的情景,但我相信,那段经历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场噩梦。
“由于有种族主义的支持和排华法案做后盾,白人资本家门变得肆无忌惮,他们随心所欲地奴役驱使被绑去的华工,华工们的劳累程度比起修筑太平洋铁路时有过之而无不及,华工们受虐待的情况更是骇人听闻,用九死一生来形容他们的悲惨境地毫不为过,短短两年间,一大半华工就魂丧异乡,侥幸活下来的寥寥无几。
“我的祖父大难不死,在白人们发了大财后,终于回到了原来的居住地。不过,两年地狱般的生活让原来身强体壮的他变得形如槁木,他不仅因饱受风寒而染上了严重的肺病,还在凿矿中失去了三根手指头。”
李夫人站起身来,走到书架跟前,小心翼翼地拿起相架,用手指轻轻拂了拂覆盖在相片上的原本就一尘不染的玻璃,泪水险些砸在了上边,“这是我的祖父留在世间的唯一的一张相片,它原本粘贴在祖父的护照上。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的祖父,所有有关祖父的事情都是从我的父亲那里听说的。不过,我深深为自己有这样一位祖父而自豪,因为他即使丢失了自己的手指也没有丢失林清临终嘱托的铜钱。
“由于当初白人匪徒是突然闯进家中的,祖父没来得及将铜钱交给祖母保管便被绑架走了。在金矿充当苦力的那两年中,他千方百计地藏匿这枚铜钱,为了避免铜钱被喜欢惹是生非的白人抢走,他甚至一度将铜钱埋在一块做了标记的大石头下边。
“白人们得到了大量金灿灿的金砂后,再也顾不上那些被他们压榨得气息奄奄的华工,到城市里去寻欢作乐。祖父终于抱着残破的身躯回到家中。
“实际上,这个地方已经不能再称之为家了。祖父和祖母原先居住的那个自己搭建的简陋的棚屋早已经荡然无存。最令祖父难以接受的是,善良贤惠的祖母因为饥寒交迫患上了重疾,已经去世将近一年了。万幸的是,祖母留下的遗孤,也就是我的父亲,被好心的华工同胞收养,马上就会开口说话了。
“原本就病骨支离的祖父再也经不起这样的打击,他肝肠寸断,浊泪纵横,当晚就倒在了病榻上,祖父的肺病愈加严重,持续的高烧令他神志不清,即便是这样,他在昏迷中仍念叨着祖母的名字。
“华工同胞们竭尽所能,想要挽救祖父的性命,然而穷困交加的他们根本无法凑齐足够的钱去买昂贵的药品,那些自以为是的白人医生也绝计不会为一名华人看病。
“祖父自知来日不多,他伸出残缺不全的右手,最后拉了拉我父亲稚嫩的小手。我的父亲还不满一岁,望着床上躺着的这位头发蓬乱、形容憔悴的陌生人,他不但没有因为害怕而哭闹,反而咯咯地笑出声来,这时候,祖父也宽慰地笑了,这是这么多年来,他第一次露出这么幸福的笑容。祖父含着热泪,向抚养我父亲的华工同胞们抱拳行礼,感谢他们的大恩大德,那是闯荡江湖的中国人的最高礼节。祖父恳请大家能继续抚养我的父亲,以免他夭折在异土他乡。华工同胞们纷纷表示纵使自己身陷绝境也要将这位可怜的孤儿养大成人,因为他是华工留下的根,他是中国人的血脉。祖父再次流下了感激的泪水,他努力张开了布满血痂的嘴唇,用微弱的声音告诉大家,若有来世一定做牛做马来答谢他们的恩情。他挣扎着又撕开自己的衣衫,有气无力地指了指脖子上戴的铜钱,他还有最后一件事情不能放心,那就是林清最后的嘱托。
“华工同胞中有一位知道这枚铜钱的来历,因为当年他就同祖父以及林清在一起修筑铁路,林清离世的时候他也在场。他握紧祖父的手,许诺要代替祖父完成林清的遗愿。
“祖父努力点了下头,再次叮嘱工友说,‘我愧对林清兄弟,不能亲自将铜钱送回他的家乡了。赵兄弟,此项重任只能拜托你来完成,一定要将铜钱带回中国,它是林清兄弟的魂,落叶归根,林清兄弟也要魂归故里。倘若不能了结林清兄弟的心愿,我在九泉之下也会万般不安的。赵兄弟,切记林兄弟之遗嘱,多多保重,回到中国,白人的土地上永远扎不下我们的根。’
“那名赵姓的华工正要接过林清留下的铜钱,这时候,棚屋的门突然被打开了,从外面风风火火地闯进一个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