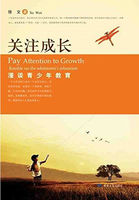山的瑰丽,小树的精神并不完全占去我童年的记忆,如果说山壁上那棵小树铸造了我的性格,赐给我顽强和勇气,那山道上的老人在我幼年的心灵又留下一种更可贵的东西,它令我至今仍产生着一种殷切的渴望。那老人便是我的祖母;一个红军团长的遗嘱,她不去城里住高楼,要求留在八葵山道上烧施茶,在夏天向过往行人免费供应,幼小的我,每到夏天几乎天天都要去祖母的茶棚,那茶设在山腰,棚里垒有石桌石凳,棚顶用树皮和茅草搭出一大片阴凉,山风悠悠,蝉鸟和鸣,潺潺溪流别有一番景象。每当汗涔涔的路人经过时,祖母便举着竹筒制成的茶杯,热情地招待来人,为他们盛茶。她那里备有凉茶、温茶,也有刚泡好的鲜茶,虽是粗大的叶片,它却带着山的气息,拌着竹杯特有的清香,叫人喝着滋润凉爽。我见祖母从不收取分文报酬,偶有陌生的过客坚持付费,我听祖母总是耐心地说:政府已经给了我许多,用不完哩,这茶算我替政府做了工作,免费的,再收费就对不住国家哩。直说得来人满脸的感激。其实我知道祖母是很不富裕的,两件瓦屋很破旧,夜里从不点油灯,总是用山上采来的松香油照明,蚊帐被它熏得黑尘尘的。那时候我太小,不明白祖母为什么这样做,常眨着迷惘的小眼睛。
许多年后,祖母仙逝了,临终前她把平时省下的一千多元抚恤金交了党费,我才知道她是党的人。祖母仙逝八年后,我也走出了山的襁褓,成为一名军人。我虽然走出山外,祖母也无法再生,可祖母的话在我记忆里翻滚奔腾,祖母的形象在我心中亦似清晰的影印,使我对荣誉和金钱显得淡漠,对同志对朋友格位真诚。在南方战火如荼的日子,我曾冒着炮火咬紧牙关从阵地背回一个又一个伤员,把阵亡的同胞抢回三八线,在迷失方向、水尽粮绝飞面对死亡的威胁时毅然献出身边仅有的半盒饼干。评功会上我把勋章送给了殉难的兄妹,荣誉证安放在麻栗坡烈士陵园。
我万分地感激祖母。
我真诚地感谢大山。
当我疲惫而思懈怠时,我的耳边会有山鸟的啼鸣:莫坐莫坐,快快收割。我便立即忙碌起来,不虚度这短暂的人生。
扁柏赞
战友?你可曾见过扁柏?我不仅见过,而且由于从小就和它发生过联系,对扁柏还有着特殊的情感哩!
几时村里谁家办什么喜事,少不了要上山采一些扁柏扎彩门,说它是四季常青的象征。腊月三十,母亲总要采来一束扁柏插在门垛上,说是迎接新春。我睡的摇篮架就是扁柏树做成的,又美观,又结实,陪伴我渡过了幼年。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大了。我开始懂事了。我对扁柏的感情也就加深了一层,我渐渐发现了它的生命力具有令人敬佩的特别性格。你看它,有的生长在岩缝中,有的生长在乱石丛,有的生长在河畔村头,无论生长环境条件如何,扁柏都以顽强的毅力,发展自己的根系,壮大自己的躯干,同顽石,寒冬酷夏作斗争,长大成树,造福于人。
随着一年四季的变换,扁柏却不赶时髦,四季常绿,有不怕旁观者讥笑的精神。你看那生在扁柏旁的枫树,春着浅蓝褂,夏穿绿纱衫,秋换红绸,冬改黑绒衣。你看那婀娜多姿的河柳,常常拂着长袖,像是对扁柏炫耀说:你看我多神气,哪象你一年四季一套黄羊皮。可扁柏不仅视而不见,反而为自己的朴素打扮感到骄傲,自豪。任风吹,任雨打,任日晒,任雪飞,它永远身披绿装,昂然屹立在大自然分配给自己的位置上,毫不动摇。
扁柏,我赞美扁柏,任凭在天南海北,高山峻岭,它始终朴实无华,不苟求生存的条件,只要需要就扎根。啊!战友?你见过扁柏吧?它的性格,它的精神,它的打扮与谁能相比拟?你一定会想到这个问题。
让我们都做一株常绿的扁柏吧,让它那乐于奉献的精神,永远驻在我们的心里。
村头树
我爱家乡的村头树。
我们山区的农村,过去每个村头几乎都有一株、两株古杉、古柏、古枫之类的参天大树。远看,苍劲、气派。近瞧,幽森、壮观。使村庄显得古朴而又庄严。
冬季里,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把背靠树根、面朝太阳谈天讲古视为莫大的快事。
夏天里,一些年轻人把在树荫下弈棋、抹牌、吹笛、摔跤作为既定的场所。
特别令人酥酥心醉的是:秋天,八月十五。春天,正月、元宵。每逢这些农家的节日,村里的青年们便巧妙地利用树的躯干,选择枝桠安起秋千。如磨麦秋、二人转、六人秋,名目繁多,花样新异,只要哪个村庄风光秀丽,秋千安装巧妙,就说明哪里殷实好客,小伙子精明能干。方圆好几里的姑娘就会一传十、十传百地邀伴前来凑热闹。于是乎,树荫下又悄悄地作着别的用场——幽会场。村里情窦初开的小伙子们都有意穿起一身崭新的衣裳,格外耐心地守候在千秋旁。热情地迎接姑娘们,争着把秋千上的客人荡过自己的头顶。细心的姑娘们,受到主人的殷情款待,口中不言,心中惬意甜蜜。姑娘若是看中了谁,文秀的暗暗记在心里,只消偷偷地多看一眼,那颗萌动的芳心就会被那个小伙子牢牢地摄住。泼辣的则明目张胆地欢叫,给荡高点,我不怕。那心花怒放的小伙子有的是力气,使劲地荡着,小心地护卫着。一上一下,眉眼相对,那情那爱便在其中了。过不了一年两载,一支洞箫,一束鞭炮便伴随着姑娘的脚步,朝着古朴、兴旺、百鸟啭林的村里缓缓而来。
十年浩动是国之厄运,民之厄运,也是树之厄运。千年青松,万年古柏,自然逃不脱那破古立新的大扫荡。一时间,锯拉斧砍,血楂四溅。数不清有多少老人落泪,记不全有多少姑娘、小伙惋惜。村头光秃秃的了,乡村显得孤寒贫瘠,冷落萧条。欢闹的场面再也没有了。
但是,恶梦醒来天破晓,春风又绿江南岸,前年探亲回家,我看见各个村头都新栽上了树,农村又呈现着一派繁荣,富足的升平景象,荡秋千的古老传统又被青年人们兴起来了,嫩小的树苗自然不能供作秋千架,然而那株株新苗凝聚着父老乡亲、姑娘小伙子们的深情挚意,寄托着他们殷切的希望,美好的理想。
我盼望村头树快快长大,我问一位老伯,这些树得几多年才能长大?他笑吟吟地说,快哩,这现在国态平安,风调雨顺的。我们赶不上,你们年轻人是能享用到的。
这一晚,我做了一个梦,梦见那村头的小树苗大节大节地猛长着,瞬息间,躯高叶茂浓荫覆盖着一座座村庄,脱尘典雅,古朴清幽,仿佛是健壮憨实的卫士,庄严地守护着乡村的富足和安宁。
尘封的日子
独自走出山寨,又孤独地回到起点。一去两年,我用青春赌明天。一片汪洋都不见。昔日的恋人离我而去;旧时的朋友侧目而视,无奈的我面对这冷酷的现实,真不知该怎么走向明天。
孤独的日子,安守本分。我不敢奢望有什么奇迹会出现;或独立寒窗倾听寨子里儿童朗朗书声,或目视苍穹任日头落进西山那道叉子里。心灰意冷,多么渴望能找到一点热情,哪怕是针尖般小的温馨。翻开从南方打工带回的笔记本,碰巧是辛弃疾半首诗篇:绕床饥鼠,蝙蝠翻灯舞,屋上松风吹急雨,破纸窗间自语。那份凄凉更似冰砖敲磕我那流血的心。
一挥手,那本子被我抛出窗外,只听见一个沉闷的响声。不知过了多久,那本子竟奇迹般又出现在我窗前;随手翻开莫让时间毁灭青春,珍珠的光华在痛苦中孕育。两行红字立即映入我的眼睑。字迹婷婷纤娟,宛若妙龄少女。我的心颤了,依稀记得那天窗前闪过霓红衣,我隐隐听寨里人说过,村小学新来了一位女教师,莫非是你?
我怎么也不敢相信,当窗前的小路无疑是通向学校的小径。从此,我在黑暗中不知渡过多少睁眼之夜。直到你告诉我你早已知道这山中有一个高考落榜、外出被骗的我,我激动不已。你说过:男人应该有气魄有志气。你给无望中的我,如同注入了希望的清泉,冷却的心被你唤回春的绿色。我从此变得开朗活跃,重新感到生活的纷呈,事业的绚丽,前途的光明。
而今我被山外一家报社聘用。我永远不会忘记你那友谊的阳光曾照耀我走出了沼泽与泥泞。尘封的日子你给我的温情时时温暖着我的心。孤独中常伴有你激励我时温柔的倩影。如今我离你远去,内心是那样的惆怅与悲哀。今生今世,我要把你给我的温馨化作忠心献给祖国,化作孝心奉给父母,化作信心留给自己,化作恒心付给未来。
带着你的温馨走出山寨,你是我心中不落的云彩。
施茶
那时我还小,小得不谙世事。
夏天到来,到垸下的李婶每天吃罢早饭背上一口黑灰灰的铁锅,提着一只笨大的木水桶,桶里放了些用竹子锯制而成的竹勾儿,新的旧的、黑的黄的,竹勾儿上安的是竹柄,竹柄横在竹筒中腰,或是在竹筒子当腰凿出一条横糟,或是在筒子的腰肚上挖两个对穿眼,然后拴一根合适的竹柄,怏怏地出了门,我很是好奇,便扯住母亲的衣襟问:大呀(山里人叫母亲叫大)李婶每天背着锅去做么事哩?母亲一听眉宇间皱起许多细而且密的皱纹,显得悲悲切切的样子,指着那一步步极其艰难地在对面山道上躬身爬行李婶的背影小声说:伢哟,小声嚷哟,叫李婶听了多难过呀,她是去大脚山上给路上烧施茶行善积德,求天上送子娘娘送她一个儿子抱哩。母亲说到这里,不由自主地将我搂进怀里亲了又亲,然后带着甜蜜和满足折回屋里。我呆呆望了那李婶很久很久,心里产生了一个疑问:烧施茶天上的送子娘娘真的送她儿子吗?多少年过去,我总没有忘记这事。
那时上学,我每天都要从大脚山翻过,一到夏季便会看见李婶在山腰给路人烧水,还办了一个茶棚。那茶棚建造极其简陋,在路边垦凿出一块平地,四角埋下四根杉杆做棚柱,杉杆上端横绑些木棒子,黄树条,竖置些被剖开的竹片子,一横一竖不繁不乱,显出一个个齐整的方格,算做这茶棚的脊顶,再割些茅草均匀地铺在脊顶上,用些杂木压稳,扯了青藤绑扎一番便大功告成。大都是就地取材,不花金钱。棚下便是一片荫凉之地,棚主人就在棚子里垒上石灶,搬上石凳,摆下竹沟,烧上茶水。不论南来北往,不论乡亲还是陌生路人,只要走进茶棚,棚主人就会热情地为他们端来茶水。那山上茶棚还不只是李婶一家,讲究的人还备有凉扇,让来客歇荫扇汗驱蚊。有的棚主还另砌有炉灶,备上柴火,专供那些远道路人生火做饭,尽情地享用,棚主并不以此向路人索取分文报酬。尽管喝茶,多少不限,只需临走前向棚主道几句吉利言语,棚主便十二分的满足,后来我听大人们说,那叫做烧施茶,大概是带有施舍之意。那时我上学备作午餐的麦粑儿,就常常在半路这些茶棚里一早就去和着茶水咽了下去,中午便守着书本吮指头,课没有上完,心早已飞下山去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渐渐对施茶有了新的认识和了解,施茶在我们山区是源远流长的,有人说它始于清朝,有人说是起于末代黄帝登基,也有人说是自有八路军那年兴的,这些是无法考究了。茶棚的主人无偿地给路人提供方便,有人又说他们是用这种默默的行为去感到上帝,这些烧茶的棚主命运不济,或膝下无子,或中午丧偶,或终年泡病。他们在争取菩萨保佑,虔诚地企盼神灵赐福于斯,消灾增福无子得子云云。我留心良久,果然那些烧施茶者总有些不尽如人意之处,或丧偶或少子。我却想这不过是自古而流传的山里人的一种美德,自觉为他人做点好事而已,要说是迷信,我却不信。李婶烧了多年的施茶却不见上帝送给她一丁一女。
不过,李婶本来是有儿子的,我读小学二年级那年她怀过一孕,施茶烧得更起劲,不料那年山里也兴起了红卫兵,红卫兵喝完她的茶水后踢了她一脚,说她搞迷信,砸破了铁锅,棚也被拨了,石凳子从山上滚到山下,幸亏她是贫农才免了游山批斗,两天后她流产了,再也没有怀上。自那年后,在我家乡的山道上再也看不到施茶棚了,几十里山道,人们默默地去又默默地回,那些挑脚送货,上山砍柴的,南来北往的路人再也没有凉爽的石凳,茶棚可坐,只有随便找了一片树荫,独自扯起衣襟扇汗,常得见他们张着干渴的大嘴,呼哧、呼哧直喘粗气,那俨然是一声声悲愤的叹息。
后来我参军,退役,进城工作,十八个年头逝去,多次回到那肥沃的山野,再也没见过一座茶棚。
想不到今年初夏,我又喝到了那大脚山的施茶,那茶棚建在山顶,是用红砖蓝瓦盖成的,茶棚的主人竟是一个二十才出头的年轻仔。他见我气喘吁吁上得山来,热情地把我迎进他的茶棚,还微微躬身打了一个请的手势,让我坐在一把油漆过的靠椅上,然后飞快地递上一条毛巾,送来满满一杯茶水,玻璃杯还安然躺倒着几片草绿的山茶,清香宜人。我被他的热情所感动,顿觉旅途的疲劳消失在他这种美的举动和热情中。待稍稍息汗,我们便攀谈起来,稍一提话头,他便知道我是占嫂的大儿(我母亲姓占),可我对他却不认识。我们聊了一阵,他的话头很快跑到我工作的城里,我发觉他热衷于打听城里各路生意行情。看来他是不少上城的,我一边品着山茶,一边认真地向他介绍城里情况,当我说到山里农民恶狠的,喜欢在田埂上穿洞的黄鳝,如今是城里人酒席上的珍贵菜肴时,我见他的眼睛异常光亮,脸上生出某种难抑的喜悦和激动,叫我直觉得他十分可笑,心里甚至为他悲哀,山里人啊,究竟是少了些见识,城里人把黄鳝当成珍肴有什么惊奇?临走时我习惯地摸出几个硬币却被拒收了,他说这是施茶不收费,忙活了半天他只落下我几句并不得体的客套话,诸如麻烦,打搅之类,他反倒很是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