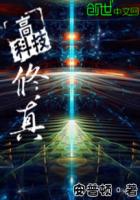弓白拾了那书简,回了书院,见了弓愚。
“父亲,这书简中说了什么”。
弓白虽然年幼,毕竟儒门之后,一身儒家仪礼自是不曾亏缺半分,因此也不曾拆开书简,见过其中内容。
弓愚仔细打量了一眼弓白,摇头叹道:“李老果然不凡,一语中的”。
此时弓白一头雾水,呐呐问道:“父亲,这是何意?”
弓愚闻言,却是陡然间舒展双眉,温语一笑,“此简乃是李老所留,并言及我儿性格孤鹜,言行似剑,日后恐怕有刀兵之祸,劝勉为父,须令我儿谨言慎行,多修儒术。罢了,你且观上一观吧”。
言毕,便将那书简递到弓白手中。弓白也不迟疑,谢过父亲,随即打开,只见竹简中,仓促的写了几句留书,原文如下。
敬文生先生安:老朽去岁多劳先生费心安置,已有半载有余,此番仓促,未及面辞,心中实有愧疚,望先生雅谅。此间缘由,非老朽不与先生得知,实为心有苦衷,若后日有期,老朽必有厚报。另有一言,望先生得知,令郎聪慧灵敏,异于常人,日后必为名宿大儒,然今天下大乱,恐令郎意正难屈,易生口舌之祸,不适于世,望先生留心。
书简末端,没有留名,论笔锋口气,便是那不辞而别的李仆无疑了。
弓白一头雾水,问道:“父亲,这李老在綦水已住了半年,为何如今又一声不响的走了?”
弓愚笑道:“乾为天,坤为地,乾坤宇内,何其浩瀚,吾欲东往,便可东去,吾欲西返,便可西归,何必烦恼?且人各有志,随他去吧”。
弓白道:“父亲说的是”。
弓白默默的下去了,让他感到惆怅的是李归,在这个年纪来说,李归算是一个不错的朋友,起码弓白唠叨之乎者也的时候,李归不会同他争辩。当然,他也不会因此而悲伤许久,毕竟年少,心性稚嫩,在这个时候,能够让人记住十年、二十年的东西,毕竟是少的。
时间,总是过得很快,也容易让人忘记它的流逝。
当弓白年岁稍长,渐渐忘了当年的李归是谁的时候,也不过是过了两年,弓白十岁,也就是昭和十一年。
天下九州依旧战火连天,入蜀地求仙问道的人越来越多,逃入蜀地的流民也越来越多。周天子渐渐失势,诸公侯对周天子也渐渐地开始不理睬了,甚至有流民传言,一些军力强盛的公侯已经开始准备筑台告天,称王祭表了。诸公候的朝觐、纳贡越来越少,最后干脆断绝了,周天子终于意识到周王室的衰微,开始在周王都“奄”之东的鹿台祭天,一开始是岁祭,即腊月时祭天,后来干脆改为四时,旧时春搜、夏苗、秋狝、冬狩,为天子大祭,如今更为春服、夏祝、秋祈、冬祭,宫寮子谏曰:佞臣为乱,必自及之。
蜀地毕竟处于九州之外,论其富庶,不值一提,乃荒僻之地,山中农户,多以打猎为生。是以在《周礼》中,尚且处于蛮、夷之外,只堪为镇、藩一等,在九畿:候、甸、男、采、卫、蛮、夷、镇、藩之中,为最下等的穷苦之地。但凡是有其弊,必有其利。蜀地之中,虽然穷困,却远离战乱,山民得免兵祸之苦。
昭和十一年腊月。
蜀地的山民砍柴、打猎、捕鱼,早已备好了岁末的储粮,静待来年的暖春。虽然山道难行,却也有野商往来,蜀中或山外的野商在岁末的时候,往往组成商队,入蜀换些山珍锦裘,再回返荆州贩卖,一往一返,常常获利不薄,如有福运者,更可寻得山中美玉,献与公侯,所得财币,便更不止千金之数了。綦水一地位居剑门关,乃入蜀必通的要道,闲暇时,便多有山民做些野商的生意,自然也相较蜀中富庶一些,因此,衣食倒也无忧,便是这綦水中,自称儒门弟子的书院教书先生,也是二十年前,方才迁入此地。寻常山民,手中或有富余的闲钱,便将家中幼小,遣送来学些字画,听听先生讲授的见闻,每逢这岁末之时,有客人来访,便吹嘘家中幼小如何如何,偶尔听来,也算一件趣事。
腊月的綦水,山风往往带着风雪,积寒之下,自然相较中原,也更为寒冷一些。其中缘由,便是蜀中山高,云雨丰沛,一年四季少有干旱,因此而多雨水,寒意更深。
在剑门关上,自蜀中遥遥走来两个男子,一名女子,沿着蜀中的小道,踩着皑皑白雪,向綦水慢慢走来,脚下咯吱咯吱作响,偶尔伴随几枝枯枝断裂的咔嚓声。那女子身着一身白衣,横簪披发,似作男子打扮,走在行首,身后两名男子,俱为青衣宽袍,头梳发髻,缚剑而行,细细观来,竟是三个道人。
剑门关南北两峰几近百丈,那三位道人走近之后,于峰口微微驻足,随后足尖微点,便飘然跃至剑门关之上。
“无牙,此地便是綦水?”
“禀师姐,我久居山中,却是不清楚,此事还需问留松”
“禀师姐,此地为剑门关,以此往东再过二十里,便是綦水了”。
“既然如此,那便走吧”。
三人言语简单,话音一落,便飘然而下,竟不用栈道,亦不用渡船,凌空踏步而下,如春红入水,浮于流水之中。
綦水,书院中。
弓愚正于院内温书,此时天寒,到了未时,便授业完课了。正看到《周礼·冬官》,吟咏间,忽然听见门外传来几声轻缓的叩门声。弓愚收了书简,望向缘炉而坐的弓白,道:“小白,且去看看,何人叩门”。
弓白应了一声,搁下书简,起身前去。此时寒意正浓,弓白心中自是不大愿意,未及宅门,便扬声高喊:“门外何人?”
叩门声依旧,却无人答话。弓白心中诧异,脚下却不曾迟疑。
书院的木门有些老了。嘎吱一声,门开了。
弓白一愣,门前站着一男二女,竟是陌生人,那后方二人如何,弓白不曾注意,这门前的女子,却丰姿绝伦,只见:眉如秋月,目似霜星,额中一点朱红如剑,唇口熏红,鼻若琼脂,一身白衣道袍,更觉天下无双。
弓白口舌迟钝,一时不知如何开口,木然道:“这位仙子,你来我家,所为何事?”
话音未落,弓愚自身后现身,见得三人,随即拱手施礼,道:“敢问三位,今日登门,所谓何事?”
那女子朱唇轻启,舌带兰香,“贫道今日登门,乃为了断一件俗缘,还望先生体谅”。
弓愚一惊,这女子虽然美色绝伦,但他自幼修习儒术,却也不会为女色所惑,更何况这女子自称“贫道”,想必是道门中人。
想到此处,弓愚问道:“鄙人自忖与道家并无恩怨,且鄙人自幼修习儒术,与道家亦无渊源,三位还请回吧”。
那女子微微一笑,侧身让步,却从后方露出一个人来。
竟是,李归!
“文生先生,贫道稽首了”。
“李家贤侄?你如今这是……?”
“贫道道号留松,前尘旧事,一梦随之,至于俗名,贫道已弃之不用了”。
“那…李家…贤……,留松道长今日登门,所为何事?”
“道境邈邈,人境惶惶,既成吾身,当绝六欲,今日此来,乃是为了了断当年此身家祖许诺先生之事”。
“留松道长误会,李老不曾有言许诺鄙人”。
“不然,此身家祖临终之时,曾有一言留世,若彼文生先生有求,唯我儿所报。此番正是为此事而来”。
“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