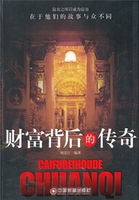就在这张报纸登过这条消息之后没几天,在它的第二版左下角贴地的地方,非常不起眼地登出了我们家与李玖妍断绝一切关系的声明,全文大概不到一百字,干脆利索,手起刀落。落款是“李德民唐亚蓉夫妇”。这真是一件叫人想不通的事,他们要一边吵架,一边讨论离婚,还要一起合伙登声明,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李文革起初走路时还是有点拐,不过走着走着就好些了。大脚趾确实接得不错,不是有点疤痕,从表面上根本看不出什么。但那毕竟是断了再接上去的,想跟没断过一样是不可能的,比如他不能跳,也不能跑,要跑只能慢跑,要跳也不能用那只脚,必须用另一只脚。就是平常走路,重心也尽量放在后脚掌。所以他只好收敛起顽劣,这样一来反倒成全了他,别人觉得这孩子越来越稳重了,而一个表面上看起来平和稳重的人跟权力似乎特别有缘,他后来做官做得比较顺,他这只再植的、外强中干的大脚趾功不可没。
李文革的大脚趾接上去了,我父母却离了,—我估计就是那个时候离的,最后合伙干了一把,登出了那份声明,将李玖妍像摘瘤子似的从自己身上摘掉了,断根了,剩下来的事情就是离婚了。所有的事情都做完了,不离干什么?一定得离了。非离不可了。
如今我回头看一看,就知道他们彼此之间的失望和嫌恶到了什么地步。因为我和我老婆张海棠也吵。我跟张海棠吵架主要原因在张海棠。我摇着轮椅去“海棠书店”时,好几次都碰见七罗汉趴在柜台上,用一只手撑着下巴跟张海棠说话。我一直以为这是个从她老家来的民工,可是这个民工每回见了我,都是匆匆忙忙地走掉。而张海棠这时候总是对我冷冰冰的,我便觉得这个民工有点蹊跷,但忍住了没问。张海棠没我忍性好,用那只好眼朝我翻个白眼,说:“想问什么就问吧,别憋着,憋出毛病来不好。”我说:“好人不用管,坏人管不成,问什么?”张海棠嘴一撇,像笑又不像笑地哼一声。有一回我正好碰见张海棠在抹眼泪,我就觉得再不问就不对了,我叫住低着头从我身边匆忙走过去的七罗汉,然后问张海棠:“他是谁?”张海棠先叫七罗汉走,等他走了以后,才对我说:“七罗汉。”直到这时,我才知道她跟七罗汉还藕断丝连。她说:“你也不想想,他要是不爱我,怎么会打瞎我一只眼睛?”张海棠性格里比较可爱的一面,就是直率,不隐瞒,想说时就噼噼啪啪全倒出来。她说七罗汉还爱她,而且爱得要命。她的逻辑很怪,七罗汉打瞎她一只眼睛,她把七罗汉送进监狱,他们互相残害,可她说这是爱。她现在正在为难,不知道是老老实实跟我过日子好呢,还是回头跟七罗汉好。我说:“你慢慢拿主意吧。”张海棠便抱起双臂,用懒洋洋的口气说:“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你巴不得我提离婚,你好马上就去找你那个拐婆子!”她说的“拐婆子”,就是在白马庙市场卖酱菜的苏晓晓。我淡淡地说:“彼此彼此。”
所以在我看来,夫妻吵架吵到没有愤怒没有激情的时候,那就是无药可救了。那种失望和嫌恶是无法言说的。虽然我和张海棠关乎的是“风月”(这样烂糟的事情,不知够不够得上这两个字),而我父母是因为在艰难的合作过程中都将彼此看透了,比用显微镜看得还透,都觉得对方太不是东西,或者看见对方就等于看见了自己,对方就是自己的镜子,于是从前的风花雪月―假如真有过的话―便不堪回首了,他们关乎的应该是人格或德行,二者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但结果却是一模一样的:离婚。
真到了一点不犹豫的时候,什么问题都不是问题,我和李文革当然也不是问题。我们的归属他们很快就谈好了:李文革归我妈,我爸则捡了我这个落脚货。
我妈原想带着李文革远离老鼠街,我爸也巴不得她早点搬出去,所以两个人都在忙着跑房子。可是他们腿都跑细了,不要说小街小巷边边角角,连郊区都跑去了,也找不到一间房子。房子都是公家的,都归各区房管局革委会管着,就算有空房子,也轮不到他们。这样的事我爸又不好去麻烦人家周师傅,他拉不下老脸开这个口,怕被周师傅捡了笑。到了这时候他们才明白,他们的婚等于白离了,他们还要在一个屋檐下进出,还要在一个锅里吃饭;而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已经离了婚,不知道我们已经成了两家人。
我知道我们一家人变成了两家人是因为我爸住院。那时候我爸已不在南杂店了,虽然他挖了那么久的人防地洞,回到店里没几天,人家还是又把他赶走了,让他到他们单位上办的五七农场养猪去了。他给别人打过那么多家具,给苏酒糟也打过,可是包括苏酒糟在内,都觉得他还是去养猪的好。苏酒糟还对他说:“老李,你想想,天天守在店里有什么好?去农场养猪多自在?农场那环境,山清水秀,空气都新鲜些,我是脱不开身,脱得开身我都想去。”我爸说:“那是那是。”单位上的农场设在郊区,往东三十里,不远也不近,他吃住都在那里。那天他忽悠忽悠地挑着一担潲水刚进猪圈,忽然感到胃里一阵翻涌,随即便哇哇地呕吐,结果这一吐就没完没了,大约半个钟头左右便要吐一次,最后连苦胆都吐出来了。胆汁是绿汪汪的。猪把别的都吃了,唯有胆汁不吃,嫌苦。在当地公社卫生院吊了几瓶盐水,把死人一样的脸色吊回来一点,也还是像一张在水里漂过的草纸,再试着吃了小半碗稀饭,还没过半个小时,怎么吃进去的就怎么吐出来了,吐完了又吐胆汁。公社卫生院的医生说,快走吧,别在这里耽搁时间了。于是第二天一早就搭一辆拖拉机回来了,在区卫生院一检查,人家说长了个瘤子,赶紧开刀吧。
开刀要家属签字,而这个字是我签的。那天上午我妈去上班之前,忽然想起什么似的对我说:“哦,对了,听说你爸要开刀,你到医院里去看一下,给他签个字。”我当时非常吃惊,一是为我爸开刀,二是为她说的话和她的口气。她用那种白开水一般的口气说你爸要开刀,又说你去看一下签个字,那么她呢?她干什么?我说:“我签什么字,你不去吗?”她摇摇头说:“我跟他离婚了。”我大约是一副又困惑又吃惊的样子,她看了我一会儿,便转身去翻出了他们的离婚证,递给我,说:“你可以看一下。”
我就看了一下。我看到了他们离婚的事实。就是一张比三十二开纸略小些的白纸,质地比较粗糙,因此白得很不纯粹,透着一抹糠黄。我看见在“离婚原因”那一栏里写的是“感情不和”(从表面上看,这与我日后和张海棠的离婚原因又是一样的),再往下我就看见了我和李文革的归属:我归我爸,李文革归我妈。至于李玖妍归谁,上面没写。大约也不用写,因为李玖妍已成人了,也嫁人了,而且我们家还登过报,跟她断绝关系了。我忽然有种冷飕飕的感觉。我有点理解他们“登报”,但一点不懂他们的离婚。把离婚证还给我妈时,我禁不住狠狠地抖了几下,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我拄着双拐挪到医院时,鸡皮疙瘩已经没有了,给我爸签字时,我已经无所谓了。
我爸的瘤子是良性的。知道死不了,他半张着嘴,两个眼角上各挂了一滴泪。
在医院里侍候我爸时,除了不要把屎把尿,我什么活都要干。我充分地利用我的胳肢窝和我的脖子。洗衣服时,我把要洗的衣服挂在脖子上,来到水槽边站定,把重心放在一根拐杖上,用胳肢窝夹死,将衣服从脖子上扯下来;打肥皂搓洗时,用两个胳肢窝夹住拐杖,将自己挂在拐杖上,好腾出手来搓衣服;又将洗干净的衣服再挂上脖子,晒衣服时基本上跟洗衣服一样,把自己挂在拐杖上。我还从家里翻出了一只书包,是李玖妍的那只洗得发白的黄书包,我把它翻出来之后心里怔怔的,我眨巴着眼睛看着家里的桌子凳子柜子箱子,看着墙和板壁,看着天花板,看着墙和板壁上贴的样板戏的画纸,看着我爸从前做的那九面小镜子,看着厚厚的无人掸抹的灰尘和零乱放置的瓶瓶罐罐,以及到处乱扔的衣服和鞋袜,竟莫名其妙地觉得有一把刷子在心里一下一下地刷着。那把刷子又粗又硬。后来我才知道这叫沧桑感。沧桑感是一种很不好的感觉,伤人,弄得人心里戚戚的,说不出哪儿疼,像掉了魂似的。我戚戚地往李玖妍的黄书包里放了一只篾壳热水瓶,放了两只搪瓷碗和两把铝皮调羹,又戚戚地挂在脖子上。
在医院里的日子,这只黄书包就像长在我脖子上,买包子馒头是它,打饭打菜是它,打开水也是它。打了饭菜往里面一放,打了开水也往里面一放,然后我挪一下,它就晃一下。它和我胸前的衣襟很快就变得斑斑驳驳的了。油渍和菜汤,以及东碰西蹭之后落下的尘泥污垢,使它们看起来就像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