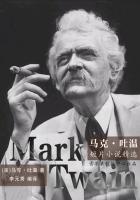所幸的是李玖妍的饭量终于减下来了,由三碗减为两碗半,又由两碗半减为两碗。饭量减下来之后,她就开始长肉了。我们看见她的皮在抻起来,骨头在往肉里缩,最明显的是颧骨,她的尖耸的颧骨在一天天矮下去,面颊在一天天丰满起来,到后来我们几乎看不见她的颧骨了。她的手也丰满起来了,无论是像男人的右手还是疤痕累累的左手,都浑圆起来了,连那几个断过的指头也在圆起来,疤痕都变得柔顺了,细腻了,不那么扎眼了。接着我们又看见她在白润起来,先是嘴唇,由灰紫而灰红;然后是皮肤,由灰黑而灰白;再就是头发,也在由灰黄转为乌黑。总之我们看见她在渐渐地清爽起来,白净圆润起来。但她的眼睛没有一点变化,似乎一块钱一斤的早米只能养皮肉,不能养眼睛。她的眼睛还是蒙着一层厚厚的无色的干灰,特别是被“监督管制”过后,灰得更厉害了;看人时更是战战兢兢,尤其是拿眼睛“刮”人,速度更快,嗖的一下,甚至比“嗖”还快,就把你给“刮”了。
也许是胖了之后看她顺眼一些,不管她的眼睛怎样,我都认为她是长得越来越像李玖妍了。只是她像李玖妍的时间不长,因为她胖得太快,长着长着又离李玖妍远了。她的脸比李玖妍大,肩比李玖妍圆,还有身子和屁股也都比李玖妍厚实多了。
看着她胖起来,我爸反而忧心忡忡,他现在满脸都是紧巴巴的皱纹,他的每一条皱纹都变成了细麻绳,他摇着他的被细麻绳捆得结结实实的脸,悄悄对我妈说:“她这样胖起来真成问题,又不是猪,她怎么能胖得这么快呢?”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她变成了一头猪,哪见过人胖得这么快的呢,只有猪才会胖得这么快,所以他又说:“你说不管她吧,她傻头傻脑瞎想,你吓她几句,不准她想事呢,她就把肉都长到脑子里去了,你说怎么办?”我妈反问他:“你问我,我问谁?”他便摇头叹气,什么话也没有了。
假如李玖妍真是一头猪还好,那就咬咬牙养着她就是了,无非是日子过得紧巴一些,大家少吃几口而已。可这是假如。那么现在李玖妍究竟变成了一个怎样的人呢?我绞尽脑汁,试图用一个词说明她,结果我用了无数个词:封闭,呆板,灰暗,蹇涩,冷漠,沉默,抑郁,胆怯、猥琐、不安……就像一大堆标签,抽出任何一张都可以往她身上贴,可是即便你在她身上贴满了这样的标签,也还是说明不了她。她跟每一个词都搭界,也就是说每一个标签都能说明她一点点,却又没有一个标签能准确地清晰地说透她。
她天天待在房间里糊火柴盒,我妈说妍子出来吃饭吧,她就出来吃饭;我妈说妍子,洗脸吧,她就出来洗脸;我妈说你脚也不要洗吗?她就坐下来洗脚;我妈又说你还没用水呢,她便从房门口踅回来,端了点水去房里洗屁股。连洗屁股这样的事都要我妈叫,我妈就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她猜她在枣树沟和八里铺都是不洗屁股的,她把洗屁股这件事忘了。她出来倒水时,我妈就问她怎么用水都要人叫呢,是不是在那里不用水的呢?
她不回答,站在那里,用眼睛飞快地“刮”了我妈一下。
总之我妈不叫她,她就闷在房里不出来。还好她耳朵一点没坏,我妈在厨房里叫她,尽管声音要拐几个弯,尽管她的房门和窗户都关得严严的,她都听得见。而且听见了就是听见了,她从不装憨,你一叫她她马上就出来了。她那个房间没有朝外的窗户,窗户开在拐进厨房过道的板壁上,本来窗扇上就巴满了厚厚的油烟,油烟上又巴着绒毛一样的灰尘,暗得发昏,她还偏要关死窗户,拉死窗帘。她的眼睛倒是好得出奇,在那么暗的地方还能糊火柴盒:我妈总想替她把窗帘拉开,把窗户也开开,好让房间里见一点光亮,换一点空气,可是我妈前脚走出房间,她后脚就把窗户关死,把窗帘拉上了。有时我爸说,亚蓉你喊妍子帮着干点活,别让她坐出别的病来。我妈说,要叫你叫,我叫烦了。
我爸就叫:“妍子呀,你出来帮着做点事吧。”李玖妍就打开一条门缝出来,低头站在那里,等我爸吩咐。我爸说:“看事做事呀,你没看到篮子里的菜吗,先把白菜拣一下吧。”她就拣白菜,拣好了,转身就回了房间。我爸又叫她:“你拣一下就算了?菜还没洗呢,你怎么不洗一下呢?”她就又出来把菜洗了,洗了,却又回房间去了。我爸只好再叫她:“妍子呀,菜洗好了不要切的吗?出来切菜呀。”她就再出来切菜,切了菜,也不放进筲箕里,就那样堆在砧板上。我爸皱起眉头在一边看着她,想说什么又忍着没说,只咽了一口唾沫。就这样,我爸叫了她几回,便没精神再叫了,说她是一颗算盘珠子,你拨一下她动一下,你不拨她就不动。我爸说:“我拨累了,拨不动了,由她吧。”
李玖妍最烦人的地方是不说话。她的嘴巴闭得紧紧的,不到非说不可,她绝不说话。有一回吃过晚饭,她进了房间,过了一会儿又拉开一条门缝,低着头走出来,垂着手站到我妈面前,说:“纸。”声音像蚊子。我妈说:“什么?”她说:“来了。”还是像蚊子。我妈愣了半天才明白过来,说:“哦。”赶紧去给她找了一沓卫生纸。
另外就是她非常怕人,见了人她就低着头溜着肩膀,一副养不熟的童养媳的样子,眼神看起来是呆呆的,可你总觉得她的眼睛里还藏着什么。她会藏起了什么呢?
除了上厕所,她几乎不出大门一步。她把糊好的火柴盒—大半是废品—用一个纸箱子装着,拿出来放在饭桌上,等我爸帮她去送货接货。若是我爸有事耽误了,她就在房间里枯坐着,我爸耽误多久她就枯坐多久。
她最难办也最叫人揪心的还是上厕所,每次上厕所她都像怕鬼似的,要先躲在门后面的暗影里朝外张望,目光低低的,看了半天,突然闪出去。老鼠街的公共厕所缩在巷子北头的偏巷里,巷子本来就拐了点小弯,还有小半条偏巷,所以从我们家门口是一点也望不到的。就算望得到也没用,老鼠街一带都是老房子,住的人家也都是普通老百姓,家里都没有卫生间,这么多人全靠一个厕所,厕所里的繁忙程度可想而知,李玖妍想趁没人时上厕所,几乎是不可能的。再说巷子里也总是有人的,而且多是老鼠街上的邻居。她最怕的似乎就是邻居,在众多邻居里,她尤其怕费伯娘,费伯娘老在巷子里晃来晃去,见了石头都想说两句。费伯娘说:“这是老李家的妍子吧?”费伯娘又说:“这孩子,你跑什么呢,我跟你说话呢!”她低头含胸,往厕所里一溜小跑。
只要看到巷子里有人,或者听到脚步声,特别是听到费伯娘的趿板子在呱嗒呱嗒地响着,李玖妍便躲在门后不出去。她十个指头绞在一起,死命地憋着,用大手绞小手,又用小手绞大手。两只手都有点痉挛,筋脉都鼓凸起来,骨节和疤瘌都充血泛红,有时候连身子也跟着战栗起来了。战栗会像水波一样在她身上走动,一波接一波,由指头到整只手,又到手臂,再到肩膀和整个身子。有好几回,她大概实在憋不住了,便像革命烈士舍命炸碉堡似的,灰白着脸往外冲。她习惯溜墙根,眼睛盯着脚尖,出门后便如壁虎般贴着巷墙根疾走,脚底下生出来的风居然可以带飞一些小纸屑。
有一天她连厕所也不肯上了。她躲在门后不敢出去。丁珠玉主任带了几个人在巷子里有说有笑地贴标语。我看见战栗又像水波一样在她身上走动起来了,她死死地咬住嘴唇,飞快地转身,从脸盆架下面拿过一个洗脚盆,躲到房间里去方便。洗脚盆是铝皮的,又薄,所以响声很大,而且立刻就有一股新鲜的厕所气息进入了我们的鼻孔。我妈循着声音和气息从厨房来到她房门口,对着那扇门吸鼻子,隔着门问她:“妍子,你是肚子不舒服吗?”问了几句,她一声不吭,连铝皮洗脚盆都不再发出响声。我妈朝天花板翻了个白眼,又敲门,叫她好了说一声,她好叫李文革去给她把盆子倒掉。
李文革一听就鬼叫:“我不倒我不倒我不倒!”
我妈说:“听话!”
李文革说:“不听!”一边说一边兔子似的往外蹿。
这时候李玖妍在房里轻声说:“好了。”我妈又朝天花板翻一个白眼,然后看着我爸,我爸便拉长了脸,说:“你看着我干什么?”我妈说:“革子不肯倒,你说叫谁去倒吧?”
我爸跟我妈练了几句口角,末了还是气呼呼地去倒了盆子,回来把盆子一扔,转身就出去了,买回来一个带盖的搪瓷便盆,哐的一声,重重地放李玖妍的房门口。
“便盆给你买来了,要用的话就自己倒,没人侍候你的屎尿!”
过了一会儿,李玖妍的房门打开了一条缝,一只灰胖的大大的手飞快地伸出来,飞快地拿过那只印着一朵糊糊涂涂的牡丹的便盆,又飞快地缩进去。
有了这只便盆,李玖妍就不用白天上厕所了。但我们就十分受罪了。我们越来越觉得她是个怪物。我们家的空气已经是非常糟糕了,我们闻惯了的药味被她弄出来的怪味盖住了。客观一点说,那股味道其实不是很重,再说也不全是她的味道,我们的红薯屁也还在空气里飘着,但我们怎么可能客观呢?我们就是觉得它很重很污浊,觉得全是她的味道。不是她,我们吃什么红薯?她的味道塞满了我们的鼻子。我们被它熏得皱眉皱眼。李文革还动不动捂着鼻子,拿另一只手给鼻子扇风。真正烦人的是夜静更深时―好像她故意把那些汤汤水水都憋到这时候―她在便盆里弄出来的声音不是一般的响亮,感觉就是一条大河。我们忍无可忍。李文革会用脚后跟猛敲他的床板,我也会拍打我的破竹床,或者用力翻身,反正就是故意弄出一串嚓扎嚓扎的破响。她还有一点自觉,我们这里一有响动,她那里便立即停下来,停了一会儿,没听到什么了,才又鬼鬼祟祟地再响起来,把一条大河憋成了一条涓涓细流。
这时候我就会听见从我爸妈房里传出的叹息,有时候是我爸,有时候是我妈。都是气声,很混浊的一片,跟李玖妍的味道一起,弥漫着在黑暗里散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