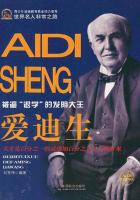昼梦
垂着纱,
无从追寻那开始的情绪
还未曾开花;
柔韧得像一根
乳白色的茎,缠住
纱帐下;银光
有时映亮,去了又来;
盘盘丝络
一半失落在梦外。
花竟开了,开了;
零落的攒集,
从容的舒展,
一朵,那千百瓣!
抖擞那不可言喻的
刹那情绪,
庄严峰顶——
天上一颗星……
晕紫,深赤。
天空外旷碧,
是颜色同颜色的浮溢,腾飞……
深沉,
又凝定——
悄然香馥,
袅娜一片静。
昼梦
垂着纱,
无从追踪的情绪
开了花;
四下里香深,
低覆着禅寂,
间或游丝似的摇移,
悠忽一重影;
悲哀或不悲哀
全是无名,
一闪娉婷。
——林徽因
一九三六年
穿百褶裙的少女
“徽音……徽音……这衣服可怎么穿?”
表姐曾语儿手中拿着黑色长袜和浅灰裙子,跑到徽音面前小声发
问道。
徽音正低头整理裙子的百褶,轻轻地将上衣拉平,盖住腰际的裙边。她纤细的小腿已经被黑色的长袜温柔地包裹起来,勾勒出笔直的线条。
“很简单的,这样将袜子卷起来……然后抬起脚,把整个腿套进去便是。”
“哦……也许是衣服的样式……总觉得有些奇怪。”表姐依旧皱着眉头,有些怯怯。
“哪里奇怪啦?我倒觉得很别致。中式上衣配西式百褶裙,既摩登,又娟秀。”徽音说着,快乐地踩着小皮鞋转了个圈。
发亮的黑色鞋子看起来精致而整洁,平整的上衣在袖口卷起秀气乖巧的白边,配着胸前项链上的培华女子学校校徽——现在这身装束让她满意极了。
“快换上吧,你身段高,穿上一定比我更好看。”徽音欢快地拉着语儿的衣角,轻声催促道,“我爹还叫我们各自穿好,一同去相馆拍
照呢。”
林长民自日本回国后,便一向事务繁忙,难顾家眷。先是在上海、浙江两地频繁奔走,后又由于在北洋政府任职,需要常驻,索性便将全家迁至北京,尽力照应。好在孩子们都算是懂事,并未因迁居而抱怨厮闹,也都乐得随遇而安——中国正处于这般风雨如晦的年代,即便她们是家境显赫的贵族少女,也生来便学会了习惯流离。
十二岁的徽音也就随父亲来到北京,同表姐妹们一齐进入了由英国教会办的培华女子中学念书。
今日便是徽音入中学的第一天,听完几位相貌庄严、神态恭谨的女教师的讲话,女孩子们就被分发了一样的制式校服,样式同她们过去常穿常见的衣服颇有不同。
“美丽的小佳人们,到这里来!”刚一走出培华女校的大门,就看见林长民正在一辆黑色的车里冲她们笑着招手。徽音同语儿表姐手牵着手,一同跳上了车子。
“真是好看。”林长民从前排转过头来,温和地称赞着。
“说你呢,曾小姐。”徽音戳戳语儿,小声说。
“才不是!一定是说我们最美丽的小林小姐。”语儿轻轻揪了揪她的发辫,两个小丫头嬉闹着在车里笑成一团。
林长民静静靠在车座上,嘴角带着不自觉的上扬。耳畔孩子们无忧无虑的笑声,让他的心里感觉到一种久违的平和。他知道,就在这车子外面,同样一座城市里,甚至是他现在视线所及、正被这辆车子渐次经过的每一条街道上,都充斥着太多动荡和不幸。
假如徽儿可以永远这般快乐,该有多好。
假如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年轻的少女,都可以这般快乐——正如年轻本该拥有的那样,多好!
不知不觉,车子便在相馆前停了下来,徽音同语儿牵着手跃下车来。
这是她第一次在北京的相馆拍照。她抬头看着这相馆的构造同摆设,似乎比过去在上海拍过的宝记照相馆、致真照相馆都要疏散随意许多,倒同北京常见的院落一般,四四方方,周正安然。
徽音注意到相馆门口的墙上贴着一张红纸,上以毛笔书写着几行楷体字。顶头略大的标题,正经写着“电灯照法 与众不同”:
今有用电照相新法 形容毕肖 妙极新奇 能如人四五尺高矮 照出之相 神色生辉 且能久存 永无退色之虞 由六寸起可映至六十寸高 配景备有树木竹篱楼台亭阁石山等 一应俱全 蒙顾者请至店内
一旁穿墨色长袍的男子戴着玳瑁边的眼镜,笑着站到她身边来。
“这位年轻小姐可是第一次照相?我们这里的贵客,可不须登楼呢。”
“登楼?”徽音歪着脑袋,疑惑道。
“喏,就是那一层。”眼镜男子指了指高处的一层台子。
徽音眯着眼迎着阳光看过去,那个位置似乎尤易被日光眷顾,不过如今已似个小小花园,摆了几盆夹竹桃和一大缸莲花。
“过去没有电灯照相,贵客们来了都需登楼,用日光照明。否则拍出的相片总是暗淡,神态难辨。”他继续解释着。
“我在上海宝记照相时,可也从来不用登楼啊。”徽音想了想,认真地说。
眼镜男子那和善的笑脸立马变得有些尴尬,只好抓了抓脑袋,咳嗽几声。
林长民哈哈一笑,揽过徽音的肩膀,道:“上海宝记可是康有为先生都连连赞叹的相馆,自然技艺高超。总站在门口说什么?来,快快进去拍照。”
就在这让相馆引以为傲的电灯照明下,徽音同表姐轻轻偎着,穿着培华女校好看的制式校服,永远留下了十二岁清丽而天真的丰神。
相照罢了,林长民将女孩们送回学校,便又吩咐司机去政府办公。
徽音同语儿挽着手,亲昵地走进了学校内。
“下午就要上第一节课了,有点紧张呢,你也不在。”到了教舍门前,语儿拉着徽音的手轻轻说。由于她长徽音两岁,所以被分在了较年长的学生中一同学习,高徽音一个年级。
“这有什么,认真听着便是。若是女老师叫你回答,遇见懂得的问题就说,不懂得的就冲她笑一笑。”徽音说着,调皮地冲语儿眨了眨眼睛,两人又一起笑起来。
“你们下午要学什么?我们是英文。”徽音问。
“我们是科学吧。”
“好的,那下学见。”
“下学见!”
待徽音走进教舍,许多女孩子已经各自找好了位子坐着,屋内只有最靠前的一排还有空位。
刚坐下不久,便有一位年轻的女郎走进门来。
她着一袭浅灰色裙子,外罩一件长款的朱红色开襟粗针织上衣,身姿翩然;仔细看去,双眼十分明亮,鼻梁很高,肌肤也充满了活力的光泽。
“各位可爱的小姐,我是大家的英文老师。我姓赵,不过我更喜欢你们叫我Anna。”这位微笑着的美丽女郎迅速吸引了教舍中所有十二三岁女孩子的注意力。
徽音认真地听着。父亲在家也曾经教过她英文,加上Anna小姐讲话清晰而富有耐心,所以听起来并不吃力,反而觉得饶有趣味。
“……那么,我们来为每个人取一个好听的英文名字吧。”
Anna小姐微笑着,走到了女孩们的身边。面对老师的靠近,许多孩子都害羞地低下头去,只有徽音眨巴着眼睛,乖巧而从容地迎上Anna的目光。
“这位美丽的小姐,能告诉我你喜欢什么东西吗?比如,白雪、蓝天、飞鸟。”Anna走到徽音面前,俯下身来温柔地问道。
“我喜欢花,各种美丽的花朵。”徽音清晰地答道。
“那就叫你Flora好吗?这是罗马神话中花神的名字。”
还不待徽音回答,身后就有一个女孩子的声音响起来:
“不可以!Flora是我的名字。”
教室里所有女孩子和Anna一同循声望去,第三排椅子上,一个下巴尖尖的漂亮小姑娘正神气地站着。
“Anna小姐,Flora是我在家时,叔叔为我起的,不可以让别人叫一样的英文名。”她认真地说。
“是吗,你叫什么名字?”Anna微笑着问。
“付冰清。”
“付小姐,这世界上其他姓付的小姐也还有许多哩。那么若是其他付小姐也恰好叫了一样的名字,也没什么事情吧?更何况这位小姐同你还未必同姓呢。”她的语气始终温柔如春风,“你叫什么名字呢?”
“林徽音。”
“那么,你们一个叫作Flora林,一个叫作Flora付,可以吗?”Anna依旧微笑着问两个小姑娘。
“不可以!”又是心急的付冰清抢着开口。
“若是北京城还有其他叫付冰清的女孩子,叫我遇上了,我一定也不自在。何况每日一同上课,怎么可以叫一样的名字呢?”她认真地说完,有些气呼呼地鼓起嘴巴来。
“付小姐……”Anna还要说,徽音则在一旁开了口。
“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我也不好意思抢付冰清同学的名字,何况以后走在一处,别人叫Flora,也不好分清楚呀。请Anna小姐帮我另取一个吧。”
Anna点了点头:“好的,那你就叫Phyllis吧,这是希腊神话里的美女噢。”
满屋子的女孩子都本能地冲付冰清看去,教舍里发出几声琐碎的低语。付冰清嫩白的脸微微发红,低着头坐下了。
两个钟头过去,今天的英文课便结束了。女孩子们都各自整理着桌上的书本。
“林徽音。”一个有些羞怯的声音在徽音耳边响起来。抬头一看,付冰清正双手交十握在胸前,有些害羞地看着她。
“你好。”徽音冲她友好地一笑。
“你好。”付冰清显得很开心地点点头,“我可以知道你的名字怎么写吗?”
“好呀,给你看。”徽音从抽屉里将放好的英文课本重新取出,翻到扉页,指着自己写的名字。 “林徽音”三个小楷字后面,还带着几个优美的英文字母——Phyllis。
“啊,你的字真漂亮。”付冰清由衷地赞叹着。
“谢谢,你的名字也很好听。”
“那个……今天真对不起,我太没有礼貌了。”付冰清秀丽的脸又泛出微红,“那个英文名字是我最喜欢的四叔为我起的,所以我很
珍惜。”
“没关系没关系,我很喜欢Phyllis这个名字,你看——我都写在书本上啦。你千万不要放在心上。”徽音赶忙摆手。
“谢谢你。”付冰清感激地看着她,漂亮的眼睛里闪着友好的光芒,“徽音……很高兴认识你。你家住在哪里?”
“我也很高兴认识你,冰清。”徽音开心地一笑,“我家住在后王工厂。不过……我们刚搬到北京没多久,家里还一团乱呢。”
冰清快乐地拉起她的手来:“徽音,今天下学还早,我父亲在政府忙,应该还没有回家,我可以邀请你去我家玩吗?”
少女之间的友情总是感性又浪漫,一旦彼此欣赏,亲密度便突飞猛进。从陌不相识到手挽着手,或许只相隔不到一个钟头。
徽音趴在语儿表姐的教舍窗外,踮着脚看去,里面的科学老师似乎全然没有结束授课的意思。而语儿端正地坐在椅子上,认真地盯着前方。
“给她丢个纸团进去吧!”冰清在一旁出着主意。
徽音赞许地点点头,接过她递来的纸张,认真地写道——
“语儿:同课上结识女友付冰清去她家中玩耍,约三个钟头后付家司机送我至家,告爹爹勿念。徽儿。”
写罢,将纸张用手掌揉成个小团。趁着科学教师低头翻书的工夫,顺着窗子轻轻向下一丢,纸团便不紧不慢滚到了语儿的鞋子边。
语儿听到轻响,低头捡起。阅罢又看到窗外徽音同个漂亮的小姑娘一齐眼巴巴地看着她,赶忙冲她们轻轻点点头,又将手放在裙子下面小心翼翼地摆了摆。
徽音同冰清嘻嘻一笑,这才放心地向校门奔去——付家的司机定然已经在外等候着了。
一踏进付家的院子,徽音便小心翼翼,准备着随时问好。谁知除了来往的仆佣,却没见到一个付家的长辈,就被冰清拉着一路进了她的闺房。
“爹爹果然还没有回来,娘可能在奶奶房中忙着呢。这样最好,我们玩我们的。”冰清开心地引着徽音坐在小竹椅子上,自己则坐在她对面的床上。
“你们家是才搬来北京城的吗?那过去你住在哪里?”
“嗯……先是杭州,后来去的上海。总之对北京来说,都是江南啦。”
“杭州?”冰清听了,好奇地睁大了眼,“那里应该很美吧?有一片很大的西湖。听说江南的屋子也比北京的好看,都不会这么方正
死板。”
“嗯,西湖很美的。北京的屋子也很好看呀。我倒觉得,这里四四方方的,均衡对称,更有种庄严的感觉。”徽音认真地说。
两个女孩子又快活地聊了一会儿天,一位女佣轻叩了门进来,为她们端了花茶与点心。
徽音一眼便注意到了那别致的茶具。虽也像是常见的釉上粉彩,但那彩绘中的花朵却与别处不同,显得尤为娇粉清新。这正是徽音虽未曾亲眼见过,却无比熟悉的樱花——幼时她拥有的那只宫装人偶,便穿着一件印着这樱花的小小和服。
冰清见她看得出神,自豪地说:“很漂亮吧?这是我四叔从日本带回来的。”
“这么巧?我爹爹也去过日本。我小时候很喜欢的一个布娃娃,就是从日本带来的。”徽音惊讶道。
“真的吗?不过我四叔又去日本了,现在还没回来呢……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回来。”
冰清垂下了眼睛,长而浓密的睫毛轻轻盖住她有些失落的眼神。徽音不由得想起了自己想念爹爹而不得见的寂寞童年时光。
“你同你四叔很亲近吧?”她有些小心地轻轻问着。
“嗯……四叔最疼我,我从小也最爱同他玩。他走了,我……很想念他。”冰清的回答也轻轻的,声音却透着种努力保持乖巧的难过——这是徽音多么熟悉的感觉啊!她心里涌上一阵熟悉而轻盈的忧伤,不禁拉住了冰清的手。
“也不知道日本有什么好的,一个个都爱去。”徽音气呼呼地说。
“就是的。”冰清也鼓起嘴巴,“去了一趟都还不够。”
两个女孩一同抱怨完,又不约而同生气地翻了翻眼睛,随即又被彼此的默契与一致逗乐,拉着手笑个不停。
“哎呀……你刚才说布娃娃,”冰清突然想起来似的,坐直了身子,“四叔也送过我一个呢,不过我不喜欢这些东西,就在我爹的书房角落摆着。不如我拉你去看吧,要是你喜欢,我就送给你。”
“啊,这怎么行,这是你四叔送你的礼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