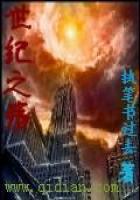这客人与以往所见的叔叔们有些不同。他有些微胖的身体裹着新式的西洋套服,平展的上衣松开了几粒纽扣,刻意露出里面同样平展的马甲。他的皮肤同头发的颜色和父亲似乎都是接近的,五官也说不出有什么迥异。只是鼻子下面正趴着一小撮胡子,整齐地向下方延伸着,仿佛在凶巴巴地监视着下面的嘴巴何时开口。
刚刚的话便是他笑着对徽音说的。
这人讲起话来,虽是嘴角分明认真地上扬,眼睛里却毫无笑意,僵硬得像两颗玻璃珠。配上他那让徽音觉得颇有些不适应的装束和气质,整个人都带着种古怪的违和感。
这人倒是兀自说着,丝毫没察觉到父亲怀里的徽音有些警惕的眼神。
“每一年的三月三日女儿节,日本各户都会将这样的宫装人偶摆放起来,替我们抵挡厄运,守卫幸福。”
啊……这只小小的宫装人偶——竟远渡重洋,从日本来到江南。这可比徽音出过的远门要远多了。
她在心里暗暗想着,却仍旧有些抗拒跟这位古怪的叔叔对话,只是脖子往后缩着,小心翼翼地点点头。
这个日本男人却突然将桌上的宫装人偶抓取起来,递到她的眼前。
“送给你!”
美丽的人偶被他粗糙的手抓着,小和服的缎面都微微皱了起来,那平顺刘海下的双眼却仍然是笑意盈盈,一点都不因这粗鲁的手而生气似的。
小徽音忍不住睁大了眼睛,继而转头看向爸爸,目光里带着探询的意思。她第一眼便是喜欢这只漂亮娃娃的,只是听那个男人叽里呱啦说了一通,却越发有些迷糊这礼物可不可以收下。
“女儿节之举,原是异国风俗,你不必谋效。当作个好看玩意拿去玩就罢了。”
林长民缓缓开口,微笑着冲她点点头。徽音这才放心地将人偶接过来,小心翼翼地把它身上的衣服拉平,将圆圆的小身体抱在手心。
“谢谢叔叔。”别扭又小声,像只刚睡醒的猫咪。
拿了小人偶,徽音便跑出了房门,独自在外面的庭院玩耍,等着张妈稍后带自己去吃晚饭。
那满院鸣叫着的蝉喉咙里仿佛总是堵着什么,叫得扭扭捏捏,好不情愿。这别扭的声音一直持续着,保持着固执的节奏,充斥了整座宅子,像一个技艺单一却热爱表现的演奏团。
徽音仰着脑袋认真听了会儿,想要听出这演奏的主题来。
千万束阳光正温柔地向地平线洒落,黄昏慢慢浮起了它金黄色的轮廓。光与影的碎片被揉成了半透明的纱,流淌向看不到的山谷和海洋。
徽音突然想,这些鸣叫着的蝉,是把白天都吞到肚子里去了吗?它们一面唱歌,一面偷偷地吃掉光明,把黑暗挂上天空。
而这世界上有那么多、那么多的阳光——难怪它们的喉咙里总是吞吞吐吐,绵绵不绝呢。
晚餐席间,徽音被张妈放在母亲旁边的椅子上。
母亲依旧穿着鹅黄色的衫子,腕上也依旧戴着那只如意图纹的银镯。只是这镯子在她手上,显得越发晃荡了——她终日郁郁少食,自然一天天地消瘦下去。
记忆中每每她要抱小徽音时,徽音总是开心地伸出一双小胳膊迎着,母亲那只银镯便调皮地同她手上的小玛瑙镯子相碰,发出清脆的声音。有时母亲轻抚着徽音的头发,那银镯又恶作剧似的缠住了她柔软的发丝,她仰仰头便疼得快要掉下泪来。
只是徽音已经很久没有被母亲抱过了。
自从麟趾死去,何雪媛就终日恍惚,寡欢寡言。徽音既心疼母亲憔悴的面容,也因屡屡不被母亲正视而觉得惧怕,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在母亲面前处处小心,不敢再如以往般嬉闹。
如果依然可以在母亲温柔的怀里开心地撒娇,就算还是会冷不防被缠住头发,也没有关系了吧。
犹豫了一下,小徽音还是将今天得到的人偶从小口袋里摸出来,轻轻拉了拉母亲的手,给母亲看。
“娘,这是今天爹爹房里的叔叔送我的日本国娃娃。”
母亲的反应竟不似她想象中那般冷淡,而是认真将那只人偶拿过来,放在桌面上仔细端详。
“……真漂亮。”她轻轻地说。
“娘要是喜欢,可以送给娘。”徽音无比开心。被亲爱的母亲夸赞了自己的玩具,简直得意到什么事都愿意乖乖去做。
何雪媛只是轻轻摇了摇头。她依然仔细看着那只微笑的娃娃。
乌黑的头发,乖巧的平刘海,雪白的皮肤,一直带着温顺笑容的美丽面孔,这一切漂亮而精致的细节,都让她想起了一个曾经那样美丽的孩子。
“这布娃娃虽然是好看,但我看还不如我们小徽音呢。徽音现在就那样清秀,长大后一定更是个大美人。”
正坐在徽音对面的大姑母笑着说话了。她原本是住在外面的,今日也来宅子里看祖父,顺道一同用晚餐。大姑母是父亲的大姐,虽是女子,诗书学问却十分通晓,为人也温柔可亲,每每见到徽音都要抱在怀里疼爱一番。
听到大姑母这样的夸赞,小徽音粉嫩的脸上微微泛红,轻轻摇晃着脑袋,有些害羞:“徽音谢谢大姑母。”
“……徽音也就是清秀罢了。”母亲突然在一边开口。
“徽音的眉眼太细,要真论起来,还是麟趾好看。眼睛又圆又亮,才两岁睫毛就又长又密,风一吹总爱眯了眼呢。”
母亲若无其事地说着。大姑母愣了愣,知道她自麟趾死后忧伤过度,也并不同她分辩。
徽音有些害怕地低下头去。她知道,母亲又要开始说妹妹的好了。
“麟趾的皮肤最是细嫩。”何雪媛兀自说着,丝毫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
一桌子人都沉默地不接腔,只剩下她自个儿一味地说下去,仿佛戏台上独白的青衣,周身笼着层水雾般的烟。
“麟趾年纪虽小,已看得出尖尖的下巴,好看极了。有时她熟睡了,我在旁看着她的面容——皮肤像缎子,鼻尖儿也是翘的,嘴巴像朵小小蔷薇。若是她长大了……”
何雪媛的眼神突然黯淡下来。继而眼睛微微垂下,无数的悲伤慢慢飘落在地上。
“若是她长大了……”她有些发痴地念着这一句。最终吐出一句话来,“……比徽音,可要漂亮多了。”
满桌的人都沉默着,死一般的寂静。
何雪媛这样兀自发起痴来,不顾旁人地念起麟趾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情了。起初大家都同情她——先是幼子夭折,又是麟趾两岁而亡,心中自是有无限悲恸;可时日久了,也无人能长久地怀抱着宽容的态度对待她无休止的怨念。如今连家里的佣人,都是尽快做完活儿就努力离何雪媛远一些。
她身上仿佛罩着一个巨大的玻璃罩子,周身所剩的气场都是满满的悲伤和绝望,拒绝了所有的喜悦与平和,寻常人都近不得身。
最可怜便是徽音。
还只有五岁,就经历了弟弟妹妹的早夭,且要面对这样被命运的不幸击溃了的母亲。
大姑母林泽民看到小徽音坐在母亲身边,怔怔地抓着自己的衣服下摆,嘴巴微微抿着,眼里蕴着孩童那种不懂得倾诉的悲伤和难过。她心下怜惜,起身将小徽音抱到自己怀中坐下,也不看何雪媛,径自温柔地为小徽音夹了块晶莹的龙井虾仁吃。
“谢谢姑母。”
林泽民夹筷子的手微微颤了一下。她分明听见了小徽音那声稚嫩的“谢谢”里,有喉咙口压抑的哽咽。
林长民在书房外背着双手站立着,闲看着墙上攀附的金银花。
徽音的五岁生日刚刚过去,五年前她诞生的时日,便是金银花开得正好的时候。
“爹爹!”小徽音开心的声音传来,他回头俯下身,小丫头就伸出胳膊,一下抱上了他的颈子,被父亲稳稳地端在怀里。
“今日可有乖乖念书?”
“有啦!”小徽音一面答着,一面用手指调皮地捏着父亲鼻梁上的眼镜架子。
虽然父亲在家的日子也多是繁忙,可同徽音在一起的时候,他总是那般慈爱温和,从来没有横眉对她讲过一句话。和父亲在一起的回忆,每一件都是欢乐而温暖的——被父亲抱在臂弯里散步,闹着要父亲把自己背在肩膀上玩耍,或是在父亲坐着喝茶时抱着他的双膝撒娇。
尤其是母亲渐渐不愿再同她玩耍后,父亲的温暖更变得像天赐的幸运,他的怀抱就是小徽音最喜欢的温床。
“爹爹走后,你也要每日认真念书。”父亲依然笑着说。
她却一下子急了:“爹爹要到哪里去?”
“日本。和上次送你布娃娃的那位叔叔同去。”
徽音一下子放下心来。父亲也不是第一次去日本了,上次父亲去了日本,只一个月就回来啦。
“好的,等爹爹回来我给爹爹背诗歌。”
“那要背好多好多首咯。”林长民捏捏徽音的小脸蛋。
“爹爹这次要去很久很久,回来的时候也许你已经长大了……”他有些愧疚地说着。徽音还这么小,她知道很久很久会有多久吗?
“……为什么,要很久?”小徽音努力问出来这句话。
她并不懂得长久的分离——除了妹妹教会她的死亡。但无论是多么久的“离别”,如今的她都觉得不舍。
每天黄昏落下的阳光都那么多,满院的蝉都要吃好久好久。
她不想一个人度过这数不清的黄昏日落。
她希望爹爹能在自己身边,一直一直,陪自己长大。
林长民有些怅然。他不知该如何回答仅有五岁的小女儿。
告诉她,其实在这个宅子外的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大动乱?
告诉她,一样叫作战争的魔鬼,已经几乎要吞噬了中华?
告诉她,万千的士人都感到了自己彻头彻尾的无能,破损的国权已经岌岌可危,所有的有识之士都在不顾一切谋求着救国的途径?
告诉她,自己将要去日本,是为了学习他们的维新,学习他们的先进,学习他们的政治、科学、文化……一切可以让祖国远离怆痛的
本领?
这些连成年人都难以承担的惶恐和不幸,怎么可以告诉天真的小
徽音?
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奔走,通过所有像他一般的人的努力。在这些天真的孩子长大之前,把中国拯救回来,变作一个完好的神州,给孩子们看。
也许他们终究会懂得那段历史,但他们永远、永远不需要承担那份身处其中,睹其支离的悲哀。
可是,数千年的腐朽等待着清扫,千万计的铁蹄正将国土践踏。
想要力挽狂澜,想要扭转天地,想要拯救这朝夕飞速扩散着的沦丧——一代人,真的做得到吗?
父亲已经走了。
徽音独自坐在庭院里,裙子上放着那只美丽的布娃娃。阳光透过稀疏的树叶,落在那精巧的红色和服上,投下闪亮的光点。
她想起那日问父亲:“这只布娃娃真的可以抵挡厄运吗?”
当时父亲是这样说的:“若是普通祈福,也就似你娘念佛一般没什么两样,美好祈愿罢了;若是已经做出了天理难容的事,却希望通过奉个漂亮娃娃就能逃过报应,也未免太自欺欺人、无形助恶了。”
“那——它到底可以让人逃过不幸吗?”听不太懂父亲的回答,她只好把问题简化了,抓着父亲衣角又问一次。
“……会的。”
要是早点有这个布娃娃,麟趾或许就可以逃过那场不幸,现在,还在庭院里和自己一同玩耍吧?依然可以看到她乖巧的笑容,握着她柔软的小手,听她用糯米饭一般甜的声音叫自己“只只”。
徽音有些难过地想着。
如果那样,母亲现在……也就不会那么冷淡自己了吧?
父亲走后,徽音好几次去找母亲,想陪着她说话。母亲却都只是敷衍,连眼睛都不怎么看向她,唯独说得长一些的句子,都是关于不在了的麟趾的。
麟趾的温顺,麟趾的漂亮,麟趾的聪明,麟趾的可爱……这些,曾经是徽音引以为傲的事,也是徽音最最乐于跟别人讲的事。如今仿佛变成了符咒一般,自母亲的口中吐出,似乎要将她从母亲的面前快快赶走,不可留恋一秒。
夜深人静的时候,徽音抓着被子躺在床上,还会难过地想起妹妹落水的那个夜晚。她无法想象麟趾那娇小的身体如何挣扎着被水面吞噬……这让她自己也觉得快要窒息。
她也很想这个时候,扑进母亲的怀里,放肆地大哭出来,让所有对妹妹的追思,对死亡的恐惧,都化作透明的泪暂时离开自己。
可是她始终不能在母亲的怀里痛哭。
因为母亲……母亲……
她沉浸在失去麟趾的悲伤里,已经忘了同样年幼、同样经历了这场噩梦的徽音。偶尔想起,只是拿来比较,讲述麟趾的好。
徽音有时候会悄悄地想,如果麟趾没有去……如果一定要有一个人去,就像宫装人偶顶替了人类去接受不幸,那她愿意是自己。
如果溺水的是自己,母亲也许会比现在好受些吧?毕竟,她心中更好的女儿……是麟趾啊。
姑母她们都说,天下父母对自己的孩子,自然都是很爱很爱的。这爱就是与生俱来的本能,并将永无止境,一直陪伴着孩子们温暖幸福地长大。
可这“爱”既然应该是温暖的事,为什么却偏偏也会有多少之分?
无论是生来注定的缘分,还是得到与失去的偏重,总让本该足够的爱显得相对稀少。
就连至美好、至温暖的事,细想来都这么残忍,这才是这世界本来的面目吗?
“只只,只只。”麟趾清甜的声音若有似无地传来。
徽音抬头一看,那个熟悉的可爱身影正站在自己面前,回头冲着自己笑。
麟趾的身后,是那池噩梦般的荷花。
徽音惊恐地奔跑过去。她绝不要看到妹妹跌落在水里失去生命,永远离开大家。
可是她无论怎么努力地迈着双腿,似乎都无法缩短到麟趾身边的距离。她的小腿已经酸到不可置信,眼泪在奔跑中飞向耳畔,拉成刺一般细长的线,沾湿了头发。
而小小的麟趾,始终静静地站在那个可望而不可即的距离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