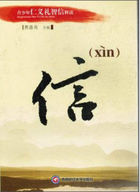〔挪威〕史蒂根我从北极区移居首都奥斯陆已有多年,但对那极地岁月仍然魂牵梦萦。童年时在极地的生活教我甘于寂寞,勿急功近利;教我勤于思索,勿浅尝辄止;教我以自己的心灵而不是仅仅以自己的五官去感受自然,感受生活。
最难忘的是极地的一位盲人。他只身蛰居在海滨的一间小屋里,在常人看来他实在是极其可怜的——唯有一根拐杖可以相依为命,甚至连一条做伴的狗也没有。而他最大的不幸当然是他的失明了。这样他就不能够亲身去体味光阴的变幻和季节的交替。
然而,这恐怕只是人们好心的揣想。说到人与自然的交契,我还不曾发现有哪位明眼人能够超越他的。当极夜将尽,太阳快要在地平线上重新绽开笑脸的日子里,人们都会看到他的身影:信步经过大街旁的人行道,而后径直走上小山,再沿着山脊,在赤杨林中找到一条通往山脊的小路。然后,他找到一处四际一无遮蔽的所在,面向南方凝神而望,浑然忘情于对初阳的等待。个把小时之后,他又会准确地循原路归来。
要是在一场新雪之后,人们就更容易判定他是否到过山上了。因为这位盲人尽管在这个人的生活享受上十分节俭,但他穿的胶皮套鞋总是新的。所以,只要一发现他的套鞋印在雪地上的足迹,人们就完全可以相信:暖人心海的太阳即将来临。
当时,还没有什么人像今天这样侈谈什么“默契”,什么“沟通”。在这位老人的时候,“默契”之说尚未流行,他自然也决非在追求时髦以沽名钓誉——他只是个深深地渴望着能体味那初阳灵趣的人,虽然在他的脑海中那也许只是一抹紫红的闪耀。
这两件事的紧密相连:新雪上波纹的痕迹和太阳的新生,使得这位盲人在一些和他具有同样渴求的人们心目中占据了永生不灭的位置。我们这些人虽然双目炯炯(也许这正是障碍之一),却反而看不透极夜之后的辉煌,而难以摆脱漫长的不安的折磨,全然没有盲人那种沉着坚定的自信之情。
——心里有了这位盲人,在生活的跋涉中,太阳永远是不落的。